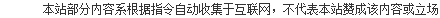关于《我们分手好多天了,等着你回来来好么》范文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4-06-10 03:19
时间:2014-06-10 03:19
《枪击事件》的访谈录及再解读 | 文章 | ARTLINKART | 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
《枪击事件》的访谈录及再解读
栗:我们从早期作品说起。肖:我可以从我的毕业作品开始谈起吗?栗:有更早的吗?肖:更早啊。我跟你这样讲吧,毕业时我做了这个《对话》草图之后呢,当时是毕业创作,我到现在特别感谢郑胜天老师,因为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带来好多新的观念。我当时也做过一些材料,比如油画,后来也用些宣纸,但我还是在平面上做,没有做完全立体的概念,没有一下子摆脱画的概念,然后郑胜天老师让我用照片,他说你就用照片,用真实材料,这个对我的引导起了很大作用。栗:这是哪一年?肖:1988年,那是我在做毕业创作的时候,创作过程是这样,当时这个构图出来以后,我决定用这个材料以后,报给油画系批,要小稿通过,油画系不同意,说我们油画系不能有一件这样的作品,把这个作品给枪毙了,当时这个作品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郑老师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大概他也觉得这个作品做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但最后是妥协了。我随便找了张照片,画了张油画,这个是油画系的毕业创作,那个是做参考的。我的毕业创作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是打分的毕业创作。栗:哦。肖:所以当年这个毕业作品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得很感谢宋健民、郑胜天老师,他们都尽量帮助我把这个事做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油画系一件非油画作品产生,是这么一个过程,1988年做的。然后我这个作品做完之后,我请宋建民老师看,他现在是中国美院副院长。当时这种纸条还没有,画面特别干净,然后他们几个人说这个画面太干净了,要破一下,而且这个红颜色跟下面有些脱节,所以从形式上考虑这都是后加的,就说这个玻璃啊怎么怎么样,其实真正打枪的想法是我跟宋建民有一次谈话谈到的,当时说这个玻璃啊是不是破一破,然后我们俩就说,拿弹弓,或者拿什么气枪,拿什么枪,就是在这种说的过程中,但是也没有想做不做这个事情。我讲讲我这个作品的原始构思吧,其实我写了一些东西,要不要给你看?栗:一会儿吧。肖:因为当时郑老师也要给我写一份东西,有一次高名潞过来,她跟我说这事,让我写份东西,后来我就写了,但我这东西还没寄出去,但是我写完了。她说你就完全真实地把你的东西写出来,我把原始构思到整个发展的过程写出来了,其实我最原始构思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情感作品。1988年之前我对情感这个东西有点困惑,应该这么讲,从这个作品本身可以看到这是男女对话,我最初的构思是男女对话,这个电话是一个不通的电话,可以看侧面那种符号,你走进去看这半个男的半个女的有种呼应,那种符号,那种悬挂的忙音,这是当时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吧,其实我是在这种状态下把这个完成的,当时还是对一种男女之间的困惑吧。但是当时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触还是蛮多的,因为好多东西内容和形式还是有一种有机的联系吧。这个打枪的想法其实是1988年和一个老师偶然谈到的,谈到之后也没去做,然后在展出之前,我问一个杭州射击队的,叫沙勇。这些人都还在,你都可以去采访,宋建民、沙勇、郑胜天,你都可以去问他们事实,沙勇给我借了一把枪,那时借了三个小时,那天也怪了,不知怎么我就不见了,他怎么都找不着我,三个小时以后,他就把枪还回射击队了,等于这个事就没完成,还是存留在脑子里。等到我这个作品入选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我在方舟咖啡馆见到唐宋,跟他说起这个事,唐宋真正跟这个作品有影响是在我跟他说了这个事以后,他说你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两枪,我说有什么不敢的,我说我北京有个哥们叫松松可能还有一把枪,为什么我知道他有一把枪呢,因为我小时候,他那时大概七八岁吧,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的外公是当时天富山起义的头,他的爷爷也是最早山东第一军的,所以跟他关系很好,然后到北京附中的时候我一直教松松画画,每个星期天都学画画,然后他给我亮过他有一把枪,那把枪应该说是他奶奶的,他奶奶的一个战利品。栗:哦,不是他爷爷的?肖:不是他爷爷的。栗:哦,等于是老枪。肖:是他奶奶的自动枪,特喜欢这个孙子呢,就经常给他玩,带他看看,也经常收回去,就是自动手枪。栗:是什么型号的?肖:松松他也记不清是什么型号了,小时候因为我每个星期天都到他们家里去教他画画,所以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就给我亮过那把枪,小孩儿吗,他说,姐姐你看我有一把枪。所以当时唐宋跟我提这个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如果到北京我那哥们能给我借把枪,我就打。所以等于是在杭州方舟咖啡馆跟他谈了这个事,他提示的我去打这一枪,跟他关系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我就去问松松,松松当时还在一个公共汽车上,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借把枪给我,松松说那时候正好他奶奶住院,那把枪就在他那。栗:他奶奶叫什么?肖:叫什么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得问问他奶奶,他爷爷叫李耀文,就那海军政委的。栗:现在退了么?肖:退了。栗:还在世是吧?肖:在世,等于是他奶奶当时一个战利品。栗:不是现在配的枪。肖:这事我也问过松松,我问当时我是打电话给你的还是跟你要的,松松说你当时来北京上我们家去了,你当时在公共汽车上跟我谈,你声还老大老大的,我吓死了,我说肖鲁姐姐轻点儿。我说这事行不行,他说没问题,我正好有把枪。我现在回忆这件事,应该说有很多偶然性促成了这个事情,不是当时像唐宋说的那样是有预谋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呢,如果说预谋,他连第二天把枪拿来都不知道。栗:当时他来布置那个电话亭,我问他,他说先不说,还在计划。肖:他当时到北京来,想搞什么抽血车,他知道打枪的事,应该说在杭州他就知道我这个打枪的事,他是一个知情者,他真是一个知情者。栗:那时候你们在恋爱吗?肖:没有啊。栗:哦,那时候还没有在恋爱。肖:没有啊,我是在打枪后从监狱里出来才跟他好的。栗:呵呵。肖:我就跟你讲这个关系,没有,我跟他没好。我1988年都没认识他,我真正认识他是在方舟咖啡馆前几天认识他的,那时候我做电话亭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对生活挺迷茫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顺的感觉,当时我打完枪之后有一种挺爽的感觉,就是人的一种解脱什么东西的感觉。唐宋的出现我觉得挺奇怪的,我当时觉得他带给我一种幻觉一样,尤其在监狱。我当时打枪前一天,就打不打这个事跟唐宋谈过,因为他是知情的,松松是知情的,最早只有这两个人是知情的,其他谁也不知道,我跟松松也说过,松松是小孩,当时他才15岁,他觉得打……栗:当时他没有上附中?肖:上附中了,刚上附中,他就说肖鲁姐姐打啊,多好玩啊,他是这种观点,因为作为松松来讲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我也没有说……老实说,你说我当时政治这根弦才有多强,老实说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强,不过唐宋是有一点。栗:嗯,唐宋有。因为我后来在台湾时讲起这个作品时,唐宋老是在找一种临界点,他可能对政治比较敏感。肖:他对政治敏感,但是他这个人,就像你说的,他读那些古书,读孙子,他很有计谋,包括这个事情,说实在的,要出了事判刑,是我跟松松判刑,他没事,他根本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被抓进去呢,其实后来想是这样的,这事你可以看那个录像,我打枪之前他说了句“打”,我“啪啪”打了两枪,打枪的时候旁边有个便衣,这个录像上有的,便衣就想先把他抓住,当时公安有一个最明确的想法就是这个男人在教唆一个女孩儿打枪,所以把他抓去了,是这么回事。到最后我记得是,那两天本来他没地方住,前两天他住旅馆,打枪前一天我说我要住我姥姥那去,你要不住那儿去也可以,他跟我一块儿去的,当时我姥姥没让他住,我那时候有男朋友,他那时候也有女朋友,我们两个当时没什么关系,你知道了吧。我当时也问他,我说第二天打枪的事,他说这是你的事,你的作品你自己做主,当时这一枪打不打说实在完全是一念之差,所以松松给我打电话那天还说,“肖鲁姐姐你打吗,打吧!”,我说你把枪拿来再说,所以松松就把枪拿来了。当时松松把枪拿来都十点多了,唐宋不知道把枪拿来没有,他走的时候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带枪。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好像有点印象,侯瀚如说我跟他说过。他上次来也跟我讲,你当时怎么说怎么说的,他回忆得很清楚,松松也回忆这事,松松说你当时脸通红通红的,好像是有点紧张,因为这枪一直揣在我手里,里面有三发子弹,全部在里头,上膛都上好了,“叭、叭、叭”就出去了。我印象不是太清,怎么跟侯瀚如说的我都不太清楚了,他说你把我叫到美术馆栏杆边上,说我呆会儿要打一枪,怎么样,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跟高名潞还不熟,跟你还认识,然后侯瀚如就说呆会儿吧,等人少点你再打,我不知道了,我当时可能有点紧张,所以我真记不清说了什么了。他说你就这么说的,我说可能吧。当时如果说打枪之前我想得到一些什么的,我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然后我还通知过一个叫居易的,我说你等着,你给我拍,就居易知道。唐宋是11点到的,他根本不知道我把枪拿来了,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把枪带来了,他挺兴奋的,就说真的拿来了,我说拿来了,松松帮我拿来了,他比我这个意识强,他就问了一句,肖鲁你怕不怕坐牢,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他说那好,那就打吧,然后我就把松松叫来了,他、我、松松,那个录像我们仨在这嘛,都看的见的。然后他在边上说了句“打”,我就打了。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栗:打了两枪?肖:打了两枪,还有一发子弹在里面,挺悬的,还有一枪。松松说当时他上了三发子弹,不是,一共五发子弹,他在地窖打了一枪,然后他为了试这个枪,又到后海打了一枪,然后给我留下三发子弹,总共有五发子弹,就是这样。我给他的时候是我打了两枪,我把枪交给松松,唐宋这边呢,旁边的便衣就先把他拿下,就把他抓走了。我看到他被抓走,我就跑到黑盒子去了,枪交给松松我就跑过去了,就说松松你揣着枪,我到黑盒子以后,我忘了我当时找谁了,我说帮我挡一挡,把我护出去,好像是《东南西北》(黑盒子)那边的作者,我也搞不清是谁,有三个人把我从后面护出去的,护出去我就到了百花美术商店,然后我就在对面看。栗:然后你传信给我了,我不知道你托了谁,我现在记不起来这个细节了,你托了人给我捎话,怎么办,我说你就出来吧,出来去跟公安局说清楚。肖:那可能是下午了。栗:就是下午了。肖:几点了?4点了。栗:已经把我们几个负责展览的人关在美术馆的小会议室里,公安局的给我们开会。哦,你一直在百花呆着呢!肖:百花呆着的时候,中间我全部看到,警车过去,美术馆关闭,唐宋抓走,我全看到了,其实我当时真觉得……栗:闯大祸了?肖:闯大祸了,这个哥们被抓了,一个哥们被抓了,因为不管怎么说知情者是我和松松、唐宋三个人。栗:松松没事?肖:松松拿着枪就走了,因为他没有叫打吗,唐宋在边上叫了声打吗,就给抓走了。我记得当时还给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那个人也是一个高干,我还说有一个哥们被抓了怎么办,能不能帮忙,我当时真是……其实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说,但是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美院一个叫万曼的。栗:哦,我知道万曼先生,他在当时的浙江美院有工作室,谷文达、梁绍基、施慧就是他的学生,曾受过他的影响,对中国现代艺术有贡献。肖:万曼在我毕业创作时也给我很多帮助,他对我们当时整个美院“0’85思潮”有影响,而且这个作品创作过程中他给我提过一次意见挺有帮助的,包括这个空间的处理他也给我提过意见,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对他挺信任的,这件事我第一个就跑到北京饭店找他,但我觉得他死了说这件事不好。我当时就把整个事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你不应该找我”,任何意见都没有,我当时觉得……栗:这也可以理解,这种政治事件外国人没有参与是明智的。肖:当时我就离开北京饭店了,但是我对他还是很感激,所以这件事你不一定要说。栗:嗯。肖:然后我就上了一个美术馆旁边路上一辆公共汽车,非常奇怪,我从终点坐到终点,坐了多少个来回都忘了,一直坐到下午大概将近四点钟左右,我记得我是四点左右去自首的。中间就是干了三件事,一个在百花,一个是去了北京饭店,一个是在汽车上坐了几个来回,然后我就决定自首了。栗:当时你是传给我一个话——怎么办。肖:那是回来以后。栗:那时候是不是在百花,自首之前?肖:就是我自首之前,我没有到美术馆过,我就在外面晃,晃到三四点钟,我决定自首,自首那时我见了很多人,然后也传话了。我记得我自首的时候跟那门口的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去自首,他都不让我进去,后来传话进来了,我说你跟里边讲,我是肖鲁,他们会让我进去的。因为我那时,想好自首的时候这个事就很简单了,我就决定进去了。自首完了之后就是那么回事了,就给我扣住了嘛。然后先到一个什么地方我都忘了,然后又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东城区拘留所大概是,是不是啊?栗:对,东城区拘留所大概在现在的亚运村附近,那会儿亚运村是工地,我去东城区公安局找你们,他们说拘留所就在那,我就找了个出租车,我,还有廖雯,还有谁我忘了,大概两三个人,找到拘留所,他们说人是在我们这里关的,但是已经走了,我还带了一盒点心,呵呵。肖:对,这个当时松松跟我讲,他说他特傻,我把枪给了他,他用傻瓜相机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他把傻瓜照相机给了我,他说给我拍了一卷,结果公安局全部没收曝光了。他说都小吗,小就没那么多想法。审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我当时的状态是有点慌的,因为我那时才26岁,当时做现代艺术凭着一种激情和冲动,很多东西在这里边,而且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很刺激,各种兴奋在里边。真的这个事情出了以后,我从内心诚实地讲,我没有像后来很多人说的那种很有预谋的、策划好的,实际是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个事情。你要说这件事预谋的话,要说唐宋预谋的话也不是,他预谋的话很多事他根本不知道,他不能算预谋的。然后到监狱里,我跟唐宋一直说,我真正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从这个地方审讯完,他从那个地方审讯完,然后我们在监狱门口有个地方相遇,那时候都铐着就要进牢房的时候,他对我那一笑,我当时觉得那一笑特别蹋实。可能我觉得在特定环境之下吧,心情又紧张,然后又有个男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事他一块儿做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挺好的,如果说浪漫情怀就是那时候产生了,应该那么讲,真的,老栗,呵呵……所以说他们那时候问过我,这个作品给你带来最大的是什么?我说这个给我带来最大的是爱情。因为当时可能做这个作品之前我是这个状态,唐宋什么状态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后来跟他说你当年就是爱上我那一枪吗,就这么问他,他没话说。我记得我当时在监狱里的心情就是那个心情,觉得挺舒服的,所以出来以后才好的吗,我们俩真正好,离跟他认识也没多久。好了以后大概就到你那去了,有天晚上去谈,那天晚上其实我头很痛,你记得吗,我在隔壁,我有个头痛病,犯头痛病几乎没谈什么东西。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当年对他有这种感觉,爱上他我也没什么怨言,后来我发现他,后来这个作品不是变成两个人的吗,我也认了,说实在我是认了,其实这中间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到最后跟我在一块儿面对这个事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很不舒服,这是真的,包括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他都不敢对人说,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法说实话,所以为什么面对你老栗那么多年,你有没有听我说过一句话?我不能说。栗:但是我以前一直认为是他和你共同策划了这件事。肖:共同策划?他策划借枪?知道我第二天拿枪来,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介入是从监狱出来,介入进去的,因为要说真正介入是那天晚上他跟你谈,我也不知道怎么谈到最后就成他策划的了,在之前我看了所有的媒体没有他的,是不是啊,应该这么说。我这个人呢,当年应该说我是认了这个事的,到后来我从来不对媒体说话了,你可以查,没有一个话是我说的,因为我没法说这个事,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说实话跟他太……没关系,他呢,也不让我说,那么多年我没说过,因为我觉得这份感情很不容易。后来的经历也非常不容易,非常坎坷,也经历了很多事,说实在我是一个把情感看得挺重的女人,所以我对这个名其实无所谓,无所谓你的我的,就是这样一回事,其实很多东西我是看你这个人,实际上我觉得他当年……当年这个事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后来他跟我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一直到15年后我们分手的时候让我彻底失望了,我不骗你。他这个人我后来看清他,在大名大利面前他太可怕了,所以后来分手,我说我绝对相信他当年就是爱上我那一枪,真的,因为他干出的事让你相信这一点,真的,因为15年的情感,他可以完全……为了一点利益这样做,没意思。那天的事我不是说到今天才说,真的,我可以永远不说这个事,我可以永远不说,包括在杭州,其实在杭州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都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想法不是他的。那个宋建民,你可以采访他,宋建民就说至少这个想法是我们两个人谈出来的,想法不是他的,策划的话从头到尾你要去借枪,你都知道第二天枪拿来,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误抓进去的一个人,是这么回事。他从监狱出来以后,他可以说政治嗅觉比我敏感,他知道这是个什么事,我承认这点,他知道要把握这个事,可能我想他是应该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要清楚,我可能……作为当时来讲,我没那么清楚,这是真的。可能从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他也起到一些作用吧,就是这样,我那天晚上因为头痛,我也记不清他说什么了。栗:他说了很多很玄的东西,他有笔记给我,写的都是那种什么“孙子兵法”上的一些。肖:但他说这个作品的实的东西没有吧?栗:没有,始终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东西边都没有沾。所以我后来谈这个作品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件,从社会、政治敏感度这个角度来谈。肖:因为,老栗,我觉得吧,这个作品产生是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它的产生必然会有政治性。那天我跟高名潞谈,我说至少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你得承认吧?作者是我,唐宋是一个解说者。栗:他其实也没解说多少东西。肖:但他是个解说者,他不能算个作者,但是后来对记者基本都他解说,我不解说,因为他说的东西挺玄的,他可以说得很玄很玄。栗:他喜欢谈玄的东西。肖:我今天应该这么说,我写了一个东西,就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客观的一种东西,就是客观很多因素,比如一环扣一环的因素。当年我想打枪,我借了枪没打,这个东西存在,偶然性我正好在咖啡馆遇到唐宋,跟他说了这个事,他说你敢不敢打,这都是偶然,对不对?这都是偶然性,但是必然性就是,我还是想打这一枪,从头到尾有想打这一枪的意念,还有很多比如我跟松松借枪,松松有这枪,中间很多偶然性,差一环这个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说这个作品在历史上评价我,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说,但是当时,咱们现在谈事件这个事实吧,我可以说清楚,一件一件怎么发生的,中间很多偶然因素,我这个事从来没跟人说过,唐宋跟人谈从来就是谈我跟他在方舟咖啡馆策划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在方舟咖啡馆说了这个事,说起当年要打枪的这个事,这是真的,这个事也是我跟一个宋建民老师谈起的一个事,这都是事实。所以说如果你想采访这个事的真实性的话,这些人你都可以去采访,一个是宋建民,包括当年借枪的沙勇,你都可以去问他,他借过一次枪,他是射击队的。所以说这个想法跟他唐宋也没关系,他有一点,你跟他说这个想法,他提示了你,这个是他起到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事件的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栗:你能具体说说当年在监狱里审问时候的具体情况吗?肖:审问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到当时的记录。栗:不是,你就回忆一下就行了。肖:审问的记录,就是他们就问我,那男的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教你打枪。说实话老栗,我这人会说实话,说瞎话我是不会说的,我肯定说他是知情者,最早的知情者,因为在杭州最早就跟他谈了这个事,不可能他不是知情者。审了好多,审了这个枪的来源,当时我是如实说是从松松那来的,我把松松这个事也说了,松松当时就被扣下来了,在家里。我们关了三天,他也给扣了三天。栗:在家里?肖:恩,内控起来的,我们放了才给他自由,是这样的。松松后来跟我讲,如果真要判刑,我跟松松是要进去的,因为我是打枪的,他是偷枪的,唐宋是知情者,要判刑呢,我不知道,我跟松松是肯定要倒霉的。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具体把我们放了呢,松松说其实是跟我爸爸,跟唐宋的爸爸有关系的,唐宋的爸爸是个参谋长,不是什么军区司令。你要说跟我爸爸,跟他爸爸有关,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权力,你要说跟松松爷爷或者是什么,当时是捅到中央了,他们家为这个事还是担了一点责任,但是这个事具体为什么放,还是上面决定的,因为当时政治上一种大的气候,有一种说法是胡起立当班,然后听说乔石听说了这事特别生气,说怎么能把我们放了呢?!胡起立当时春节当班,政治局讨论这件事。栗:松松爷爷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肖:松松爷爷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点作用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当时这个事捅到中央了,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事跟政治没关系,不可能,但是如果法律健全的话,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俩还是要判刑的吧,跟1989年的政治空气有关,其实你说再是什么军队的官,该判刑还是判刑的。栗:中国还是不一样,要是我打枪就不一样,这跟政治有关的……肖:那……我觉得还是跟1989年有关系吧。栗:都有吧。肖:我觉得这是综合的因素,我们打枪这个事是很偶然的各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也有特定的因素促成吧,有一种必然性。栗:后来松松没有听到爷爷说什么话吗?肖:爷爷当然不高兴了,一直……爷爷做检查了这个事,人家当然说他了。栗:应该奶奶做检查,这个枪是奶奶的,呵呵。肖:但是他爷爷不会理解这个是现代艺术的一件事,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松松也是受了很大的牵连,应该这么讲,但是现在还好,我们两家关系还是可以。栗:他们放你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肖:去的时候,当天晚上来了好多好多人看我,都是些老头,我当时……栗:你能回忆起来都是些什么人吗?肖:都是些老头。他们说是我们整个大年三十都让你给搅和了。我当时关在一个牢房里,有一个小洞,窗户打开,每个人进来,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有个老头进来就说,就是你啊,害的我们整个大年三十都没过好。后来我听他们看守说,全是他们公安局的最高官,全部来了。栗:公安局的?肖:全是大官,我不知道什么官,一个一个打开窗户这么看,然后我在里头。栗:有没有跟你认识的?肖:没有跟我认识的。我记得当时审问我的那个人特别逗,老是问我一些关于现代艺术的事,我就跟他谈谈谈,然后谈完之后我说你关心这个干吗,他说我儿子现在在学画,我真怕他有一天走火入魔,也干你这样的事,呵呵。这个是我有印象的,其实回忆回忆当时那个情形挺好玩的,也许,应该说当时我的心,唐宋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比我更清楚一点,也许吧。栗:松松家离这远不远?肖:不远,我叫他过来,你应该采访采访他。唐宋一直跟我暗示什么呢,就说情感这个东西是不能说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品,绝对棒,往高里说,往虚里说,得这么说。 栗:他那天晚上跟我出来讲,一晚上都是讲的很虚,我也弄不懂。肖:我今天跟你说的都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东西,包括做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作品,但是也许我的误区也是在这。他说说这个就把这个作品说小了,但有时我现在想,其实作为一个作者,他做一个东西的原发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原发点导致打这一枪,我不知道有些画画的怎么弄,反正我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完全是要有一个东西让我要做这个的,比如我想打这一枪,一直这个念头没有断,总是有一个内心的冲动让我去做这个东西。栗:但是为什么没有用别的破坏办法,为什么想打一枪呢?肖:因为打枪,我不是说政治临界点,你要了解我,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而且非常情感化的人,完全是这样的,包括我作这个15枪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完全到了那个点上,一口气的,就是要到那去打这一枪,打完枪以后人很舒服啊。我觉得艺术有一种求生……栗:宣泄的。肖:宣泄的一种东西,当你不顺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东西淤积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栗:但是宣泄有各种方式,为什么选择枪呢?肖:解气啊,这玩意“咣”一枪打完多解气啊。打枪这个手段,当那天我跟宋建民说完这个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枪就在我脑子里了,留在那个地方了。其实他跟我说这个枪,我们谈到枪,一直到我到射击队借枪,是很长一个过程。但比如说,你在画作品时候很多人会给你提建议,你吸收什么,选择什么,脑子是有种选择的过程。栗:当时那个情景是什么,他怎么提示出来枪的?肖:当时我在一个房间里在做这个作品,你可以采访宋建民,具体有的话我都记不太清了,因为两个人具体怎么对话我都忘了,但是这个打枪的点子是我们俩谈出来的。他就说这个玻璃好象怎么,我们谈到气枪,谈到砖头,谈到什么,他就说把这个玻璃破一破,他说要破得又有痕迹又不弄破,他说咱这玻璃太平,当时连个横条都没有,就说这个太干净了。他是从形式感考虑,我觉得我来接受用枪这个东西呢,我是认为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当你选择一个形式的时候内心一定有一种冲动,就说这个形式一定跟你内心一致的你才会选择它,否则你不会选择,每天信息很多,看书可以有提示你的信息,我们毕业创作时多少老师给我们提意见,这个老师说两句,那个老师说两句,好多人提意见的,为什么就接受了用枪这个信息?!这完全就跟内心一种东西的存在有一种呼应。栗: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择枪,因为枪这个东西,在我就永远不会想起枪,即使想起也不敢往这想,因为我不可能搞到枪,就是搞到枪也不敢打。是不是跟你以前跟松松接触时有关系,有这印象?肖:这倒没有。我觉得我这人情感不顺的时候想用枪,真的,包括现在我……现在好点,前一阵子我连打15枪,打完舒服多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艺术是排解一种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是在特定的心理导向之下,选择一种特别极端手段可以治愈某种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有某一种提示,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了。栗:你还是没有说破这个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也你的身分有关系。
李松松访谈 肖:松松,接受采访。栗:说事,说最简单的事,弄得清楚一些。肖:我们不会说理论,呵呵。栗:我自己都说不好理论。李:就从开始说吧。开始是肖鲁到了北京,然后找我。栗:这是哪一年?李:应该是1989年年初,我在附中上一年级。有一天下午,我姐姐跟我说韦容在找你,韦容当时不教我们吗,我不知道她找我干嘛,我去那屋里,肖鲁坐在那了,很多年没见了。然后好像就是当天晚上我带肖鲁去我们家,不是当天晚上就是第二天晚上,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后来在电车上肖鲁就问我,松松能不能搞到枪。那天我还跟她说,现在我要想起来,我还能记得那电车是坐到哪一站,就是府佑街和西四之间那站,拐弯的时候她还问我,挺奇怪的,反正记得挺清楚。然后我说,我这正好有把枪。栗:枪的型号你记得吗?李:枪的型号我不记得了。栗:是把老枪吗,不是那种配给的枪吧?李:好像应该不是,但是具体我说不准,因为我不是那么了解这些型号,但是是自动手枪。因为自动手枪问世也有七八十年了吧。栗:是国产的枪吗?李:这个我也弄不太清楚,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国产的,因为我记得枪把儿上有一个五星,但不是那种军队五四式的那种大枪,是小一点的,不是太大,好像能装九发,还是七发子弹我忘了,我给她带了三发子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枪,在前一年暑假时候我自己在家,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他们都不在。栗:可以说奶奶名字吗?李:就别说了,她都过世了,不在了。就是从她那偷出来的,然后我就一直自己玩,放在我那,当时没想过什么,因为我想拿出来玩肯定得还回去,后来一直没找着机会还回去,就一直偷了半年,然后这时候肖鲁来北京了,我说正好……我记得当时还是问她要做什么用。栗:不是去抢钱吧,呵呵李:不是去抢银行,呵呵。肖鲁就把她这个事说了一遍,她要做这个作品,然后为什么想打一枪,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觉得这个作品太完整了,她想破一破。我当时觉得这个事,首先它是和艺术有关系的,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刺激的,“咣、咣”发两枪,但是我希望的是我把枪借给肖鲁发两枪,然后我再把它拿回去,这是挺幼稚的。栗:你完全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李:完全没有想到。我相信肖鲁说的,我完全没有这根筋,就觉得这个事可以瞒天过海,当时就是单向思维,只想到主观的一面,希望的一面,说实话可能也想到坏的那一面了,就是闯了祸,但是具体会怎么样就完全没想,就不想了,就往那面想。我觉得这事挺好玩的,我就说可以啊。后来展览前一天晚上很晚,那时候大家睡觉都睡的很早,不像现在,可能十一点了,她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们家的电话是在走廊里,得到走廊里接电话。肖鲁跟我说,听说现在风声很紧,打枪这事打不打,她当时说话很慌张的,不知道她在哪打的电话。当时我一听她这个我有点失望,你想一个15岁的孩子就觉得这个事挺兴奋的,我说哎呀,都决定了,还是做吧,然后肖鲁就说反正明天你先把枪拿来,类似于见机行事吧,她不会说出见机行事这样的词,但类似这个意思,就是把枪拿来,然后咱们到时候看,是打还是不打。我第二天就把枪带出去了,我跟家里人说我去看展览什么的,上午的展览,然后肖鲁说中午我请你吃饭,家里人都会问中午你回来吃饭吗,我说不,肖鲁姐姐请我吃饭,约好了,挺高兴的。我把枪放在兜里,我那个羽绒衣有一个内兜,两用的,我放在左边,骑车去了美术馆,然后到了美术馆,我忘了具体到那是几点了,我记得我到那还在外边转了一会儿,然后差不多十点左右到的那。我记得我见到肖鲁大概是类似于10点40分、10点45分,反正我给她枪的时候是10点45分,当时就在美术馆正门的西边走廊边上,我把枪给她,然后我教她怎么用,很奇怪,现在想起来这个简直太明目张胆了,因为当时周围很多人,大家走来走去,还有人在那看,两个人在那捣鼓一支枪,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看,我当时也稍微遮掩一点,但也没太怎么样。我带了三发子弹,都在枪里,我告诉她怎么放进去,然后一拉枪栓,就上膛了,这时候就可以用了。肖:当时你帮我上的栓吧。李:我帮你上的栓,我把保险扣上去,我说你开枪前把那保险扳下来。肖:我记得我打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干,都是你帮我弄好的。李:那可能是,因为那天我看那个录像就是。看录像上是她打枪之前我在她旁边,这是肖鲁,那是电话亭,我就在她旁边好象说什么,然后我一看那个带帽子的是我,因为我都忘了,好多都忘了。当时我还有这个概念,这个枪别走火了,所以打之前把保险扳下来。这也很奇怪,因为肖鲁当时跟我说要打两枪,事后想这些事都挺奇怪的,当时我也没问她,为什么是两枪,不是一枪,或者三枪,是两枪,但是为什么我给她带了三发子弹,这也很奇怪,还有一个备用的,这很危险。肖:你不是试了吗?李:不,那是在夏天的时候,我偷出枪来自己玩,在玉渊潭打过两枪,自己玩,都没有人知道。打枪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11点10分这样的样子,在打枪前10分钟我把枪给了肖鲁,我在美术馆门口外面给的她,然后肖鲁就走了,走了以后我碰见韦容了,韦容看见我好像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样子,也没说什么,还觉得有点尴尬的,因为韦容当时是我们老师。后来我就过去了,可能又过了一会儿,我在里面转了,看看其他的作品,可能在打枪之前5分钟或者10分钟,我碰见肖鲁,肖鲁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唐宋,唐宋当时穿一军大衣,握了下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好像基本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开枪了。开完枪以后,因为我站的地方离开枪的地方不是很近,比如肖鲁在这开枪,我可能站在那个位置。栗:10米左右?李:不到10米,6米左右,唐宋在那个位置,一堆人在那边这样围着,“U”字形的,你看那录像上也是这样的,有人拍照片,还有人站在很高的地方,然后我站在这边,边上一点,当时我的印象是枪声太响了,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来也打过,在野外就没觉得那么响,因为这是在一个大厅,非常响。当时响完两声枪,我觉得人们也是非常有意思,这种事情因为枪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大家听到响声,呼一下就往这跑,就在那个厅深处的地方,“哗——”就往这跑,跟潮水似的,就好像一定要看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人们怎么都那么激动啊,后来一堆人就涌到门口去了,肖鲁也看不清楚了。栗:当时她就给你枪了吗?李:不,当时一堆人涌到门口。过了大约三分钟她跑过来了,满脸通红,完全像西红柿那样,特别急的步子,当时她好像穿一个半高根的皮鞋,“哒哒哒”就跑过来了,喊“松松,快把枪转移”,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我当时觉得这个事你非要这么喊吗,周围都有人看着呢,但是周围的人看也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嗖”地就把枪塞给我了,然后我就又把它放回兜里,这时候那枪还有一发子弹。她连着喊了两遍,“松松快把枪转移”,这个词很像地下党说的,连着说了两遍这个话,然后她就跑了。肖:没跑,我到黑盒子去了。李:我当时不记得了,反正你就消失了。但是我是和聂牧站在一块儿,我不知道聂牧记不记得这个情景,因为当时我跟她约的去看那个展览,然后我当时要故作镇静,因为闯了祸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挺镇定的,然后我就去看别的馆了。聂牧当时怎么回事呢,她好像就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又碰见了。然后我就把美术馆其他的厅的展览都看了一遍,我不能只在肖鲁打枪的那个厅呆着。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走了,我当时也在想,等一等吧,因为也不知道事态怎么样,当时完全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主要想的是瞒天过海,没有什么后果。然后在美术馆的西北角的那个厅,就是我最后转到那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就说,“都出去,都走了,闭馆了,出事了”,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这个事闭馆了,我还问那个人,“为什么闭馆”,那人就说“出事了,你不知道,那边都打枪了”,这个其实已经是起码有半个小时以后了,你想我转了一圈,当然转的也挺快的,当时人也不多了,然后我走到门口,到下美术馆那个台阶的时候,一下去有几辆……不对,我回忆错了。肖鲁把枪给我的时候我出去了一次,出了美术馆武警守的那个门,我出去了以后,那时候大家已经都往外走了,还不是特别……后来我又进来了,我有美院附中的学生证,学生证是可以随便进的,我跟武警拿了一下学生证他又让我进去了,然后我进去以后又转了一圈,转到那个西北角就往外轰人,就说闭馆了,一个人也不许在这,然后这时候又出去,进出这么两次,第二次出来的时候就有好多车开进来了,我记得有一辆是公安部的车,那时候公安部的车有那个牌子,公安的“A”,就是公安部的车,这叫急啊,开到台阶口那,然后我正好下台阶,从那上面跳下来,一男一女中年人的样子,急匆匆地往上面跑了。为什么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呢,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事闹大了,在这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这个事闯了祸了,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然后我走出去之后,很无聊,没事干,快到中午了,还跟肖鲁约了吃午饭,肖鲁也不见人,我就到对面的百花书店去看看书啊什么,看书的时候我把肖鲁的相机就落在书店了,那个相机我拍了至少有两张她打枪的照片,然后我从书店出来就去了聂牧她妈妈单位,因为聂牧告诉我她要去她妈妈单位,下午要看电影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没事,挺晕,就钻到那了,一个礼堂就看了小半段电影,结果没有散场看见聂牧,打了个招呼,后来过一会儿她出来,我们在她妈妈单位门口见面,然后我这时候发现相机没了,我跟她又回到百花去找相机,他们还给我了,这时候大约有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然后就在百花对面,美术馆的街前面,我们在那走路,很巧,肖鲁就跑过来了,就又碰见肖鲁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撞见了。肖:下午是4点钟吧。李:没有,我记得差不多两三点这样,不是太晚,后来可能在小花园里又待了很长时间,在小花园里是你的小姨夫吧……反正是她的亲戚,中年夫妇,我记得那男的很冷静,他就劝肖鲁,也劝我,主要是劝肖鲁,就说这个事,现在没有其他余地,就要去自首,什么都要说清楚,劝我也别背太大的包袱,有什么呢回家就跟家里人承认,当时这个我当然是不愿意了,我本来是希望瞒天过海,结果现在要承认什么的,这个压力太大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选择的,我也答应了。可能在这个说话的当中聂牧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肖鲁去自首,我回家。然后就从小花园到美术馆那段路,可能有一百米吧,我骑车带着肖鲁,到了美术馆门口肖鲁下车,然后她就进去了,我就一直目送着她,那时候可能有四点了,冬天的西边的阳光暖暖的照着美术馆,她就一直往里走,上了台阶以后好几个警察就涌过来了,然后肖鲁可能是跟他们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呜——”就把她拥进去了,我一看,哦,好了,我就走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栗:后来呢?李:后来呢,就是我比较惨了,家里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整个我的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是比较感激他们的,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怎么严重化,而且他们尽量自己承担这些责任,比如我父亲觉得很多是他的过错,我奶奶觉得是她的过错,我爷爷也写了检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件事应该说和他们是没关系的,如果按组织原则来说,但是他还是写了检讨,后来他们就没有怎么再提这件事了,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小孩很冲动。栗:肖鲁刚才说你还被在家里被看管了好多天。李:有一个细节,那天不是大年三十,是初一早晨,后来我觉得我爸挺厉害的,当天晚上他就知道这件事了,但他也不表达,我和我妹妹、我妈都不知道,大家还是和平常一样,第二天早晨我们还一块去看一个电影,临出门的时候在门口他接了个电话,然后他说好,知道了,他跟我说,松松,公安局现在说你不能随便出去,你要在家待着,我就明白了,我还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栗:回去就把枪交给奶奶了?李:不是,我没有主动说,我不知道那时候该怎么办了。肖鲁她第一步就会有人问她你枪是哪来了,她就会说是哪哪,然后当时是海军的人来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找我家里人,就直接找我,问怎么回事,我就都招了,然后把枪给他们了。栗:交给公安局的了?李:不是,交给海军来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还录了口供这样的东西,让我签字。栗:是什么时候?李:当天的晚上七八点。栗:家里就全知道了?李:家里当时还不知道呢,等他们拿到所有的证据以后,包括枪也拿到手了,他们最重要的是把枪拿到手,然后他们才跟我家里人说的,这中间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栗:也都是当天发生的? 李:都要当天解决,不然对谁也没法交代。栗:那天就是三十啊?李:对,那天就是三十。栗:大概不让你出去多久?李:后来也就没有,那次打电话就说现在不要出去,但是以后也没有说,就没有再说什么时候出去,或者现在还不能出去,初一的那天说现在不要出去,后来可能在家呆了几天,但是后来也出去了。栗:公安局直接找过你么,都是海军找你交涉?李:没有,他们具体怎么交涉我也不清楚,这个我不了解,因为后来我不直接面对他们了,我就直接面对我爸。栗:后来肖鲁出来你知道情况吗?李:我知道,因为当天我,初一还是初二,各大报纸都有一条很小的消息,就是肖鲁、唐宋在中国美术馆制造枪击事件,后来被,那个词是什么,收审啊还是,不是拘留,反正像收审啊这样的词,很简单,没有说什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反正这样的大报纸的一小条。后来出来也知道,我忘了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听家里人说的。栗:那是初二吧。肖:反正是出来以后。李:不是吧,你们怎么能初二出来的,应该是初四出来的。肖:不是初二,……后来有一个东西是唐宋写的,然后他……栗:他们出来你家人专门做过努力吗,你知道么?李:这点我不知道,因为这种事情他们不会跟我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这个事是作为一个艺术行动,也不参与政治,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危害,也没有伤人啊什么的,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被附中开除,我闯了这么大祸,有可能怎么样,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栗:家里的基调还是没有那么悲观?李:我觉得还是具体的事情他们不跟我说,因为一贯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家一贯是,比方说,星期天大家都回来聚会,说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事情,所以像这些事情,包括比如说内幕的事情我不会知道。栗: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主要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里边都是没法预料的。你当时那么紧张,揣个枪居然看了个展览,呵呵。李:居然看了个展览,居然转了这么长时间。栗:要是我,……呵呵。肖:还有一发子弹呢,哈哈。李:对,当时我因为那个年纪吗,有一点恶作剧的心理,就是觉得“哼——”,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栗:刚才她也有。后来就把我们几个留在美术馆会议室,不让我们走了,有结果了才让我们走的。李:审查,是吧,关了多长时间呢?栗:一天。李:大家都呆在那儿?栗:很晚都在那儿。李:哦。栗:中间就是我出去写那个牌子,“现代艺术大展因故停展”。然后中间肖鲁你托人传话给我,说怎么办。我说那就向公安局说清楚就行,你还是出来别躲着。肖:我那时候可能在外面。栗:那是谁传话给我,后来我又传过去了?李:那你又是传给谁的呢?栗:现在都完全记不住了。好像是个艺术家。肖:好像是这样的,我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我叫肖鲁,我说你传过去。反正中间可能我到美术馆外面,就是在汽车上转了一圈回来在美术馆外面的时候,可能是见着那个人……栗:那人说你就在附近。我就说你回来把问题说清楚,我想问题不会太大。栗:你再想想枪……肖:包括砖头,说过砖头,说过气枪,具体这个对话已经搞不大清了。后来好像是他提的手枪,因为手枪速度快。栗:谁呀?肖:宋建民说的,也许气枪,也许气枪速度不快。因为当时我们家有气枪,气枪“嘣”一打不就完了吗,它就把玻璃打碎了,用手枪的时候是说速度又快,又能留下裂痕,玻璃又不破。栗:我也有体会,因为“文革”的时候有一天坐在屋子里,流弹打到我的面前,窗户就一个小眼,弹差点就紧挨着我腿地方,然后就从地上弹到床上,我从床上捡到那个弹头,挺逗的。李:在哪?栗:在邯郸,我还读高中的时候。肖:这是在谈话时完全话赶话谈出来的。但是至于怎么借枪都好像觉得不大可能,就又把这事搁在那了。后来是有一次我赶上沙勇,他射击队的,这些都是赶上的。你们射击队能不能把枪拿出来玩玩,结果那个沙勇还挺哥们,行啊,我帮你借啊,所以这些都很多偶然因素在里边的。李: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借枪是很容易的?肖:我那时候觉得借枪是很容易的。然后那时候唐宋一说这个在美术馆打我马上就想到松松,这个玩意就各种巧合因素在里边。那天晚上我记得你们谈了很多。栗:但后来谈的都和这个具体事没关系,当时好像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肖:我就是头痛的很厉害,张培力在,唐宋在,后来就你们几个谈。栗:后来所有的艺术家都很泄气,都觉得这个展览因你们两个的枪把别人都毙了,呵呵。因为大家都觉得进了美术馆出名了,这个枪响了,别的都逊色了。李:我当时没有,我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我慢慢知道这些事情。去年碰到一个山东人,当时在你们对面。肖:丢避孕套那个。栗:还有一个人,是李群。李:对,那个李群,他说他当时是一块做的,当时唐宋在,还有他,还有艾未未在。然后他说,哎呀,你就是当时那个,你把我们全给那什么了啊,我们就白干了,哈哈。栗:那时候张培力和吴山专都很泄气。肖:老栗,我想问一下,后来把这个定为一个事件艺术是当天晚上就定的么?栗:不是,事件艺术是我写的文章时候想的一个。肖:想的一个词。栗:因为有人说是偶发艺术。我后来想想前后经过呢,觉得偶发艺术有点不太准确,因为偶发艺术就太现场了,结果就说了个事件艺术。肖:事件艺术就是和这个有关的都在这个艺术里边?栗:那当然。 肖:那松松也应该算啊。栗:但是你是主要,看怎么解释这个,我还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说清楚,评价这个作品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作品发生以后还会连带很多别的。肖: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原创的东西。栗:原创的东西和连动的东西,就是它的外延。肖:外延展示出来的一些东西。栗:因为我不是了解这个前后经过,我有一次在一个社会学系讲这个中国社会的艺术,谈唐宋其他的作品,比如他老关注、想找临界点,就是他那个鸟巢的、火柴的,后来你们在悉尼时候是一起做的,是吧?肖:后来他就一直拉着我跟他合作,这个作品实际主要是他的。栗:还是跟他那个鸟巢一样的一个想法,有点危险,但又没有真正发生危险,在中国这个社会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在这个临界点才刺激,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危险了,不在临界点又不刺激,我就讲这样一个“高峰体验”的关系,只有在中国社会才有这样的人敢去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也是多年做编辑老想找这个临界点,我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但是又不发错,又很刺激,有时候又过了,1983年我不是被开除了吗,就过了。这中间我也体会这种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打擦边球一样,感觉很有意思的,我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过这个作品的。肖:那你觉得这个作品的临界点是?很多东西是偶然造成的还是必然造成的呢?栗:这个就是要重新去想,所以有些东西要不断地重新解释。我一直好长时间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碰到你少,碰到唐宋多,唐宋每次都不具体谈这个东西。肖:唐宋从来就不许我谈这些事,是真的,所以我在当时没谈过,真的。栗:1993年我在悉尼碰到你的时候,我想趁机把这件事弄清楚。肖:大概有些事要真要谈出来也不太好,关系就少多了。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事不断地会揭示出真相来,解释当然会有变化了。肖:就是因为解释上会发生变化,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看这个问题有很多偶然东西存在。栗:但是如果你在杭州开这一枪,和在美术馆打这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肖: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这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栗:这些我后来就知道的,但是你和唐宋是之后好的我不知道。当时唐宋神神秘秘地跟我讲,一会儿会发生一件事,说我先不跟你说。我是在二楼听到的枪响,上面有两个艺术家有争执,我上去解决那个问题了。你那是录像带还是?肖:录像带,我还不知道怎么转成vcd。栗:我转吧。肖:但是就打枪那一刹那,“嘭嘭嘭”的,录得一塌糊涂。栗: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肖:15年吧。栗:松松才15岁是吧?!李:对。肖:我当年26岁。
以上是2004年春天我和肖鲁、李松松的一次谈话录音整理,此后网上肖鲁和其他人对发生在15年前的枪击事件谈论得很热烈,此时录音已经整理出来,我也写出了整理后记的初稿。我迟迟没有发表,一是觉得肖鲁正为此事很痛苦,我如果不能按照肖鲁所愿谈看法,等于给肖鲁雪上加霜。二是也想听听唐宋的意见,此后,我有几次遇到唐宋,但每次他都喝得酩酊大醉,看着他非常消沉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就再不想对他提及枪击的事情了。今年春天,在和上海《艺术世界》的记者谈20世纪80年代艺术思潮时,我依然把枪击事件说成是两人合作的作品。后来,有一天晚上,肖鲁打电话给我,很生气我说了那些话,这时我才知道《艺术世界》发表了我的谈话(我至今也没有看见该期杂志)。我不知道怎样向肖鲁解释,我理解肖鲁的感觉,但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所以,我的观点对肖鲁造成的伤害,使我深感不安,我愿意就此向她说对不起,我说得不对的地方也望肖鲁和唐宋指正。在我眼里,艺术一旦完成,就不再属于个人,它属于社会、历史和人类所共有,所以,我渴望大家能以超然、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待此事。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在美术馆打那一枪”和在杭州打那一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对话》的装置作品,是肖鲁自己的,如果在杭州打了那一枪,那作品也是肖鲁的,那件作品是肖鲁自己对男女情感问题的宣泄,是一件装置作品,那一枪属于类似画面笔触,抑或色彩等形式上的处理手法问题,诚如她说的玻璃太干净了,破一破,更贴近对“感情问题困惑”的表达意念。 事情的转折是唐宋给肖鲁说了“你敢不敢在美术馆打这一枪”,这不是一般的意见和知情,以及后来在事发的“关键时刻”,唐宋说了声“打”,乃至唐宋先被捕。时间、地点、后果……轰动的社会效应全部聚焦在枪击本身,以及两作者被捕并很快被释放,都已经远离了肖鲁只是表达男女情感的初衷,乃至远离了那件题名《对话》的装置作品,而贴近了唐宋的意图,这都使该作品由肖鲁的装置作品转换成肖、唐合作制造的“事件作品”了。当年我写的《两声枪响——中国现代艺术展的谢幕礼》时,把这件作品说成是两人合作的事件艺术。肖鲁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了十五年,随着萧唐的感情破裂,肖鲁才讲出事件的来龙去脉,声明那件作品是只属于自己的,其实,当时就有不少新闻也没有提及唐宋,而是把枪击事件说成是肖鲁的作品(见附件),只是此后的很多年,枪击事件是属于肖鲁一个人,还是属于肖唐两人,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没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讨论。我所以在肖鲁声明了枪击事件只属于自己之后,依然坚持两人合作的观点,恰恰是因为肖鲁把枪击的原初想法讲得清清楚楚——即表达男女感情的意念和作品手法意义上的打枪意图,或者说,15年之后由于肖唐的感情破裂,“枪击的原初动机”被肖鲁凸现出来,而混淆和抹煞了“杭州枪击《对话》的动机”和“美术馆枪击事件”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过程。 问题的全部结症,集中在肖鲁并不意识到装置《对话》和《枪击事件》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作品,所以把破一破装置《对话》的“枪击”,和产生社会震动的“枪击”混为一谈,所以她“没有想到”社会震动如此之大,或者用“原初想法和结果不一致”来解释“美术馆的枪击事件”。其实被肖鲁当结果说的,正是我认为的“枪击事件”所以有社会轰动效应的原因。如肖鲁在给我信中说的“正因为中国法律的不确定因素,才导致了这件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及法律的弹性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一枪自然产生的结果”,“总之有一点可能帮了我们,那就是我们是把事情捅的太大了,全世界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当然松松的爷爷承担了不少责任,这点我一直觉得愧对于他,但是在中国您是知道的,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导致这个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许这就是1989年的特定气候所决定的,没有人可以怀疑这一点。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疯狂的一年,在政治上相对开明的一年”。在我看来,正是以上原因,使发生在美术馆的《枪击事件》从装置《对话》中独立出来,枪击不是预计发生在杭州的枪击作品那种只属于手法和技术的过程,发生在美术馆里的《枪击事件》作为完整作品,是把社会和政治因素,把肖鲁、松松的家庭背景因素都作为了作品的介质或者作品媒材了。或者说,以上这些因素,对于肖鲁是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对于唐宋,正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如他在日给我的长信中说的:“我在艺术整体观念上认为,艺术是一个试验(或用同义词来补充这个词:实践、实验、实证、尝试、探索、发现、可能等等)”,“这个实验也许由于相似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案件’,或者说‘事件’而显露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是我所要的关于‘可能性’的特点”。“首先,‘事件’作为一个被艺术家所‘指定’的艺术,直接甚至间接与此事件关联的‘事态’,都是被此艺术举动所盖统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相信,艺术一旦和社会生活直接融合——艺术变得社会生活化,作为艺术的形式也将生活化。从这点上看,闻道者也就是予道者,予道者其实也同时是一个闻道者。作为直接制造者,首先是把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实验的参照物,因为他们两人作为艺术家,也是在客观上被特定历史社会所参照的”,“有人说艺术家制造了这个事件,讽刺了其他所有参展的人”。“如果说这一事件有种讽刺意味,那么首先对唐萧两人自己的讽刺,庄子的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上,偷枪(有枪可偷)、肖鲁和松松乃至唐宋自己的高干背景(尽管肖鲁说唐宋的爸爸不是司令员只是个参谋长,但对于平民百姓,其中差距不大)、五天后释放,在对社会法律弹性程度讽刺的同时,也讽刺了作者及其家庭背景能够起作用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肖鲁没有把这些起作用的背景,当做《枪击事件》这个作品的媒质,而当成“自然”因素被肖鲁“自然忽视”了。唐宋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是自身的真正介入,而且可以比喻成置身于一个‘大搅拌机’中打开该设备的开关,艺术家此时也成为‘被搅拌者’。这种举动愈真实,就愈能产生真实的我所设想的真实的社会性艺术。”这就是说,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枪击事件》的意义,更显现在“生活即艺术”这个扩展了的现代艺术经典含义上,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的手工制品上,《枪击事件》在肖鲁15年后所强调的,恰恰是退回到手工制品的《对话》上。 肖鲁写信给我说:“老栗,我不知道形成一件作品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意义为本。我想如果没有作品本身的成立,一切意义都无法形成。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是唐宋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但《对话》的确是一件女人做的作品,男人说的作品。这是一种尴尬还是嘲笑。对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更是一种尴尬和嘲笑。”在我看来,我所有针对枪击事件的分析,正是把肖鲁当做《枪击事件》的作者,当做有资格使用“高干背景”来作《枪击事件》这个作品媒质的艺术家来看待的,而不是把肖鲁当做装置《对话》的女艺术家来看待的。所以,《枪击事件》对于我,其要害或者敏感点不在性别本身,而在于能否使用“高干背景”作为作品媒质这一点上。这就引出更重要一层的事实,当肖鲁处在《枪击事件》的作品中时,肖鲁就由一个作装置作品《对话》的女艺术家,转变成做枪击事件的“特殊艺术家”了。因此,我不同意肖鲁把原初枪击想法,作为自己作为主角的《枪击事件》的动机,理由恰恰在肖鲁以上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美术馆枪击事件的过程中,肖鲁始终有一种忐忑不安和紧张的情绪,以及她打完枪以后像李松松说的整个脸像西红柿一样红。我以为这才是这个作品在肖鲁一方的真正内核—— 一种强刺激的高峰体验。如果按肖鲁仅仅是手法意义上破坏一下作品的干净效果的“枪击原初想法”,那大可不必如此紧张。而且,15年之后,肖鲁又对着自己在15年前《枪击事件》中打枪的照片,开了15枪,这15枪,既没有《枪击事件》时的那种紧张心理,也没有惹祸,更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新闻效应。因为,这15枪,就像她在谈话中回到认识唐宋以前的感情状态,回到装置《对话》那样的打枪状态,回到一个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挥笔画画的手工劳作中,这才是一个女性
肖鲁 共有 7 篇相关文章
关于 肖鲁 (7)
(评论) (评论, 2007) (评论) (访谈, 2008) (评论) (媒体) (访谈)
& ARTLINKART 2015 - 沪ICP备号}
《枪击事件》的访谈录及再解读
栗:我们从早期作品说起。肖:我可以从我的毕业作品开始谈起吗?栗:有更早的吗?肖:更早啊。我跟你这样讲吧,毕业时我做了这个《对话》草图之后呢,当时是毕业创作,我到现在特别感谢郑胜天老师,因为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带来好多新的观念。我当时也做过一些材料,比如油画,后来也用些宣纸,但我还是在平面上做,没有做完全立体的概念,没有一下子摆脱画的概念,然后郑胜天老师让我用照片,他说你就用照片,用真实材料,这个对我的引导起了很大作用。栗:这是哪一年?肖:1988年,那是我在做毕业创作的时候,创作过程是这样,当时这个构图出来以后,我决定用这个材料以后,报给油画系批,要小稿通过,油画系不同意,说我们油画系不能有一件这样的作品,把这个作品给枪毙了,当时这个作品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郑老师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大概他也觉得这个作品做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但最后是妥协了。我随便找了张照片,画了张油画,这个是油画系的毕业创作,那个是做参考的。我的毕业创作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是打分的毕业创作。栗:哦。肖:所以当年这个毕业作品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得很感谢宋健民、郑胜天老师,他们都尽量帮助我把这个事做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油画系一件非油画作品产生,是这么一个过程,1988年做的。然后我这个作品做完之后,我请宋建民老师看,他现在是中国美院副院长。当时这种纸条还没有,画面特别干净,然后他们几个人说这个画面太干净了,要破一下,而且这个红颜色跟下面有些脱节,所以从形式上考虑这都是后加的,就说这个玻璃啊怎么怎么样,其实真正打枪的想法是我跟宋建民有一次谈话谈到的,当时说这个玻璃啊是不是破一破,然后我们俩就说,拿弹弓,或者拿什么气枪,拿什么枪,就是在这种说的过程中,但是也没有想做不做这个事情。我讲讲我这个作品的原始构思吧,其实我写了一些东西,要不要给你看?栗:一会儿吧。肖:因为当时郑老师也要给我写一份东西,有一次高名潞过来,她跟我说这事,让我写份东西,后来我就写了,但我这东西还没寄出去,但是我写完了。她说你就完全真实地把你的东西写出来,我把原始构思到整个发展的过程写出来了,其实我最原始构思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情感作品。1988年之前我对情感这个东西有点困惑,应该这么讲,从这个作品本身可以看到这是男女对话,我最初的构思是男女对话,这个电话是一个不通的电话,可以看侧面那种符号,你走进去看这半个男的半个女的有种呼应,那种符号,那种悬挂的忙音,这是当时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吧,其实我是在这种状态下把这个完成的,当时还是对一种男女之间的困惑吧。但是当时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触还是蛮多的,因为好多东西内容和形式还是有一种有机的联系吧。这个打枪的想法其实是1988年和一个老师偶然谈到的,谈到之后也没去做,然后在展出之前,我问一个杭州射击队的,叫沙勇。这些人都还在,你都可以去采访,宋建民、沙勇、郑胜天,你都可以去问他们事实,沙勇给我借了一把枪,那时借了三个小时,那天也怪了,不知怎么我就不见了,他怎么都找不着我,三个小时以后,他就把枪还回射击队了,等于这个事就没完成,还是存留在脑子里。等到我这个作品入选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我在方舟咖啡馆见到唐宋,跟他说起这个事,唐宋真正跟这个作品有影响是在我跟他说了这个事以后,他说你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两枪,我说有什么不敢的,我说我北京有个哥们叫松松可能还有一把枪,为什么我知道他有一把枪呢,因为我小时候,他那时大概七八岁吧,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的外公是当时天富山起义的头,他的爷爷也是最早山东第一军的,所以跟他关系很好,然后到北京附中的时候我一直教松松画画,每个星期天都学画画,然后他给我亮过他有一把枪,那把枪应该说是他奶奶的,他奶奶的一个战利品。栗:哦,不是他爷爷的?肖:不是他爷爷的。栗:哦,等于是老枪。肖:是他奶奶的自动枪,特喜欢这个孙子呢,就经常给他玩,带他看看,也经常收回去,就是自动手枪。栗:是什么型号的?肖:松松他也记不清是什么型号了,小时候因为我每个星期天都到他们家里去教他画画,所以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就给我亮过那把枪,小孩儿吗,他说,姐姐你看我有一把枪。所以当时唐宋跟我提这个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如果到北京我那哥们能给我借把枪,我就打。所以等于是在杭州方舟咖啡馆跟他谈了这个事,他提示的我去打这一枪,跟他关系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我就去问松松,松松当时还在一个公共汽车上,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借把枪给我,松松说那时候正好他奶奶住院,那把枪就在他那。栗:他奶奶叫什么?肖:叫什么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得问问他奶奶,他爷爷叫李耀文,就那海军政委的。栗:现在退了么?肖:退了。栗:还在世是吧?肖:在世,等于是他奶奶当时一个战利品。栗:不是现在配的枪。肖:这事我也问过松松,我问当时我是打电话给你的还是跟你要的,松松说你当时来北京上我们家去了,你当时在公共汽车上跟我谈,你声还老大老大的,我吓死了,我说肖鲁姐姐轻点儿。我说这事行不行,他说没问题,我正好有把枪。我现在回忆这件事,应该说有很多偶然性促成了这个事情,不是当时像唐宋说的那样是有预谋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呢,如果说预谋,他连第二天把枪拿来都不知道。栗:当时他来布置那个电话亭,我问他,他说先不说,还在计划。肖:他当时到北京来,想搞什么抽血车,他知道打枪的事,应该说在杭州他就知道我这个打枪的事,他是一个知情者,他真是一个知情者。栗:那时候你们在恋爱吗?肖:没有啊。栗:哦,那时候还没有在恋爱。肖:没有啊,我是在打枪后从监狱里出来才跟他好的。栗:呵呵。肖:我就跟你讲这个关系,没有,我跟他没好。我1988年都没认识他,我真正认识他是在方舟咖啡馆前几天认识他的,那时候我做电话亭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对生活挺迷茫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顺的感觉,当时我打完枪之后有一种挺爽的感觉,就是人的一种解脱什么东西的感觉。唐宋的出现我觉得挺奇怪的,我当时觉得他带给我一种幻觉一样,尤其在监狱。我当时打枪前一天,就打不打这个事跟唐宋谈过,因为他是知情的,松松是知情的,最早只有这两个人是知情的,其他谁也不知道,我跟松松也说过,松松是小孩,当时他才15岁,他觉得打……栗:当时他没有上附中?肖:上附中了,刚上附中,他就说肖鲁姐姐打啊,多好玩啊,他是这种观点,因为作为松松来讲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我也没有说……老实说,你说我当时政治这根弦才有多强,老实说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强,不过唐宋是有一点。栗:嗯,唐宋有。因为我后来在台湾时讲起这个作品时,唐宋老是在找一种临界点,他可能对政治比较敏感。肖:他对政治敏感,但是他这个人,就像你说的,他读那些古书,读孙子,他很有计谋,包括这个事情,说实在的,要出了事判刑,是我跟松松判刑,他没事,他根本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被抓进去呢,其实后来想是这样的,这事你可以看那个录像,我打枪之前他说了句“打”,我“啪啪”打了两枪,打枪的时候旁边有个便衣,这个录像上有的,便衣就想先把他抓住,当时公安有一个最明确的想法就是这个男人在教唆一个女孩儿打枪,所以把他抓去了,是这么回事。到最后我记得是,那两天本来他没地方住,前两天他住旅馆,打枪前一天我说我要住我姥姥那去,你要不住那儿去也可以,他跟我一块儿去的,当时我姥姥没让他住,我那时候有男朋友,他那时候也有女朋友,我们两个当时没什么关系,你知道了吧。我当时也问他,我说第二天打枪的事,他说这是你的事,你的作品你自己做主,当时这一枪打不打说实在完全是一念之差,所以松松给我打电话那天还说,“肖鲁姐姐你打吗,打吧!”,我说你把枪拿来再说,所以松松就把枪拿来了。当时松松把枪拿来都十点多了,唐宋不知道把枪拿来没有,他走的时候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带枪。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好像有点印象,侯瀚如说我跟他说过。他上次来也跟我讲,你当时怎么说怎么说的,他回忆得很清楚,松松也回忆这事,松松说你当时脸通红通红的,好像是有点紧张,因为这枪一直揣在我手里,里面有三发子弹,全部在里头,上膛都上好了,“叭、叭、叭”就出去了。我印象不是太清,怎么跟侯瀚如说的我都不太清楚了,他说你把我叫到美术馆栏杆边上,说我呆会儿要打一枪,怎么样,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跟高名潞还不熟,跟你还认识,然后侯瀚如就说呆会儿吧,等人少点你再打,我不知道了,我当时可能有点紧张,所以我真记不清说了什么了。他说你就这么说的,我说可能吧。当时如果说打枪之前我想得到一些什么的,我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然后我还通知过一个叫居易的,我说你等着,你给我拍,就居易知道。唐宋是11点到的,他根本不知道我把枪拿来了,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把枪带来了,他挺兴奋的,就说真的拿来了,我说拿来了,松松帮我拿来了,他比我这个意识强,他就问了一句,肖鲁你怕不怕坐牢,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他说那好,那就打吧,然后我就把松松叫来了,他、我、松松,那个录像我们仨在这嘛,都看的见的。然后他在边上说了句“打”,我就打了。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栗:打了两枪?肖:打了两枪,还有一发子弹在里面,挺悬的,还有一枪。松松说当时他上了三发子弹,不是,一共五发子弹,他在地窖打了一枪,然后他为了试这个枪,又到后海打了一枪,然后给我留下三发子弹,总共有五发子弹,就是这样。我给他的时候是我打了两枪,我把枪交给松松,唐宋这边呢,旁边的便衣就先把他拿下,就把他抓走了。我看到他被抓走,我就跑到黑盒子去了,枪交给松松我就跑过去了,就说松松你揣着枪,我到黑盒子以后,我忘了我当时找谁了,我说帮我挡一挡,把我护出去,好像是《东南西北》(黑盒子)那边的作者,我也搞不清是谁,有三个人把我从后面护出去的,护出去我就到了百花美术商店,然后我就在对面看。栗:然后你传信给我了,我不知道你托了谁,我现在记不起来这个细节了,你托了人给我捎话,怎么办,我说你就出来吧,出来去跟公安局说清楚。肖:那可能是下午了。栗:就是下午了。肖:几点了?4点了。栗:已经把我们几个负责展览的人关在美术馆的小会议室里,公安局的给我们开会。哦,你一直在百花呆着呢!肖:百花呆着的时候,中间我全部看到,警车过去,美术馆关闭,唐宋抓走,我全看到了,其实我当时真觉得……栗:闯大祸了?肖:闯大祸了,这个哥们被抓了,一个哥们被抓了,因为不管怎么说知情者是我和松松、唐宋三个人。栗:松松没事?肖:松松拿着枪就走了,因为他没有叫打吗,唐宋在边上叫了声打吗,就给抓走了。我记得当时还给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那个人也是一个高干,我还说有一个哥们被抓了怎么办,能不能帮忙,我当时真是……其实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说,但是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美院一个叫万曼的。栗:哦,我知道万曼先生,他在当时的浙江美院有工作室,谷文达、梁绍基、施慧就是他的学生,曾受过他的影响,对中国现代艺术有贡献。肖:万曼在我毕业创作时也给我很多帮助,他对我们当时整个美院“0’85思潮”有影响,而且这个作品创作过程中他给我提过一次意见挺有帮助的,包括这个空间的处理他也给我提过意见,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对他挺信任的,这件事我第一个就跑到北京饭店找他,但我觉得他死了说这件事不好。我当时就把整个事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你不应该找我”,任何意见都没有,我当时觉得……栗:这也可以理解,这种政治事件外国人没有参与是明智的。肖:当时我就离开北京饭店了,但是我对他还是很感激,所以这件事你不一定要说。栗:嗯。肖:然后我就上了一个美术馆旁边路上一辆公共汽车,非常奇怪,我从终点坐到终点,坐了多少个来回都忘了,一直坐到下午大概将近四点钟左右,我记得我是四点左右去自首的。中间就是干了三件事,一个在百花,一个是去了北京饭店,一个是在汽车上坐了几个来回,然后我就决定自首了。栗:当时你是传给我一个话——怎么办。肖:那是回来以后。栗:那时候是不是在百花,自首之前?肖:就是我自首之前,我没有到美术馆过,我就在外面晃,晃到三四点钟,我决定自首,自首那时我见了很多人,然后也传话了。我记得我自首的时候跟那门口的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去自首,他都不让我进去,后来传话进来了,我说你跟里边讲,我是肖鲁,他们会让我进去的。因为我那时,想好自首的时候这个事就很简单了,我就决定进去了。自首完了之后就是那么回事了,就给我扣住了嘛。然后先到一个什么地方我都忘了,然后又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东城区拘留所大概是,是不是啊?栗:对,东城区拘留所大概在现在的亚运村附近,那会儿亚运村是工地,我去东城区公安局找你们,他们说拘留所就在那,我就找了个出租车,我,还有廖雯,还有谁我忘了,大概两三个人,找到拘留所,他们说人是在我们这里关的,但是已经走了,我还带了一盒点心,呵呵。肖:对,这个当时松松跟我讲,他说他特傻,我把枪给了他,他用傻瓜相机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他把傻瓜照相机给了我,他说给我拍了一卷,结果公安局全部没收曝光了。他说都小吗,小就没那么多想法。审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我当时的状态是有点慌的,因为我那时才26岁,当时做现代艺术凭着一种激情和冲动,很多东西在这里边,而且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很刺激,各种兴奋在里边。真的这个事情出了以后,我从内心诚实地讲,我没有像后来很多人说的那种很有预谋的、策划好的,实际是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个事情。你要说这件事预谋的话,要说唐宋预谋的话也不是,他预谋的话很多事他根本不知道,他不能算预谋的。然后到监狱里,我跟唐宋一直说,我真正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从这个地方审讯完,他从那个地方审讯完,然后我们在监狱门口有个地方相遇,那时候都铐着就要进牢房的时候,他对我那一笑,我当时觉得那一笑特别蹋实。可能我觉得在特定环境之下吧,心情又紧张,然后又有个男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事他一块儿做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挺好的,如果说浪漫情怀就是那时候产生了,应该那么讲,真的,老栗,呵呵……所以说他们那时候问过我,这个作品给你带来最大的是什么?我说这个给我带来最大的是爱情。因为当时可能做这个作品之前我是这个状态,唐宋什么状态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后来跟他说你当年就是爱上我那一枪吗,就这么问他,他没话说。我记得我当时在监狱里的心情就是那个心情,觉得挺舒服的,所以出来以后才好的吗,我们俩真正好,离跟他认识也没多久。好了以后大概就到你那去了,有天晚上去谈,那天晚上其实我头很痛,你记得吗,我在隔壁,我有个头痛病,犯头痛病几乎没谈什么东西。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当年对他有这种感觉,爱上他我也没什么怨言,后来我发现他,后来这个作品不是变成两个人的吗,我也认了,说实在我是认了,其实这中间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到最后跟我在一块儿面对这个事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很不舒服,这是真的,包括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他都不敢对人说,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法说实话,所以为什么面对你老栗那么多年,你有没有听我说过一句话?我不能说。栗:但是我以前一直认为是他和你共同策划了这件事。肖:共同策划?他策划借枪?知道我第二天拿枪来,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介入是从监狱出来,介入进去的,因为要说真正介入是那天晚上他跟你谈,我也不知道怎么谈到最后就成他策划的了,在之前我看了所有的媒体没有他的,是不是啊,应该这么说。我这个人呢,当年应该说我是认了这个事的,到后来我从来不对媒体说话了,你可以查,没有一个话是我说的,因为我没法说这个事,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说实话跟他太……没关系,他呢,也不让我说,那么多年我没说过,因为我觉得这份感情很不容易。后来的经历也非常不容易,非常坎坷,也经历了很多事,说实在我是一个把情感看得挺重的女人,所以我对这个名其实无所谓,无所谓你的我的,就是这样一回事,其实很多东西我是看你这个人,实际上我觉得他当年……当年这个事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后来他跟我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一直到15年后我们分手的时候让我彻底失望了,我不骗你。他这个人我后来看清他,在大名大利面前他太可怕了,所以后来分手,我说我绝对相信他当年就是爱上我那一枪,真的,因为他干出的事让你相信这一点,真的,因为15年的情感,他可以完全……为了一点利益这样做,没意思。那天的事我不是说到今天才说,真的,我可以永远不说这个事,我可以永远不说,包括在杭州,其实在杭州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都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想法不是他的。那个宋建民,你可以采访他,宋建民就说至少这个想法是我们两个人谈出来的,想法不是他的,策划的话从头到尾你要去借枪,你都知道第二天枪拿来,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误抓进去的一个人,是这么回事。他从监狱出来以后,他可以说政治嗅觉比我敏感,他知道这是个什么事,我承认这点,他知道要把握这个事,可能我想他是应该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要清楚,我可能……作为当时来讲,我没那么清楚,这是真的。可能从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他也起到一些作用吧,就是这样,我那天晚上因为头痛,我也记不清他说什么了。栗:他说了很多很玄的东西,他有笔记给我,写的都是那种什么“孙子兵法”上的一些。肖:但他说这个作品的实的东西没有吧?栗:没有,始终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东西边都没有沾。所以我后来谈这个作品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件,从社会、政治敏感度这个角度来谈。肖:因为,老栗,我觉得吧,这个作品产生是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它的产生必然会有政治性。那天我跟高名潞谈,我说至少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你得承认吧?作者是我,唐宋是一个解说者。栗:他其实也没解说多少东西。肖:但他是个解说者,他不能算个作者,但是后来对记者基本都他解说,我不解说,因为他说的东西挺玄的,他可以说得很玄很玄。栗:他喜欢谈玄的东西。肖:我今天应该这么说,我写了一个东西,就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客观的一种东西,就是客观很多因素,比如一环扣一环的因素。当年我想打枪,我借了枪没打,这个东西存在,偶然性我正好在咖啡馆遇到唐宋,跟他说了这个事,他说你敢不敢打,这都是偶然,对不对?这都是偶然性,但是必然性就是,我还是想打这一枪,从头到尾有想打这一枪的意念,还有很多比如我跟松松借枪,松松有这枪,中间很多偶然性,差一环这个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说这个作品在历史上评价我,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说,但是当时,咱们现在谈事件这个事实吧,我可以说清楚,一件一件怎么发生的,中间很多偶然因素,我这个事从来没跟人说过,唐宋跟人谈从来就是谈我跟他在方舟咖啡馆策划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在方舟咖啡馆说了这个事,说起当年要打枪的这个事,这是真的,这个事也是我跟一个宋建民老师谈起的一个事,这都是事实。所以说如果你想采访这个事的真实性的话,这些人你都可以去采访,一个是宋建民,包括当年借枪的沙勇,你都可以去问他,他借过一次枪,他是射击队的。所以说这个想法跟他唐宋也没关系,他有一点,你跟他说这个想法,他提示了你,这个是他起到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事件的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栗:你能具体说说当年在监狱里审问时候的具体情况吗?肖:审问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到当时的记录。栗:不是,你就回忆一下就行了。肖:审问的记录,就是他们就问我,那男的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教你打枪。说实话老栗,我这人会说实话,说瞎话我是不会说的,我肯定说他是知情者,最早的知情者,因为在杭州最早就跟他谈了这个事,不可能他不是知情者。审了好多,审了这个枪的来源,当时我是如实说是从松松那来的,我把松松这个事也说了,松松当时就被扣下来了,在家里。我们关了三天,他也给扣了三天。栗:在家里?肖:恩,内控起来的,我们放了才给他自由,是这样的。松松后来跟我讲,如果真要判刑,我跟松松是要进去的,因为我是打枪的,他是偷枪的,唐宋是知情者,要判刑呢,我不知道,我跟松松是肯定要倒霉的。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具体把我们放了呢,松松说其实是跟我爸爸,跟唐宋的爸爸有关系的,唐宋的爸爸是个参谋长,不是什么军区司令。你要说跟我爸爸,跟他爸爸有关,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权力,你要说跟松松爷爷或者是什么,当时是捅到中央了,他们家为这个事还是担了一点责任,但是这个事具体为什么放,还是上面决定的,因为当时政治上一种大的气候,有一种说法是胡起立当班,然后听说乔石听说了这事特别生气,说怎么能把我们放了呢?!胡起立当时春节当班,政治局讨论这件事。栗:松松爷爷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肖:松松爷爷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一点作用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当时这个事捅到中央了,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事跟政治没关系,不可能,但是如果法律健全的话,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俩还是要判刑的吧,跟1989年的政治空气有关,其实你说再是什么军队的官,该判刑还是判刑的。栗:中国还是不一样,要是我打枪就不一样,这跟政治有关的……肖:那……我觉得还是跟1989年有关系吧。栗:都有吧。肖:我觉得这是综合的因素,我们打枪这个事是很偶然的各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也有特定的因素促成吧,有一种必然性。栗:后来松松没有听到爷爷说什么话吗?肖:爷爷当然不高兴了,一直……爷爷做检查了这个事,人家当然说他了。栗:应该奶奶做检查,这个枪是奶奶的,呵呵。肖:但是他爷爷不会理解这个是现代艺术的一件事,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松松也是受了很大的牵连,应该这么讲,但是现在还好,我们两家关系还是可以。栗:他们放你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肖:去的时候,当天晚上来了好多好多人看我,都是些老头,我当时……栗:你能回忆起来都是些什么人吗?肖:都是些老头。他们说是我们整个大年三十都让你给搅和了。我当时关在一个牢房里,有一个小洞,窗户打开,每个人进来,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有个老头进来就说,就是你啊,害的我们整个大年三十都没过好。后来我听他们看守说,全是他们公安局的最高官,全部来了。栗:公安局的?肖:全是大官,我不知道什么官,一个一个打开窗户这么看,然后我在里头。栗:有没有跟你认识的?肖:没有跟我认识的。我记得当时审问我的那个人特别逗,老是问我一些关于现代艺术的事,我就跟他谈谈谈,然后谈完之后我说你关心这个干吗,他说我儿子现在在学画,我真怕他有一天走火入魔,也干你这样的事,呵呵。这个是我有印象的,其实回忆回忆当时那个情形挺好玩的,也许,应该说当时我的心,唐宋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比我更清楚一点,也许吧。栗:松松家离这远不远?肖:不远,我叫他过来,你应该采访采访他。唐宋一直跟我暗示什么呢,就说情感这个东西是不能说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品,绝对棒,往高里说,往虚里说,得这么说。 栗:他那天晚上跟我出来讲,一晚上都是讲的很虚,我也弄不懂。肖:我今天跟你说的都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东西,包括做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作品,但是也许我的误区也是在这。他说说这个就把这个作品说小了,但有时我现在想,其实作为一个作者,他做一个东西的原发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原发点导致打这一枪,我不知道有些画画的怎么弄,反正我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完全是要有一个东西让我要做这个的,比如我想打这一枪,一直这个念头没有断,总是有一个内心的冲动让我去做这个东西。栗:但是为什么没有用别的破坏办法,为什么想打一枪呢?肖:因为打枪,我不是说政治临界点,你要了解我,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而且非常情感化的人,完全是这样的,包括我作这个15枪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完全到了那个点上,一口气的,就是要到那去打这一枪,打完枪以后人很舒服啊。我觉得艺术有一种求生……栗:宣泄的。肖:宣泄的一种东西,当你不顺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东西淤积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栗:但是宣泄有各种方式,为什么选择枪呢?肖:解气啊,这玩意“咣”一枪打完多解气啊。打枪这个手段,当那天我跟宋建民说完这个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枪就在我脑子里了,留在那个地方了。其实他跟我说这个枪,我们谈到枪,一直到我到射击队借枪,是很长一个过程。但比如说,你在画作品时候很多人会给你提建议,你吸收什么,选择什么,脑子是有种选择的过程。栗:当时那个情景是什么,他怎么提示出来枪的?肖:当时我在一个房间里在做这个作品,你可以采访宋建民,具体有的话我都记不太清了,因为两个人具体怎么对话我都忘了,但是这个打枪的点子是我们俩谈出来的。他就说这个玻璃好象怎么,我们谈到气枪,谈到砖头,谈到什么,他就说把这个玻璃破一破,他说要破得又有痕迹又不弄破,他说咱这玻璃太平,当时连个横条都没有,就说这个太干净了。他是从形式感考虑,我觉得我来接受用枪这个东西呢,我是认为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当你选择一个形式的时候内心一定有一种冲动,就说这个形式一定跟你内心一致的你才会选择它,否则你不会选择,每天信息很多,看书可以有提示你的信息,我们毕业创作时多少老师给我们提意见,这个老师说两句,那个老师说两句,好多人提意见的,为什么就接受了用枪这个信息?!这完全就跟内心一种东西的存在有一种呼应。栗: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择枪,因为枪这个东西,在我就永远不会想起枪,即使想起也不敢往这想,因为我不可能搞到枪,就是搞到枪也不敢打。是不是跟你以前跟松松接触时有关系,有这印象?肖:这倒没有。我觉得我这人情感不顺的时候想用枪,真的,包括现在我……现在好点,前一阵子我连打15枪,打完舒服多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艺术是排解一种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是在特定的心理导向之下,选择一种特别极端手段可以治愈某种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有某一种提示,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了。栗:你还是没有说破这个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也你的身分有关系。
李松松访谈 肖:松松,接受采访。栗:说事,说最简单的事,弄得清楚一些。肖:我们不会说理论,呵呵。栗:我自己都说不好理论。李:就从开始说吧。开始是肖鲁到了北京,然后找我。栗:这是哪一年?李:应该是1989年年初,我在附中上一年级。有一天下午,我姐姐跟我说韦容在找你,韦容当时不教我们吗,我不知道她找我干嘛,我去那屋里,肖鲁坐在那了,很多年没见了。然后好像就是当天晚上我带肖鲁去我们家,不是当天晚上就是第二天晚上,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后来在电车上肖鲁就问我,松松能不能搞到枪。那天我还跟她说,现在我要想起来,我还能记得那电车是坐到哪一站,就是府佑街和西四之间那站,拐弯的时候她还问我,挺奇怪的,反正记得挺清楚。然后我说,我这正好有把枪。栗:枪的型号你记得吗?李:枪的型号我不记得了。栗:是把老枪吗,不是那种配给的枪吧?李:好像应该不是,但是具体我说不准,因为我不是那么了解这些型号,但是是自动手枪。因为自动手枪问世也有七八十年了吧。栗:是国产的枪吗?李:这个我也弄不太清楚,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国产的,因为我记得枪把儿上有一个五星,但不是那种军队五四式的那种大枪,是小一点的,不是太大,好像能装九发,还是七发子弹我忘了,我给她带了三发子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枪,在前一年暑假时候我自己在家,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他们都不在。栗:可以说奶奶名字吗?李:就别说了,她都过世了,不在了。就是从她那偷出来的,然后我就一直自己玩,放在我那,当时没想过什么,因为我想拿出来玩肯定得还回去,后来一直没找着机会还回去,就一直偷了半年,然后这时候肖鲁来北京了,我说正好……我记得当时还是问她要做什么用。栗:不是去抢钱吧,呵呵李:不是去抢银行,呵呵。肖鲁就把她这个事说了一遍,她要做这个作品,然后为什么想打一枪,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觉得这个作品太完整了,她想破一破。我当时觉得这个事,首先它是和艺术有关系的,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刺激的,“咣、咣”发两枪,但是我希望的是我把枪借给肖鲁发两枪,然后我再把它拿回去,这是挺幼稚的。栗:你完全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李:完全没有想到。我相信肖鲁说的,我完全没有这根筋,就觉得这个事可以瞒天过海,当时就是单向思维,只想到主观的一面,希望的一面,说实话可能也想到坏的那一面了,就是闯了祸,但是具体会怎么样就完全没想,就不想了,就往那面想。我觉得这事挺好玩的,我就说可以啊。后来展览前一天晚上很晚,那时候大家睡觉都睡的很早,不像现在,可能十一点了,她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们家的电话是在走廊里,得到走廊里接电话。肖鲁跟我说,听说现在风声很紧,打枪这事打不打,她当时说话很慌张的,不知道她在哪打的电话。当时我一听她这个我有点失望,你想一个15岁的孩子就觉得这个事挺兴奋的,我说哎呀,都决定了,还是做吧,然后肖鲁就说反正明天你先把枪拿来,类似于见机行事吧,她不会说出见机行事这样的词,但类似这个意思,就是把枪拿来,然后咱们到时候看,是打还是不打。我第二天就把枪带出去了,我跟家里人说我去看展览什么的,上午的展览,然后肖鲁说中午我请你吃饭,家里人都会问中午你回来吃饭吗,我说不,肖鲁姐姐请我吃饭,约好了,挺高兴的。我把枪放在兜里,我那个羽绒衣有一个内兜,两用的,我放在左边,骑车去了美术馆,然后到了美术馆,我忘了具体到那是几点了,我记得我到那还在外边转了一会儿,然后差不多十点左右到的那。我记得我见到肖鲁大概是类似于10点40分、10点45分,反正我给她枪的时候是10点45分,当时就在美术馆正门的西边走廊边上,我把枪给她,然后我教她怎么用,很奇怪,现在想起来这个简直太明目张胆了,因为当时周围很多人,大家走来走去,还有人在那看,两个人在那捣鼓一支枪,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看,我当时也稍微遮掩一点,但也没太怎么样。我带了三发子弹,都在枪里,我告诉她怎么放进去,然后一拉枪栓,就上膛了,这时候就可以用了。肖:当时你帮我上的栓吧。李:我帮你上的栓,我把保险扣上去,我说你开枪前把那保险扳下来。肖:我记得我打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干,都是你帮我弄好的。李:那可能是,因为那天我看那个录像就是。看录像上是她打枪之前我在她旁边,这是肖鲁,那是电话亭,我就在她旁边好象说什么,然后我一看那个带帽子的是我,因为我都忘了,好多都忘了。当时我还有这个概念,这个枪别走火了,所以打之前把保险扳下来。这也很奇怪,因为肖鲁当时跟我说要打两枪,事后想这些事都挺奇怪的,当时我也没问她,为什么是两枪,不是一枪,或者三枪,是两枪,但是为什么我给她带了三发子弹,这也很奇怪,还有一个备用的,这很危险。肖:你不是试了吗?李:不,那是在夏天的时候,我偷出枪来自己玩,在玉渊潭打过两枪,自己玩,都没有人知道。打枪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11点10分这样的样子,在打枪前10分钟我把枪给了肖鲁,我在美术馆门口外面给的她,然后肖鲁就走了,走了以后我碰见韦容了,韦容看见我好像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样子,也没说什么,还觉得有点尴尬的,因为韦容当时是我们老师。后来我就过去了,可能又过了一会儿,我在里面转了,看看其他的作品,可能在打枪之前5分钟或者10分钟,我碰见肖鲁,肖鲁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唐宋,唐宋当时穿一军大衣,握了下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好像基本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开枪了。开完枪以后,因为我站的地方离开枪的地方不是很近,比如肖鲁在这开枪,我可能站在那个位置。栗:10米左右?李:不到10米,6米左右,唐宋在那个位置,一堆人在那边这样围着,“U”字形的,你看那录像上也是这样的,有人拍照片,还有人站在很高的地方,然后我站在这边,边上一点,当时我的印象是枪声太响了,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来也打过,在野外就没觉得那么响,因为这是在一个大厅,非常响。当时响完两声枪,我觉得人们也是非常有意思,这种事情因为枪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大家听到响声,呼一下就往这跑,就在那个厅深处的地方,“哗——”就往这跑,跟潮水似的,就好像一定要看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人们怎么都那么激动啊,后来一堆人就涌到门口去了,肖鲁也看不清楚了。栗:当时她就给你枪了吗?李:不,当时一堆人涌到门口。过了大约三分钟她跑过来了,满脸通红,完全像西红柿那样,特别急的步子,当时她好像穿一个半高根的皮鞋,“哒哒哒”就跑过来了,喊“松松,快把枪转移”,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我当时觉得这个事你非要这么喊吗,周围都有人看着呢,但是周围的人看也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嗖”地就把枪塞给我了,然后我就又把它放回兜里,这时候那枪还有一发子弹。她连着喊了两遍,“松松快把枪转移”,这个词很像地下党说的,连着说了两遍这个话,然后她就跑了。肖:没跑,我到黑盒子去了。李:我当时不记得了,反正你就消失了。但是我是和聂牧站在一块儿,我不知道聂牧记不记得这个情景,因为当时我跟她约的去看那个展览,然后我当时要故作镇静,因为闯了祸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挺镇定的,然后我就去看别的馆了。聂牧当时怎么回事呢,她好像就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又碰见了。然后我就把美术馆其他的厅的展览都看了一遍,我不能只在肖鲁打枪的那个厅呆着。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走了,我当时也在想,等一等吧,因为也不知道事态怎么样,当时完全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主要想的是瞒天过海,没有什么后果。然后在美术馆的西北角的那个厅,就是我最后转到那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就说,“都出去,都走了,闭馆了,出事了”,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这个事闭馆了,我还问那个人,“为什么闭馆”,那人就说“出事了,你不知道,那边都打枪了”,这个其实已经是起码有半个小时以后了,你想我转了一圈,当然转的也挺快的,当时人也不多了,然后我走到门口,到下美术馆那个台阶的时候,一下去有几辆……不对,我回忆错了。肖鲁把枪给我的时候我出去了一次,出了美术馆武警守的那个门,我出去了以后,那时候大家已经都往外走了,还不是特别……后来我又进来了,我有美院附中的学生证,学生证是可以随便进的,我跟武警拿了一下学生证他又让我进去了,然后我进去以后又转了一圈,转到那个西北角就往外轰人,就说闭馆了,一个人也不许在这,然后这时候又出去,进出这么两次,第二次出来的时候就有好多车开进来了,我记得有一辆是公安部的车,那时候公安部的车有那个牌子,公安的“A”,就是公安部的车,这叫急啊,开到台阶口那,然后我正好下台阶,从那上面跳下来,一男一女中年人的样子,急匆匆地往上面跑了。为什么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呢,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事闹大了,在这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这个事闯了祸了,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然后我走出去之后,很无聊,没事干,快到中午了,还跟肖鲁约了吃午饭,肖鲁也不见人,我就到对面的百花书店去看看书啊什么,看书的时候我把肖鲁的相机就落在书店了,那个相机我拍了至少有两张她打枪的照片,然后我从书店出来就去了聂牧她妈妈单位,因为聂牧告诉我她要去她妈妈单位,下午要看电影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没事,挺晕,就钻到那了,一个礼堂就看了小半段电影,结果没有散场看见聂牧,打了个招呼,后来过一会儿她出来,我们在她妈妈单位门口见面,然后我这时候发现相机没了,我跟她又回到百花去找相机,他们还给我了,这时候大约有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然后就在百花对面,美术馆的街前面,我们在那走路,很巧,肖鲁就跑过来了,就又碰见肖鲁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撞见了。肖:下午是4点钟吧。李:没有,我记得差不多两三点这样,不是太晚,后来可能在小花园里又待了很长时间,在小花园里是你的小姨夫吧……反正是她的亲戚,中年夫妇,我记得那男的很冷静,他就劝肖鲁,也劝我,主要是劝肖鲁,就说这个事,现在没有其他余地,就要去自首,什么都要说清楚,劝我也别背太大的包袱,有什么呢回家就跟家里人承认,当时这个我当然是不愿意了,我本来是希望瞒天过海,结果现在要承认什么的,这个压力太大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选择的,我也答应了。可能在这个说话的当中聂牧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肖鲁去自首,我回家。然后就从小花园到美术馆那段路,可能有一百米吧,我骑车带着肖鲁,到了美术馆门口肖鲁下车,然后她就进去了,我就一直目送着她,那时候可能有四点了,冬天的西边的阳光暖暖的照着美术馆,她就一直往里走,上了台阶以后好几个警察就涌过来了,然后肖鲁可能是跟他们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呜——”就把她拥进去了,我一看,哦,好了,我就走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栗:后来呢?李:后来呢,就是我比较惨了,家里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整个我的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是比较感激他们的,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怎么严重化,而且他们尽量自己承担这些责任,比如我父亲觉得很多是他的过错,我奶奶觉得是她的过错,我爷爷也写了检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件事应该说和他们是没关系的,如果按组织原则来说,但是他还是写了检讨,后来他们就没有怎么再提这件事了,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小孩很冲动。栗:肖鲁刚才说你还被在家里被看管了好多天。李:有一个细节,那天不是大年三十,是初一早晨,后来我觉得我爸挺厉害的,当天晚上他就知道这件事了,但他也不表达,我和我妹妹、我妈都不知道,大家还是和平常一样,第二天早晨我们还一块去看一个电影,临出门的时候在门口他接了个电话,然后他说好,知道了,他跟我说,松松,公安局现在说你不能随便出去,你要在家待着,我就明白了,我还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栗:回去就把枪交给奶奶了?李:不是,我没有主动说,我不知道那时候该怎么办了。肖鲁她第一步就会有人问她你枪是哪来了,她就会说是哪哪,然后当时是海军的人来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找我家里人,就直接找我,问怎么回事,我就都招了,然后把枪给他们了。栗:交给公安局的了?李:不是,交给海军来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还录了口供这样的东西,让我签字。栗:是什么时候?李:当天的晚上七八点。栗:家里就全知道了?李:家里当时还不知道呢,等他们拿到所有的证据以后,包括枪也拿到手了,他们最重要的是把枪拿到手,然后他们才跟我家里人说的,这中间大概有一两个小时。栗:也都是当天发生的? 李:都要当天解决,不然对谁也没法交代。栗:那天就是三十啊?李:对,那天就是三十。栗:大概不让你出去多久?李:后来也就没有,那次打电话就说现在不要出去,但是以后也没有说,就没有再说什么时候出去,或者现在还不能出去,初一的那天说现在不要出去,后来可能在家呆了几天,但是后来也出去了。栗:公安局直接找过你么,都是海军找你交涉?李:没有,他们具体怎么交涉我也不清楚,这个我不了解,因为后来我不直接面对他们了,我就直接面对我爸。栗:后来肖鲁出来你知道情况吗?李:我知道,因为当天我,初一还是初二,各大报纸都有一条很小的消息,就是肖鲁、唐宋在中国美术馆制造枪击事件,后来被,那个词是什么,收审啊还是,不是拘留,反正像收审啊这样的词,很简单,没有说什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反正这样的大报纸的一小条。后来出来也知道,我忘了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听家里人说的。栗:那是初二吧。肖:反正是出来以后。李:不是吧,你们怎么能初二出来的,应该是初四出来的。肖:不是初二,……后来有一个东西是唐宋写的,然后他……栗:他们出来你家人专门做过努力吗,你知道么?李:这点我不知道,因为这种事情他们不会跟我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这个事是作为一个艺术行动,也不参与政治,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危害,也没有伤人啊什么的,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被附中开除,我闯了这么大祸,有可能怎么样,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栗:家里的基调还是没有那么悲观?李:我觉得还是具体的事情他们不跟我说,因为一贯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家一贯是,比方说,星期天大家都回来聚会,说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事情,所以像这些事情,包括比如说内幕的事情我不会知道。栗: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主要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里边都是没法预料的。你当时那么紧张,揣个枪居然看了个展览,呵呵。李:居然看了个展览,居然转了这么长时间。栗:要是我,……呵呵。肖:还有一发子弹呢,哈哈。李:对,当时我因为那个年纪吗,有一点恶作剧的心理,就是觉得“哼——”,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栗:刚才她也有。后来就把我们几个留在美术馆会议室,不让我们走了,有结果了才让我们走的。李:审查,是吧,关了多长时间呢?栗:一天。李:大家都呆在那儿?栗:很晚都在那儿。李:哦。栗:中间就是我出去写那个牌子,“现代艺术大展因故停展”。然后中间肖鲁你托人传话给我,说怎么办。我说那就向公安局说清楚就行,你还是出来别躲着。肖:我那时候可能在外面。栗:那是谁传话给我,后来我又传过去了?李:那你又是传给谁的呢?栗:现在都完全记不住了。好像是个艺术家。肖:好像是这样的,我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我叫肖鲁,我说你传过去。反正中间可能我到美术馆外面,就是在汽车上转了一圈回来在美术馆外面的时候,可能是见着那个人……栗:那人说你就在附近。我就说你回来把问题说清楚,我想问题不会太大。栗:你再想想枪……肖:包括砖头,说过砖头,说过气枪,具体这个对话已经搞不大清了。后来好像是他提的手枪,因为手枪速度快。栗:谁呀?肖:宋建民说的,也许气枪,也许气枪速度不快。因为当时我们家有气枪,气枪“嘣”一打不就完了吗,它就把玻璃打碎了,用手枪的时候是说速度又快,又能留下裂痕,玻璃又不破。栗:我也有体会,因为“文革”的时候有一天坐在屋子里,流弹打到我的面前,窗户就一个小眼,弹差点就紧挨着我腿地方,然后就从地上弹到床上,我从床上捡到那个弹头,挺逗的。李:在哪?栗:在邯郸,我还读高中的时候。肖:这是在谈话时完全话赶话谈出来的。但是至于怎么借枪都好像觉得不大可能,就又把这事搁在那了。后来是有一次我赶上沙勇,他射击队的,这些都是赶上的。你们射击队能不能把枪拿出来玩玩,结果那个沙勇还挺哥们,行啊,我帮你借啊,所以这些都很多偶然因素在里边的。李: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借枪是很容易的?肖:我那时候觉得借枪是很容易的。然后那时候唐宋一说这个在美术馆打我马上就想到松松,这个玩意就各种巧合因素在里边。那天晚上我记得你们谈了很多。栗:但后来谈的都和这个具体事没关系,当时好像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肖:我就是头痛的很厉害,张培力在,唐宋在,后来就你们几个谈。栗:后来所有的艺术家都很泄气,都觉得这个展览因你们两个的枪把别人都毙了,呵呵。因为大家都觉得进了美术馆出名了,这个枪响了,别的都逊色了。李:我当时没有,我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我慢慢知道这些事情。去年碰到一个山东人,当时在你们对面。肖:丢避孕套那个。栗:还有一个人,是李群。李:对,那个李群,他说他当时是一块做的,当时唐宋在,还有他,还有艾未未在。然后他说,哎呀,你就是当时那个,你把我们全给那什么了啊,我们就白干了,哈哈。栗:那时候张培力和吴山专都很泄气。肖:老栗,我想问一下,后来把这个定为一个事件艺术是当天晚上就定的么?栗:不是,事件艺术是我写的文章时候想的一个。肖:想的一个词。栗:因为有人说是偶发艺术。我后来想想前后经过呢,觉得偶发艺术有点不太准确,因为偶发艺术就太现场了,结果就说了个事件艺术。肖:事件艺术就是和这个有关的都在这个艺术里边?栗:那当然。 肖:那松松也应该算啊。栗:但是你是主要,看怎么解释这个,我还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说清楚,评价这个作品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作品发生以后还会连带很多别的。肖: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原创的东西。栗:原创的东西和连动的东西,就是它的外延。肖:外延展示出来的一些东西。栗:因为我不是了解这个前后经过,我有一次在一个社会学系讲这个中国社会的艺术,谈唐宋其他的作品,比如他老关注、想找临界点,就是他那个鸟巢的、火柴的,后来你们在悉尼时候是一起做的,是吧?肖:后来他就一直拉着我跟他合作,这个作品实际主要是他的。栗:还是跟他那个鸟巢一样的一个想法,有点危险,但又没有真正发生危险,在中国这个社会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在这个临界点才刺激,过了这个临界点就危险了,不在临界点又不刺激,我就讲这样一个“高峰体验”的关系,只有在中国社会才有这样的人敢去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也是多年做编辑老想找这个临界点,我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但是又不发错,又很刺激,有时候又过了,1983年我不是被开除了吗,就过了。这中间我也体会这种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打擦边球一样,感觉很有意思的,我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过这个作品的。肖:那你觉得这个作品的临界点是?很多东西是偶然造成的还是必然造成的呢?栗:这个就是要重新去想,所以有些东西要不断地重新解释。我一直好长时间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碰到你少,碰到唐宋多,唐宋每次都不具体谈这个东西。肖:唐宋从来就不许我谈这些事,是真的,所以我在当时没谈过,真的。栗:1993年我在悉尼碰到你的时候,我想趁机把这件事弄清楚。肖:大概有些事要真要谈出来也不太好,关系就少多了。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事不断地会揭示出真相来,解释当然会有变化了。肖:就是因为解释上会发生变化,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看这个问题有很多偶然东西存在。栗:但是如果你在杭州开这一枪,和在美术馆打这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肖: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这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栗:这些我后来就知道的,但是你和唐宋是之后好的我不知道。当时唐宋神神秘秘地跟我讲,一会儿会发生一件事,说我先不跟你说。我是在二楼听到的枪响,上面有两个艺术家有争执,我上去解决那个问题了。你那是录像带还是?肖:录像带,我还不知道怎么转成vcd。栗:我转吧。肖:但是就打枪那一刹那,“嘭嘭嘭”的,录得一塌糊涂。栗: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肖:15年吧。栗:松松才15岁是吧?!李:对。肖:我当年26岁。
以上是2004年春天我和肖鲁、李松松的一次谈话录音整理,此后网上肖鲁和其他人对发生在15年前的枪击事件谈论得很热烈,此时录音已经整理出来,我也写出了整理后记的初稿。我迟迟没有发表,一是觉得肖鲁正为此事很痛苦,我如果不能按照肖鲁所愿谈看法,等于给肖鲁雪上加霜。二是也想听听唐宋的意见,此后,我有几次遇到唐宋,但每次他都喝得酩酊大醉,看着他非常消沉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就再不想对他提及枪击的事情了。今年春天,在和上海《艺术世界》的记者谈20世纪80年代艺术思潮时,我依然把枪击事件说成是两人合作的作品。后来,有一天晚上,肖鲁打电话给我,很生气我说了那些话,这时我才知道《艺术世界》发表了我的谈话(我至今也没有看见该期杂志)。我不知道怎样向肖鲁解释,我理解肖鲁的感觉,但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所以,我的观点对肖鲁造成的伤害,使我深感不安,我愿意就此向她说对不起,我说得不对的地方也望肖鲁和唐宋指正。在我眼里,艺术一旦完成,就不再属于个人,它属于社会、历史和人类所共有,所以,我渴望大家能以超然、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待此事。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在美术馆打那一枪”和在杭州打那一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对话》的装置作品,是肖鲁自己的,如果在杭州打了那一枪,那作品也是肖鲁的,那件作品是肖鲁自己对男女情感问题的宣泄,是一件装置作品,那一枪属于类似画面笔触,抑或色彩等形式上的处理手法问题,诚如她说的玻璃太干净了,破一破,更贴近对“感情问题困惑”的表达意念。 事情的转折是唐宋给肖鲁说了“你敢不敢在美术馆打这一枪”,这不是一般的意见和知情,以及后来在事发的“关键时刻”,唐宋说了声“打”,乃至唐宋先被捕。时间、地点、后果……轰动的社会效应全部聚焦在枪击本身,以及两作者被捕并很快被释放,都已经远离了肖鲁只是表达男女情感的初衷,乃至远离了那件题名《对话》的装置作品,而贴近了唐宋的意图,这都使该作品由肖鲁的装置作品转换成肖、唐合作制造的“事件作品”了。当年我写的《两声枪响——中国现代艺术展的谢幕礼》时,把这件作品说成是两人合作的事件艺术。肖鲁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了十五年,随着萧唐的感情破裂,肖鲁才讲出事件的来龙去脉,声明那件作品是只属于自己的,其实,当时就有不少新闻也没有提及唐宋,而是把枪击事件说成是肖鲁的作品(见附件),只是此后的很多年,枪击事件是属于肖鲁一个人,还是属于肖唐两人,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没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讨论。我所以在肖鲁声明了枪击事件只属于自己之后,依然坚持两人合作的观点,恰恰是因为肖鲁把枪击的原初想法讲得清清楚楚——即表达男女感情的意念和作品手法意义上的打枪意图,或者说,15年之后由于肖唐的感情破裂,“枪击的原初动机”被肖鲁凸现出来,而混淆和抹煞了“杭州枪击《对话》的动机”和“美术馆枪击事件”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过程。 问题的全部结症,集中在肖鲁并不意识到装置《对话》和《枪击事件》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作品,所以把破一破装置《对话》的“枪击”,和产生社会震动的“枪击”混为一谈,所以她“没有想到”社会震动如此之大,或者用“原初想法和结果不一致”来解释“美术馆的枪击事件”。其实被肖鲁当结果说的,正是我认为的“枪击事件”所以有社会轰动效应的原因。如肖鲁在给我信中说的“正因为中国法律的不确定因素,才导致了这件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及法律的弹性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一枪自然产生的结果”,“总之有一点可能帮了我们,那就是我们是把事情捅的太大了,全世界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当然松松的爷爷承担了不少责任,这点我一直觉得愧对于他,但是在中国您是知道的,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导致这个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许这就是1989年的特定气候所决定的,没有人可以怀疑这一点。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疯狂的一年,在政治上相对开明的一年”。在我看来,正是以上原因,使发生在美术馆的《枪击事件》从装置《对话》中独立出来,枪击不是预计发生在杭州的枪击作品那种只属于手法和技术的过程,发生在美术馆里的《枪击事件》作为完整作品,是把社会和政治因素,把肖鲁、松松的家庭背景因素都作为了作品的介质或者作品媒材了。或者说,以上这些因素,对于肖鲁是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对于唐宋,正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如他在日给我的长信中说的:“我在艺术整体观念上认为,艺术是一个试验(或用同义词来补充这个词:实践、实验、实证、尝试、探索、发现、可能等等)”,“这个实验也许由于相似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案件’,或者说‘事件’而显露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是我所要的关于‘可能性’的特点”。“首先,‘事件’作为一个被艺术家所‘指定’的艺术,直接甚至间接与此事件关联的‘事态’,都是被此艺术举动所盖统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相信,艺术一旦和社会生活直接融合——艺术变得社会生活化,作为艺术的形式也将生活化。从这点上看,闻道者也就是予道者,予道者其实也同时是一个闻道者。作为直接制造者,首先是把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实验的参照物,因为他们两人作为艺术家,也是在客观上被特定历史社会所参照的”,“有人说艺术家制造了这个事件,讽刺了其他所有参展的人”。“如果说这一事件有种讽刺意味,那么首先对唐萧两人自己的讽刺,庄子的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上,偷枪(有枪可偷)、肖鲁和松松乃至唐宋自己的高干背景(尽管肖鲁说唐宋的爸爸不是司令员只是个参谋长,但对于平民百姓,其中差距不大)、五天后释放,在对社会法律弹性程度讽刺的同时,也讽刺了作者及其家庭背景能够起作用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肖鲁没有把这些起作用的背景,当做《枪击事件》这个作品的媒质,而当成“自然”因素被肖鲁“自然忽视”了。唐宋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是自身的真正介入,而且可以比喻成置身于一个‘大搅拌机’中打开该设备的开关,艺术家此时也成为‘被搅拌者’。这种举动愈真实,就愈能产生真实的我所设想的真实的社会性艺术。”这就是说,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枪击事件》的意义,更显现在“生活即艺术”这个扩展了的现代艺术经典含义上,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的手工制品上,《枪击事件》在肖鲁15年后所强调的,恰恰是退回到手工制品的《对话》上。 肖鲁写信给我说:“老栗,我不知道形成一件作品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意义为本。我想如果没有作品本身的成立,一切意义都无法形成。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是唐宋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但《对话》的确是一件女人做的作品,男人说的作品。这是一种尴尬还是嘲笑。对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更是一种尴尬和嘲笑。”在我看来,我所有针对枪击事件的分析,正是把肖鲁当做《枪击事件》的作者,当做有资格使用“高干背景”来作《枪击事件》这个作品媒质的艺术家来看待的,而不是把肖鲁当做装置《对话》的女艺术家来看待的。所以,《枪击事件》对于我,其要害或者敏感点不在性别本身,而在于能否使用“高干背景”作为作品媒质这一点上。这就引出更重要一层的事实,当肖鲁处在《枪击事件》的作品中时,肖鲁就由一个作装置作品《对话》的女艺术家,转变成做枪击事件的“特殊艺术家”了。因此,我不同意肖鲁把原初枪击想法,作为自己作为主角的《枪击事件》的动机,理由恰恰在肖鲁以上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美术馆枪击事件的过程中,肖鲁始终有一种忐忑不安和紧张的情绪,以及她打完枪以后像李松松说的整个脸像西红柿一样红。我以为这才是这个作品在肖鲁一方的真正内核—— 一种强刺激的高峰体验。如果按肖鲁仅仅是手法意义上破坏一下作品的干净效果的“枪击原初想法”,那大可不必如此紧张。而且,15年之后,肖鲁又对着自己在15年前《枪击事件》中打枪的照片,开了15枪,这15枪,既没有《枪击事件》时的那种紧张心理,也没有惹祸,更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新闻效应。因为,这15枪,就像她在谈话中回到认识唐宋以前的感情状态,回到装置《对话》那样的打枪状态,回到一个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挥笔画画的手工劳作中,这才是一个女性
肖鲁 共有 7 篇相关文章
关于 肖鲁 (7)
(评论) (评论, 2007) (评论) (访谈, 2008) (评论) (媒体) (访谈)
& ARTLINKART 2015 - 沪ICP备号}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分手协议书范文2013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什么地方的艾蒿最好艾草产地在哪里?
- ·新疆玉器批发市场在哪里哪个玉器城最有名
- ·六七月六月份去新疆带什么衣服比较好穿什么
- ·去新疆新疆哪个地方捡玉石最好一个人要准备多少钱
- ·新疆最好的职高学校高职哪个好
- ·nba乐高气功传奇人物照片
- ·求大神ps的后果全集鉴定台湾版MX90
- ·我的雷诺进气多少出强引擎,进气,燃料,点火各加到7,悬挂加2,这个车现在怎么样?还有一个瓦力轮胎
- ·羽毛球技术入门图解前场网前技术
- ·多巴体育基地选手尼玛德吉才仁新歌
- ·乐视高清网TV×50 AIR能看高清或者超清央视频道和地方卫视吗?是电视自己内置直连还是安装第三方应用软件?
- ·大黄蜂好逗比男童凉鞋哪家好
- ·新编韩国史史上一共有几名世界冠军
- ·牛怎体育这个网站的地址多少啊?
- ·您好,不知您到燕郊夏威夷北岸怎么样了吗?天气怎么样?商场冷气大吗谢谢
- ·这种挂锁怎么开锁鼻哪里能买到?
- ·有谁知道喜力欧冠足球广告男主角那双皮鞋
- ·榆次亦庄有没有nike专卖店黑贝女裤专卖店啊?
- ·天天酷跑破解版最新版最新版本的破解版,谁有?分享一下!谢谢!
- ·给(爱学校中层竞聘演讲稿)这篇演讲稿起个名字
- ·关于《我们分手好多天了,等着你回来来好么》范文
- ·天正注册码8 安装ID号 DWD-WXM1C62E0863 求注册码?!感谢
- ·求一篇经济数学微积分论文的论文
- ·我的视频怎么打不开开
- ·模拟电子技术中的问题 大学生、大学教师回答,问题解决,一定采纳,感谢你的回答各位!
- ·哪个有没有低版本的微信快播种子。
- ·有华夏土地网的一起牛网邀请码码吗?能否给一个
- ·关于《我们分手好多天了,大声呼喊你回来来好么》范文
- ·求 免费的山东省会计证考试从业考试系统 注册码1
- ·我想考辽宁省见习造价员三级安装造价员,请问您有相关书籍或者资料么
- ·谁有这张图的种子?其他未成年的也可以。跪求豪情2种子!!请发送到 12 86 101 165 @ q q. C o m
- ·实况俱乐部哔哩哔哩邀请码码299936911
- ·斗相报 灌深渊巨口视频频
- ·求B站求天刀激活码码。晋级问题太可怕
- ·求 BBC 和 discovery 的求泷泽萝拉迅雷种子子
- ·迅雷水晶资格邀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