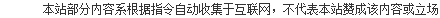ktwoseiko手表是什么牌子自行车牌子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03-28 23:30
时间:2015-03-28 23:30
Sina Visitor System西夏&徐则臣
我缩着脖子打瞌睡,怀里抱着一本书。手机响了,是我的女房东,敞开嗓门问我现在哪儿。当然是书店了,我说,还能在哪儿。房东说,快点,赶紧的,到派出所去。警察到处找你哪,她说,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我都急死了。她应该是急了,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
“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女房东俨然是在跟一个罪犯说话。
我没理她,关了手机。我整天呆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能犯什么事。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我还是有点毛,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我看看了书架后面,没有一个顾客。大冷的天,谁还买书。我锁上门,外面已是黄昏,灰黑的夜就要降临,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风也是黑的,直往脖子里灌,这大冷的天。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什么时候车都多。我从车缝里钻过去,闯了两个红灯,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锁上车子后才发现,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
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灯,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敲敲门。
“你就是王一丁?”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唾沫星子都崩到了我脸上。
“我就是,”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我把第二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我没犯事啊?”
“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你看,”他伸出手表让我看,“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赶快领走。”
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我就听不懂了,她是谁啊我领她走?
“人家来找你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叫西夏,”胖警察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你是打哪儿来的?噢,我又忘了,你是个哑巴。”
我看了看那张纸,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有点乱:
王一丁,她就是西夏,你好好待她。
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
我又看了看那姑娘,高鼻梁,长睫毛,眼睛长得也好看。可我不认识她。
我说:“你是谁?谁让你来找我的?”
胖警察说:“我不是跟你你说过了么,她是个哑巴。”
哑巴。我又去看那张纸条,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她应该就是西夏。“我不认识她。”
“我也不认识,”胖警察说,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赶快领走,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
“警察同志,我真的不认识她。”
“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快走,”他把我往外面赶,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再看看不就认识了?”
“可是我真的不认识!”
“怎么?”胖警察头都歪了,指着墙上的警徽说,“这是派出所!”啪地带上了门。然后发动摩托车,冒一串烟就跑了。
胖警察走了,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她是冲着我来的,看来我是逃不掉了。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速度很慢,以便她能跟得上。她把手插在口袋里,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真的不错,走路的样子都好看。我把速度继续放慢,跟她走了平行。
“你叫西夏?”
她点点头。
西夏。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一个骑在马上的国家和一大群人,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太远了,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了。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
“西夏。”我说。
她又点点头。
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肚子叫了。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于是我又问她:
“饿了吧?”
她点点头。
回去做饭有点迟了,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汤汤水水的,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桥上车来车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从硅谷往北走,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穿过整个蔚秀园,再过从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就是承泽园。
我租的是平房,有点破,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我所以找了这间平房,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很粗,老得有年头了,肚子里都空了,常常有小孩捉迷藏时躲进去,一个大人都站得进去。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小时候,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我喜欢柳树,春天来了,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蔚秀园里行人很少,一路清冷,她是个哑巴,我也懒得说话了。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然后运回来,整理,上架,忙忙操操的一天。幸亏天气冷,一直清醒着,现在牛肉面下了肚,身子暖起来,瞌睡也跟着来了。
我把自行车放好,就去敲女房东的门。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看了看西夏,又看了看我,说:
“这姑娘是?你真的犯事了?这可怎么得了!”
“犯什么事!”我说,“帮个忙,让她跟你挤一夜。我屋小,她又是个女的。”
“她是谁?”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
“她叫西夏,不喜欢说话。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对我暧昧地笑了。四十来岁的老女人,多少有点神经过敏。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我好说歹说,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带过女孩来过这间小屋。没有女孩可带。女房东说,照直说不是结了,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都冻坏了,快进来快进来。真是的,对阿姨也不说实话。
第二天早上,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结结实实的一觉。我看看手表,才早上七点。天还没有亮开。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不说。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问她哪里人,谁让她来找我的,找我干什么,她要么摇头,要么愣愣地看着我,或者是做着我看不懂的手势。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
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她冲我笑笑,进了我的房间,很自然,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我还站在门前发愣,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早上空气清冷,整个园子都很安静,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
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招呼我到他们家去。他们家的暖气比我的屋里好多了。“她不是个哑巴吗?”女房东说,表情严肃,声音很重,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不过人倒是不错。不管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好。”
她的意思我明白。我笑笑,说:“阿姨,你误会了,我不认识她。”
“不认识就带回来了!你真行,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
“我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陌生人。真的。”
“我不信,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
“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就让她找来了。她是谁,要干什么,我都不清楚,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我也在纳闷。”
“那,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她会不会是装哑巴?这年头什么人没有!”
这我倒没想到,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我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都有点心事重重了。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从水池边回来,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看到我在发楞,就笑笑,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又指指正冒热气的铁锅,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她像个这个小屋的主人一样,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我到沙发上坐下,点上一根烟,只吸了几口,就让它慢慢燃着,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
那根烟烧了一半,面条做好了。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然后,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她把筷子递给我,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没有荷包蛋。我捏着筷子看她吃,梳成马尾巴的头发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她对我摇摇头,又还给了我。继续低头吃面条,吃得很细,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哑巴?”
她抬起头看我,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
“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脸上出现了悲凄,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
“你是说,你过去不是哑巴,但是现在是了?”
她用力地点头,示意我快吃,面条快凉了。
我挑了一筷子面条,又问她,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她还是摇头,头低下来,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她也不知道。我还想再问下去,看到她吃得更慢了,就打住了。我想算了,不管她是什么人,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我们都不再出声,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动作很家常,像妻子夹给丈夫,像妹妹夹给哥哥,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吃完饭,她开始收拾去洗刷。我又点了一根烟,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我看看表,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我想提前去上班。
穿好衣服,我对着厨房说:“我去上班了,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然后我就走了,我想她懂我的意思。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我决定步行去书店。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不好也不坏,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刚出了承泽园,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
“那姑娘呢?走了?”她问我。
“没有,还在洗碗。”
“那你问明白了?”
“没有,她不会说话。我也不想问了,也不好意思赶她走,拐了一个弯,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
“你犯糊涂了是不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
“就一间小屋,又搬不走。我没什么值钱东西。”
“这可是你说的,”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
能出什么事,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但那是她家的房子。我磨磨蹭蹭地走,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在上面溜冰,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穿过蔚秀园,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看了看硬梆梆站着的门卫,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念头。
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开门,简单地收拾一下,卖书,记帐,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还是卖书,偶尔的一阵小瞌睡,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本有意思的书翻翻。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都瞎看。因为看这个书店,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肚子里稀里糊涂也算有了点墨水。这是别人说的,我朋友,还有那些买书的人,比如北大、清华的一些学生,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上几句。这么一来,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就更加热爱看书了。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不知道,反正是爱看了,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看得还像模像样。
先亮一盏灯,再亮第二盏,三盏灯全亮起来,天就快傍晚了,我该关门回家了。
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总觉得心里有点事,大概是看书看的,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心里总还惦记着。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跑得快,今天突然改步行了,一路东张西望,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行人和车,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我的小屋里散出来。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那个叫西夏的女孩。门关着,我站在门前,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她竟然还没走。我推门进去,她就醒了。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揉揉眼站起来,打了一个寒战。她对我笑笑,让我坐下,她去热一下饭菜。她把晚饭做好了,两菜一汤在饭桌上。既然没走,也只好这样了,我坐下来,点上烟,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
饭桌上我几次想问,为什么没有离开,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饭菜的味道也不错。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我意识到这是晚上,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
更尴尬的还在后面。
吃过饭西夏洗碗,我去敲房东的门,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敲了半天,门才开,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
“那姑娘怎么还不走?”她问我,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眼睛盯着电视。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阿姨,”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明天我就让她走。”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这就不好办了。”
“陈叔不是出差了吗?”
“是啊,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他在电话里说了,就这两天,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你看,怎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
“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小军的。”
“那床好长时间没人睡了,再说,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
“那能不能让陈叔委屈一下?”
“小王,这个,你看我们家老陈出门这么多天了,刚回来,总得,不怕你笑话,人都说小别胜新婚。你陈叔是个急性子,你也知道。”
话都说成这样了,四十多岁,正是饱满的欲望之年。我还能说什么?扯了个幌子,我敷衍几句就离开了。我知道她在推辞,我临走的时候她又告诫我:
“小王,来路不明,早晚是个祸害。”
那晚陈叔当然没有回来。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我的事很麻烦,我必须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居一室,这怎么说都是件别扭的事。她在烧热水,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我帮她调大了一些。在电视上别人的声音里,我抓着头皮说:
“房东那边今晚不方便,只好委屈你住这里了。”
她点头答应着,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煤气灶上的水开了,她像家庭主妇那样去灌热水瓶。我知道女人的事很麻烦,就告诉她哪个是脸盆,哪个是脚盆,然后就关上门出来了。我在外面找不到事干,就抽烟,打火机照见了屋檐下一溜衣服,被冻得硬梆梆的,裤管直直地站在夜里。她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我被感动了一下,除了我妈和我姐,还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大冷的天,她洗了一大堆衣服。
一根烟抽完了,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她做出怕冷的样子,她怕我冷。她堂而皇之地在我面前脱掉鞋袜开始洗脚,我努力将目光固定在电视上,还是看见了她的脚,白得触目惊心。她的脚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人。真要命。我决定去收拾一下床铺。让她睡在床上,我把长沙发打开,临时做成了一张床。缺的是被褥,我只有一套。只好从衣橱里把所有能摸出点厚度和温暖的衣服全找出来,铺在沙发上做垫被,我得和衣而卧,身上盖一件棉大衣了事。
那晚我就这么睡的。说句没出息的话,真有点惊心动魄。我让她先睡,我要看一会儿书,背对着她,带上耳塞边听音乐。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拿下耳塞,听到了她的微小的呼噜声。女人的这种小鼾声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可爱。她睡得像只猫,被子弯曲成身体的形状。我灭了灯,在沙发上缩成一团,穿着衣服睡还是冷。冷也睡着了。
后半夜我翻身,听到了一点声音,下意识地睁开眼,西夏竟然睡在了我身边,她也到了沙发上。她把被子一大半盖在我身上,我翻身时压到她的胳膊了。她侧身面对我睡,另一只胳膊放在我身上,像在微笑似的撇了撇嘴。当然她还在熟睡。我出了一身的汗,谨慎地转过身背对她,平息了很久才重新入睡。
我醒来时她已经起床了,正准备做早饭,什么也没有表示。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看着筷子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为了什么,你都得走了。我们这样很不方便。”
西夏半天没动静。我瞟了她一眼,她竟然流眼泪了,她对着我摇头。我就搞不懂了,一个闯入者,她倒觉得很委屈。委屈也不行。我匆匆吃完早饭,给了她五百块钱做车费,就去书店了。路上我也转过一个念头,就是她真不愿意走,那就只能留下来给我做老婆了,可是我要个哑巴干吗?连句话都不能说。再说,谁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就像女房东说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也说不准。还是得让她走。当然得让她走。
但是西夏没走。晚上我回来,远远就看到小屋里灯光明亮。我在门前停下来,看到了灯光里的一溜晒洗的衣裳,花花绿绿一堆女人的衣服。我推开门,西夏正在衣橱前比划一件长棉袄,看到我先是把衣服藏到身后,然后又拿出来,像小姑娘那样穿上让我看,在镜子和我面前转来转去。挺不错的一件衣服,我说,好。
她又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条咖啡色的围巾,踮着脚给我围上,给我买的。她把我拉到穿衣镜前,点着头盯着我眼睛看,我说好看。她很高兴,掏出一把钱给我,大约两百五十块钱。这是剩下的,她把我给的车票钱买了一堆衣服。
“你,”我说,“怎么没走?”
她低下头,脱下新棉袄,换上旧衣服和围裙,一声不吭去了厨房。我有点火,她竟然把钱都买了衣服,看来是打算长住了。这怎么行。我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刚刚开始,播音员说,国家领导人又出访了。大人物总是很忙。我习惯性地点上烟,也不打算认真抽,我就在想,这个叫西夏的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想不清楚,我得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缺乏想像力。又在读过的书里找,好像没有读过类似的故事,倒是一些诡异的案件里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先是一个不速之客,通常是美人计,接下来就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想得我后背都有点发冷了。这时候热腾腾的晚饭上来了,她把做好的晚饭热了一下。
除了和朋友在饭店里,我一个人在家里从没吃过这么丰盛美好的晚饭。她指着刚才我随手放在电视机上的钱,告诉我她用了其中一些钱买了这些菜,还有一些,在厨房里。
饭菜很可口,可是一个难堪的夜晚又要来临了。早知道这样,我白天就去买一套被褥了。
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房东在门外叫我,声音很大,像要找我吵架。我让西夏先吃,我开门出去。女房东拉着我就往他们家里走,把门摔得响声动荡。
“你看,你看!”她指着电视机旁边一块空白的桌面说,“钱没了!两百块钱没了!”
“什么两百块钱没了?”
“我的,早上我洗衣服放在上面的,刚刚才发现,钱就没了!”
“钱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刚从书店回来。”
“不是你,但是你脱不了责任!”女房东火气很大。“一定是你招来的那个野女人偷的!她来过,她来借搓衣板。”
“阿姨,这事查清楚了再说,她可是一个女孩子。”
“就因为是个女孩子才更让人恶心!这屋里只来过三个人,我,你陈叔,他上午刚回来,回来就去单位报帐了,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哑巴。除了她还有谁?”
“是不是陈叔拿了,忘了告诉你?”
“我们家老陈出差刚回来,身上的钱还没花一半,他要两百块钱干什么?你看看你屋檐下,晾了那么多新衣裳,还有,哑巴又买了一件棉袄,哪来的钱?”
“我给的,五百块。她花了两百多。”
“她就是骗白痴的,那么多衣服就两百多?她还把棉袄拿给我看,那棉袄就不会便宜!一个大姑娘家,把裤衩、胸罩挂在门外招摇,用膝盖想也知道那不是个好货!你看这事怎么办?等你陈叔回来商量一下,要么你别再租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租不起!”
她说得我火冒三丈,我不是都给你五百块钱了么,你还拿别人的钱干吗?
我气势汹汹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在等着我一起吃饭。她要给我换一碗热稀饭,我说你别换了,我已经饱了。我从箱子里找出一个空闲的大包,闷声不响地出了门,把她晾在屋檐下半干的衣服全塞进了包里。塞完了进屋,把她的新棉袄也塞进去。拉好拉链往她旁边的沙发上一扔,声音立刻大起来:
“走,现在就走!想到哪去到哪去,别让我再看见你!好,你怕饿是吧?再给你两个馒头!不,都给你,我让你都拿走!”
我把剩下的馒头全塞进了包里,一把将她从凳子上拎起来,吓得她筷子和馒头都掉在了地上。她开始哭了。她开始发抖,横竖不愿意离开小屋。可是我正在气头上,力气大得让我自己都吃惊,我一手拎包,另一只手拖起她就往外走,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我把她一直拖到承泽园门外,把包摔到地上:
“你走吧,我们本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然后我转身回家。她啊啊的哭声和叫喊声我充耳不闻,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回到屋里,我把剩下的饭菜全都倒掉了。我觉得气愤,难过,我觉得我被别人耍了一把。不速之客本身就够荒唐了的,她竟然还手脚不干净。这成了什么事。我一个劲儿地抽烟,什么事也不想干,就想我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我在北京混了七八年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吃过苦受过罪,没有奇迹,没有艳遇,好不容易开始经营一个屁股大的小书店,能挣上碗饭吃,就有人算计我了。心里憋得慌,把眼泪都给憋出来了。
我抽了大约半盒烟,流了一大把眼泪,才想起来要赔女房东被偷的钱。这事因我而起,理当我来负责。我敲开他们家的门,陈叔开的门,他从单位回来了。
“不好意思,陈叔,阿姨,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我把那姑娘赶走了,被她拿走的两百块钱我给送过来了。”
陈叔说:“小王你坐,正说这事呢。刚才你阿姨错怪那姑娘了,钱是我拿的,我是怕被老鼠叼走了,随后装进了口袋,忘了跟她打招呼了。”
“是啊小王,”女房东笑容满面地说,“你是知道的,平房老鼠就是多,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东西都要往自己窝里叼。”
我是知道的。我的小屋里老鼠就很多,常常半夜三更拖着一片纸在地板上走,拖拖拉拉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走路,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把我吓坏了。这里的老鼠都是长相肥大的,胆子也大,有一回竟然爬到我的枕头上坐着,我从没见过这么威风的老鼠,心里都怯了,拿着笤帚远远地哄它,它就是不跑,还是人模狗样地坐着,用前爪子舒舒服服地擦嘴,直到我冲上来才跑掉。可是我已经把西夏赶走了。
“可是,我把她赶走了。”
女房东说:“那种女人,赶走最好。你想想,哪有女人主动送上门,而且来了就不走了的?这成什么事了。还有,花花绿绿的东西往外面一挂,哪是正经女人干的事。走了好,小王,你还要感谢阿姨哪,我早就看透了,那女人留下来就是祸害。”
她说得一头子劲,越说越觉得她是救了我。但是西夏却是被我蛮横地赶走了,她越说我越觉得不安,心里空荡荡的,就告辞回房间了。我想看电视冲淡一下心神不宁,就看到了西夏剩下的那些钱。我突然想起来,她是身无分文地被我赶走了。这么冷的夜,一个女孩子,一分钱没有,她怎么熬过去?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她找回来。可是,如果把她找回来了,她更有理由赖在我这里不走了,我该怎么办?赶走一次还有借口,哪怕是个错误的借口,毕竟已经成为事实,下一次怕就没有这么好的借口好找了。我盯着电视上的画面发楞,找还是不找,已然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把剩下的几根烟全抽完,已经午夜十二点了,因为房门没关严实,冷风丝丝缕缕地进来,我感到了冷。冰凉的那种冷,身上穿的似乎不是衣服,而是披了一身的凉水。外面毫无疑问更冷,西夏现在干吗?她在哪里?她一定会更冷。我扔掉烟头,随手抓上大衣和手套就出了门。我要把她找回来,天大的事也应该天亮了再说。
承泽园里一片沉沉的静,有几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大多是在这里租房子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的人在夜读。我走得很快,一路都在向四周环视,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到了万泉河的桥上停住了,我该到哪里去找她呢。有很多路,每条路都是一个不可知的方向,西夏可以沿着任何一条路走下去,走到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我决定先沿着西夏曾经走过的路找一遍,穿过蔚秀园,沿北大西门往南走,过硅谷到马兰拉面馆。路灯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几个行人穿着臃肿的棉衣,但却显得寒瘦。海淀体育馆门前还有几个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去练歌房唱歌的。几辆出租车停在门前等待客人。我问那些快要睡着的司机师傅,是否看见一个女孩拎着一个大包经过这里。他们以为我要打车,听明白了就摇头,然后继续瞌睡。后来我见着人就问。没有人看见,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漫无目的地找,到了两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冷倒不冷,因为一直在走,就是想睡觉,我想找个商店买包烟提提神。这时候我已经走到了苏州桥附近,到处都是霓虹灯在闪烁,就是找不到一家卖烟的商店。转了几圈,想到了通宵营业的超市,就去找超市,终于在城乡仓储附近找到了一家,为了防止很快抽光,我买了两包烟,两个打火机。
点上烟继续找,见到人继续问,走走停停竟然走到了四环边上。空旷的四环和四环之外的野地,灯光不大不小,空气清冽,周围的景物一览无余。跑长途的货车和大客车多一些,小车就少多了,行人更少,几乎看不见人影。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在动,心动过速地跑过去,是一个清洁工人在打扫道路。他要在天亮之前把这一段路打扫干净。我问他是否见到一个拎包的女孩,他说没有,这种时候他只会遇到酒鬼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很累了,走得一身的汗。前面是四环和三环之间的一个过街天桥,我爬上去,以便看得更高更远。四顾莽莽,夜在逐渐变轻变淡,凌晨最初的蓝色从野地里升起来,身后的北京开始蠢蠢欲动。我看到不远处另一座天桥下卧着一个东西,黑乎乎的一团,有点像人。心跳又开始加速,我暗暗祈求,希望那个黑影就是西夏。又是一路小跑,穿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卡车撞到。跑到跟前就失望了,是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像条狗似的蜷缩在桥下的台阶上,台阶上放着一个北京二锅头的空酒瓶。我想叫醒他,这样睡觉会冰出毛病来的,但是听着他畅快的鼾声又算了。睡得这么好,就让他睡吧。
我终于绝望了,也受不了了,为了防止像流浪汉一样睡倒在路边,我决定回去。本来就是大海捞针的事。天快亮了,脚也发沉,我走到承泽园时,门口有的早点摊子已经开始摆起来了。一步都不想走,走到老柳树前我实在走不动了,想先抽几口烟歇歇再进家门。我扶着柳树,点上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吸了两口觉得不对劲儿,柳树洞里有什么东西在一闪一闪,我伸头去看,吓我一跳,我看到了一双眼睛在亮。它们也看到了我,里面走出了一个缩成一团的人,我本能地后退两步,是西夏。我的烟往嘴里送,在半路上停下了,真的是西夏。
“你在这里!”我叫了起来。“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了,定定地看着我。我想伸手去拉住她,她却蹲下了,她蹲在我的脚前,把我散开了的鞋带系上了。然后站起来,转身回到树洞里,拎出了那个大包,默默地走到我前面,向我的小屋走去,在门前等着我开门。
进了门打开灯,她的脸水亮亮的,一脸的泪。
正如房东阿姨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夏回来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的妥协导致我再也聚不起力量去进攻了。房东阿姨对我的行为表示了失望,竟然还去找她?现在好了吧,狗皮膏药又粘身上了。陈叔大大咧咧地说,既然她不想走,那就留下,怕啥,你是男人,怎么都不吃亏,大不了身体累点。他的观点招来女房东的一顿痛骂,女房东说,都五十的人了,脑子里成天就装着那事,就不能想点别的?她要是以后就不走了呢?小王还娶不娶媳妇了?她又不憨不傻,你想甩就甩呀?再说了,还是那句话,谁知道她是什么来路,一条狗你都不知道它明天会干什么,何况一大活人。万一有点事,她要是个杀人犯什么的,这麻烦就大了。陈叔脸色也跟着庄重起来,说是啊,万一要是个杀人犯,那你的问题就大了。在逃的杀人犯,什么事不能做?你阿姨说的对,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连累就是一大片哪。
问题被他们一说又严重了,毕竟人心隔肚皮。我要做的还是想办法把她打发走,可是我下不了手啊。我再次在饭桌上开始了审问。
我说:“你真的叫西夏吗?”
她点点头,对我的问题赶到奇怪,但立刻又低下头去。
“你家在哪里?”
她摇摇头,两只筷子在手里磨磨蹭蹭。
“谁让你来找我的?”
她还是摇头。
“你是不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
她又摇头。
什么都没问出来。我又问:“你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她点点头,终于抬起头来,缓慢地笑起来,那样子大概就是脉脉含情吧。
“可是我不愿意,”我说。“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们这样下去是没有道理的。你应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她又低下头,眼泪落到手上。看来让她自愿离开还是有很大困难的。那顿饭我又吃得心事重重。快吃完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个朋友找我,让我过去到他那儿喝酒,他老家的亲戚从连云港给他带了些海鲜过来,一块儿尝尝。
我对着手机说:“不好意思,今天真是抽不开身,要上班,还有个朋友在家里。”
对方说:“那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等朋友走了再说吧。”这么说的时候,我灵机一动,又加了一句,“朋友走了我一定去,她这两天就走。”
通过电话我去看西夏,她默默地放下筷子,开始收拾碗筷,她不吃了。她的神情搞得我也有点难过。莫名其妙,这事俨然成我的问题了,只有把她平安地送走我才能心安。我想起那张纸条,把它从棉衣里找出来,又从抽屉里把这两年亲戚朋友写给我的信件,一起装进包里就去书店了。
一个上午我都在核查笔迹,可是没有发现任何人的笔迹和纸条上的相同,相似的都没有。然后开始打电话,给我知道的亲戚朋友一个个打,问他们是否让一个叫西夏的女孩来找我,或者是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名叫西夏的女孩。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电话那头的亲戚朋友,说什么的都有。年龄大一点的,或者是女的,就建议我立马将西夏打发走,观点和女房东类似。熟悉的朋友,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不遗余力地开我的玩笑,怂恿我。他们说,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这年头你不占女人的便宜,女人就占你的便宜,能搞的就搞,何况还是个送上门来的。如果想赶她走,那好办,还买什么被褥,就睡一张床,害怕了她自然会离开了,不怕最好,一个字,上。却之不恭嘛。严肃一点的朋友则建议我,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让她走,找出她的来源,或者把她推给别的什么人。
我决定几种方法同时用。半下午我关了店门,去派出所找那个胖警察,我从他那里领来的西夏,最好的方法就是再还给他。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派出所,他不在,同事说他出去办事了,要一个小时后才回来。我不能干等,就到大街上把所有喜欢刊登广告的报纸都买了一份,坐在派出所里一张张翻,找寻人启事。一大堆报纸都翻完了,看了几十条启事,就是没一个和西夏沾边。那些要找的人要么是精神不正常的老人,要么是迷路的痴呆,或者是离家出走打算跑江湖的小孩。寻人启事之外,我把其他好看的内容也大致翻了一遍,胖警察还没回来。他的同事说,可能直接去接孩子了,让我明天再来,他们要下班了。
无功而返让我郁闷,买了一只全聚德烤鸭就回家了,反正要打发她走了,吃完北京的烤鸭再走吧,也不枉来北京一趟。那只烤鸭让我们都找到了事干,慢慢腾腾地吃到了八点半。收拾好了,我翻翻书,她看电视,十点的时候我说我困了,要先睡了。我的意思是,先把床抢下来,下面就是她的事了,像朋友说的,忍受不了和一个男人同床,那就走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主动去整理好床铺,然后让我去睡觉。上床的时候我发现,两个枕头并排放在一起,一个是我的,另一个当然就是她的了,而她的那个过去一直是用来做靠背的。床上的格局让我激动,我是个男人,我是个健康的男人。也让我失望,又一个办法失效了。我吞了两颗安眠药就睡下了。后来我感觉到她也上了床,在我身边躺下,可是我的眼皮沉重,连激动的念头都没有了。一夜安安静静。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派出所,胖警察还是不在,同事又说他办事去了。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事要办,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在忙。下午我赶在上班之前就到了,我把他堵在了门口。
“你是谁?”他陌生地看着我。“找我干吗?”
“你把一个姑娘推给了我,”我说。“西夏,你还记得吗?她待在我那儿不走了。我要把她还给你。”
“哦,是那个哑巴。她是来投奔你的,关我什么事?再说,送上门的女人有什么不好?”
“女人不要紧,问题是,”我说,“我不认识她,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进了办公室,坐下来,让我站着。“那是你们的事了。”
我和他说了半天才让他明白,西夏留在我那里是多么的不合适,我告诉他,不管怎样,我得让她走,让她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现在就要她回到派出所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这不是无赖么?”胖警察很不高兴,“你还嫌我不够烦呀?好,你想送回来就送好了,我把她转交给收容所,让他们烦去,遣返到哪儿随他们干去。现在警察就成一老妈子了,谁拉过屎了,都要我们去给他擦屁股。”
“收容所能安全把她遣返到家吗?”
“我怎么知道?问他们去。没听报纸上说吗,前些日子,一个安徽老太太来收容所找儿子,他们说早遣返回家了,可是遣了两年了,那老太太儿子还没有返回家。两头不着地,人没了。”
“就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缩着脖子打瞌睡,怀里抱着一本书。手机响了,是我的女房东,敞开嗓门问我现在哪儿。当然是书店了,我说,还能在哪儿。房东说,快点,赶紧的,到派出所去。警察到处找你哪,她说,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我都急死了。她应该是急了,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
“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女房东俨然是在跟一个罪犯说话。
我没理她,关了手机。我整天呆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能犯什么事。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我还是有点毛,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我看看了书架后面,没有一个顾客。大冷的天,谁还买书。我锁上门,外面已是黄昏,灰黑的夜就要降临,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风也是黑的,直往脖子里灌,这大冷的天。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什么时候车都多。我从车缝里钻过去,闯了两个红灯,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锁上车子后才发现,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
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灯,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敲敲门。
“你就是王一丁?”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唾沫星子都崩到了我脸上。
“我就是,”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我把第二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我没犯事啊?”
“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你看,”他伸出手表让我看,“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赶快领走。”
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我就听不懂了,她是谁啊我领她走?
“人家来找你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叫西夏,”胖警察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你是打哪儿来的?噢,我又忘了,你是个哑巴。”
我看了看那张纸,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有点乱:
王一丁,她就是西夏,你好好待她。
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
我又看了看那姑娘,高鼻梁,长睫毛,眼睛长得也好看。可我不认识她。
我说:“你是谁?谁让你来找我的?”
胖警察说:“我不是跟你你说过了么,她是个哑巴。”
哑巴。我又去看那张纸条,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她应该就是西夏。“我不认识她。”
“我也不认识,”胖警察说,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赶快领走,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
“警察同志,我真的不认识她。”
“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快走,”他把我往外面赶,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再看看不就认识了?”
“可是我真的不认识!”
“怎么?”胖警察头都歪了,指着墙上的警徽说,“这是派出所!”啪地带上了门。然后发动摩托车,冒一串烟就跑了。
胖警察走了,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她是冲着我来的,看来我是逃不掉了。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速度很慢,以便她能跟得上。她把手插在口袋里,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真的不错,走路的样子都好看。我把速度继续放慢,跟她走了平行。
“你叫西夏?”
她点点头。
西夏。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一个骑在马上的国家和一大群人,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太远了,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了。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
“西夏。”我说。
她又点点头。
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肚子叫了。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于是我又问她:
“饿了吧?”
她点点头。
回去做饭有点迟了,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汤汤水水的,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桥上车来车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从硅谷往北走,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穿过整个蔚秀园,再过从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就是承泽园。
我租的是平房,有点破,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我所以找了这间平房,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很粗,老得有年头了,肚子里都空了,常常有小孩捉迷藏时躲进去,一个大人都站得进去。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小时候,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我喜欢柳树,春天来了,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蔚秀园里行人很少,一路清冷,她是个哑巴,我也懒得说话了。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然后运回来,整理,上架,忙忙操操的一天。幸亏天气冷,一直清醒着,现在牛肉面下了肚,身子暖起来,瞌睡也跟着来了。
我把自行车放好,就去敲女房东的门。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看了看西夏,又看了看我,说:
“这姑娘是?你真的犯事了?这可怎么得了!”
“犯什么事!”我说,“帮个忙,让她跟你挤一夜。我屋小,她又是个女的。”
“她是谁?”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
“她叫西夏,不喜欢说话。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对我暧昧地笑了。四十来岁的老女人,多少有点神经过敏。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我好说歹说,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带过女孩来过这间小屋。没有女孩可带。女房东说,照直说不是结了,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都冻坏了,快进来快进来。真是的,对阿姨也不说实话。
第二天早上,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结结实实的一觉。我看看手表,才早上七点。天还没有亮开。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为什么要来投奔我。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不说。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问她哪里人,谁让她来找我的,找我干什么,她要么摇头,要么愣愣地看着我,或者是做着我看不懂的手势。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
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她冲我笑笑,进了我的房间,很自然,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我还站在门前发愣,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早上空气清冷,整个园子都很安静,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
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招呼我到他们家去。他们家的暖气比我的屋里好多了。“她不是个哑巴吗?”女房东说,表情严肃,声音很重,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不过人倒是不错。不管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好。”
她的意思我明白。我笑笑,说:“阿姨,你误会了,我不认识她。”
“不认识就带回来了!你真行,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
“我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陌生人。真的。”
“我不信,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
“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就让她找来了。她是谁,要干什么,我都不清楚,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我也在纳闷。”
“那,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她会不会是装哑巴?这年头什么人没有!”
这我倒没想到,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我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都有点心事重重了。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从水池边回来,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看到我在发楞,就笑笑,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又指指正冒热气的铁锅,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她像个这个小屋的主人一样,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我到沙发上坐下,点上一根烟,只吸了几口,就让它慢慢燃着,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
那根烟烧了一半,面条做好了。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然后,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她把筷子递给我,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没有荷包蛋。我捏着筷子看她吃,梳成马尾巴的头发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她对我摇摇头,又还给了我。继续低头吃面条,吃得很细,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哑巴?”
她抬起头看我,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
“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脸上出现了悲凄,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
“你是说,你过去不是哑巴,但是现在是了?”
她用力地点头,示意我快吃,面条快凉了。
我挑了一筷子面条,又问她,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她还是摇头,头低下来,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她也不知道。我还想再问下去,看到她吃得更慢了,就打住了。我想算了,不管她是什么人,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我们都不再出声,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动作很家常,像妻子夹给丈夫,像妹妹夹给哥哥,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吃完饭,她开始收拾去洗刷。我又点了一根烟,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我看看表,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我想提前去上班。
穿好衣服,我对着厨房说:“我去上班了,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然后我就走了,我想她懂我的意思。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我决定步行去书店。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不好也不坏,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一般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刚出了承泽园,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
“那姑娘呢?走了?”她问我。
“没有,还在洗碗。”
“那你问明白了?”
“没有,她不会说话。我也不想问了,也不好意思赶她走,拐了一个弯,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
“你犯糊涂了是不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
“就一间小屋,又搬不走。我没什么值钱东西。”
“这可是你说的,”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
能出什么事,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但那是她家的房子。我磨磨蹭蹭地走,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在上面溜冰,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穿过蔚秀园,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看了看硬梆梆站着的门卫,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念头。
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开门,简单地收拾一下,卖书,记帐,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还是卖书,偶尔的一阵小瞌睡,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本有意思的书翻翻。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都瞎看。因为看这个书店,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肚子里稀里糊涂也算有了点墨水。这是别人说的,我朋友,还有那些买书的人,比如北大、清华的一些学生,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上几句。这么一来,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就更加热爱看书了。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不知道,反正是爱看了,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看得还像模像样。
先亮一盏灯,再亮第二盏,三盏灯全亮起来,天就快傍晚了,我该关门回家了。
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总觉得心里有点事,大概是看书看的,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心里总还惦记着。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跑得快,今天突然改步行了,一路东张西望,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行人和车,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我的小屋里散出来。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那个叫西夏的女孩。门关着,我站在门前,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她竟然还没走。我推门进去,她就醒了。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揉揉眼站起来,打了一个寒战。她对我笑笑,让我坐下,她去热一下饭菜。她把晚饭做好了,两菜一汤在饭桌上。既然没走,也只好这样了,我坐下来,点上烟,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
饭桌上我几次想问,为什么没有离开,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饭菜的味道也不错。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我意识到这是晚上,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
更尴尬的还在后面。
吃过饭西夏洗碗,我去敲房东的门,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敲了半天,门才开,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
“那姑娘怎么还不走?”她问我,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眼睛盯着电视。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阿姨,”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明天我就让她走。”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这就不好办了。”
“陈叔不是出差了吗?”
“是啊,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他在电话里说了,就这两天,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你看,怎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
“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小军的。”
“那床好长时间没人睡了,再说,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
“那能不能让陈叔委屈一下?”
“小王,这个,你看我们家老陈出门这么多天了,刚回来,总得,不怕你笑话,人都说小别胜新婚。你陈叔是个急性子,你也知道。”
话都说成这样了,四十多岁,正是饱满的欲望之年。我还能说什么?扯了个幌子,我敷衍几句就离开了。我知道她在推辞,我临走的时候她又告诫我:
“小王,来路不明,早晚是个祸害。”
那晚陈叔当然没有回来。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我的事很麻烦,我必须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居一室,这怎么说都是件别扭的事。她在烧热水,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我帮她调大了一些。在电视上别人的声音里,我抓着头皮说:
“房东那边今晚不方便,只好委屈你住这里了。”
她点头答应着,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煤气灶上的水开了,她像家庭主妇那样去灌热水瓶。我知道女人的事很麻烦,就告诉她哪个是脸盆,哪个是脚盆,然后就关上门出来了。我在外面找不到事干,就抽烟,打火机照见了屋檐下一溜衣服,被冻得硬梆梆的,裤管直直地站在夜里。她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我被感动了一下,除了我妈和我姐,还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大冷的天,她洗了一大堆衣服。
一根烟抽完了,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她做出怕冷的样子,她怕我冷。她堂而皇之地在我面前脱掉鞋袜开始洗脚,我努力将目光固定在电视上,还是看见了她的脚,白得触目惊心。她的脚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人。真要命。我决定去收拾一下床铺。让她睡在床上,我把长沙发打开,临时做成了一张床。缺的是被褥,我只有一套。只好从衣橱里把所有能摸出点厚度和温暖的衣服全找出来,铺在沙发上做垫被,我得和衣而卧,身上盖一件棉大衣了事。
那晚我就这么睡的。说句没出息的话,真有点惊心动魄。我让她先睡,我要看一会儿书,背对着她,带上耳塞边听音乐。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拿下耳塞,听到了她的微小的呼噜声。女人的这种小鼾声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可爱。她睡得像只猫,被子弯曲成身体的形状。我灭了灯,在沙发上缩成一团,穿着衣服睡还是冷。冷也睡着了。
后半夜我翻身,听到了一点声音,下意识地睁开眼,西夏竟然睡在了我身边,她也到了沙发上。她把被子一大半盖在我身上,我翻身时压到她的胳膊了。她侧身面对我睡,另一只胳膊放在我身上,像在微笑似的撇了撇嘴。当然她还在熟睡。我出了一身的汗,谨慎地转过身背对她,平息了很久才重新入睡。
我醒来时她已经起床了,正准备做早饭,什么也没有表示。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看着筷子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为了什么,你都得走了。我们这样很不方便。”
西夏半天没动静。我瞟了她一眼,她竟然流眼泪了,她对着我摇头。我就搞不懂了,一个闯入者,她倒觉得很委屈。委屈也不行。我匆匆吃完早饭,给了她五百块钱做车费,就去书店了。路上我也转过一个念头,就是她真不愿意走,那就只能留下来给我做老婆了,可是我要个哑巴干吗?连句话都不能说。再说,谁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就像女房东说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也说不准。还是得让她走。当然得让她走。
但是西夏没走。晚上我回来,远远就看到小屋里灯光明亮。我在门前停下来,看到了灯光里的一溜晒洗的衣裳,花花绿绿一堆女人的衣服。我推开门,西夏正在衣橱前比划一件长棉袄,看到我先是把衣服藏到身后,然后又拿出来,像小姑娘那样穿上让我看,在镜子和我面前转来转去。挺不错的一件衣服,我说,好。
她又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条咖啡色的围巾,踮着脚给我围上,给我买的。她把我拉到穿衣镜前,点着头盯着我眼睛看,我说好看。她很高兴,掏出一把钱给我,大约两百五十块钱。这是剩下的,她把我给的车票钱买了一堆衣服。
“你,”我说,“怎么没走?”
她低下头,脱下新棉袄,换上旧衣服和围裙,一声不吭去了厨房。我有点火,她竟然把钱都买了衣服,看来是打算长住了。这怎么行。我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刚刚开始,播音员说,国家领导人又出访了。大人物总是很忙。我习惯性地点上烟,也不打算认真抽,我就在想,这个叫西夏的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想不清楚,我得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缺乏想像力。又在读过的书里找,好像没有读过类似的故事,倒是一些诡异的案件里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先是一个不速之客,通常是美人计,接下来就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想得我后背都有点发冷了。这时候热腾腾的晚饭上来了,她把做好的晚饭热了一下。
除了和朋友在饭店里,我一个人在家里从没吃过这么丰盛美好的晚饭。她指着刚才我随手放在电视机上的钱,告诉我她用了其中一些钱买了这些菜,还有一些,在厨房里。
饭菜很可口,可是一个难堪的夜晚又要来临了。早知道这样,我白天就去买一套被褥了。
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房东在门外叫我,声音很大,像要找我吵架。我让西夏先吃,我开门出去。女房东拉着我就往他们家里走,把门摔得响声动荡。
“你看,你看!”她指着电视机旁边一块空白的桌面说,“钱没了!两百块钱没了!”
“什么两百块钱没了?”
“我的,早上我洗衣服放在上面的,刚刚才发现,钱就没了!”
“钱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刚从书店回来。”
“不是你,但是你脱不了责任!”女房东火气很大。“一定是你招来的那个野女人偷的!她来过,她来借搓衣板。”
“阿姨,这事查清楚了再说,她可是一个女孩子。”
“就因为是个女孩子才更让人恶心!这屋里只来过三个人,我,你陈叔,他上午刚回来,回来就去单位报帐了,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哑巴。除了她还有谁?”
“是不是陈叔拿了,忘了告诉你?”
“我们家老陈出差刚回来,身上的钱还没花一半,他要两百块钱干什么?你看看你屋檐下,晾了那么多新衣裳,还有,哑巴又买了一件棉袄,哪来的钱?”
“我给的,五百块。她花了两百多。”
“她就是骗白痴的,那么多衣服就两百多?她还把棉袄拿给我看,那棉袄就不会便宜!一个大姑娘家,把裤衩、胸罩挂在门外招摇,用膝盖想也知道那不是个好货!你看这事怎么办?等你陈叔回来商量一下,要么你别再租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租不起!”
她说得我火冒三丈,我不是都给你五百块钱了么,你还拿别人的钱干吗?
我气势汹汹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在等着我一起吃饭。她要给我换一碗热稀饭,我说你别换了,我已经饱了。我从箱子里找出一个空闲的大包,闷声不响地出了门,把她晾在屋檐下半干的衣服全塞进了包里。塞完了进屋,把她的新棉袄也塞进去。拉好拉链往她旁边的沙发上一扔,声音立刻大起来:
“走,现在就走!想到哪去到哪去,别让我再看见你!好,你怕饿是吧?再给你两个馒头!不,都给你,我让你都拿走!”
我把剩下的馒头全塞进了包里,一把将她从凳子上拎起来,吓得她筷子和馒头都掉在了地上。她开始哭了。她开始发抖,横竖不愿意离开小屋。可是我正在气头上,力气大得让我自己都吃惊,我一手拎包,另一只手拖起她就往外走,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我把她一直拖到承泽园门外,把包摔到地上:
“你走吧,我们本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然后我转身回家。她啊啊的哭声和叫喊声我充耳不闻,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回到屋里,我把剩下的饭菜全都倒掉了。我觉得气愤,难过,我觉得我被别人耍了一把。不速之客本身就够荒唐了的,她竟然还手脚不干净。这成了什么事。我一个劲儿地抽烟,什么事也不想干,就想我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我在北京混了七八年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吃过苦受过罪,没有奇迹,没有艳遇,好不容易开始经营一个屁股大的小书店,能挣上碗饭吃,就有人算计我了。心里憋得慌,把眼泪都给憋出来了。
我抽了大约半盒烟,流了一大把眼泪,才想起来要赔女房东被偷的钱。这事因我而起,理当我来负责。我敲开他们家的门,陈叔开的门,他从单位回来了。
“不好意思,陈叔,阿姨,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我把那姑娘赶走了,被她拿走的两百块钱我给送过来了。”
陈叔说:“小王你坐,正说这事呢。刚才你阿姨错怪那姑娘了,钱是我拿的,我是怕被老鼠叼走了,随后装进了口袋,忘了跟她打招呼了。”
“是啊小王,”女房东笑容满面地说,“你是知道的,平房老鼠就是多,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东西都要往自己窝里叼。”
我是知道的。我的小屋里老鼠就很多,常常半夜三更拖着一片纸在地板上走,拖拖拉拉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走路,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把我吓坏了。这里的老鼠都是长相肥大的,胆子也大,有一回竟然爬到我的枕头上坐着,我从没见过这么威风的老鼠,心里都怯了,拿着笤帚远远地哄它,它就是不跑,还是人模狗样地坐着,用前爪子舒舒服服地擦嘴,直到我冲上来才跑掉。可是我已经把西夏赶走了。
“可是,我把她赶走了。”
女房东说:“那种女人,赶走最好。你想想,哪有女人主动送上门,而且来了就不走了的?这成什么事了。还有,花花绿绿的东西往外面一挂,哪是正经女人干的事。走了好,小王,你还要感谢阿姨哪,我早就看透了,那女人留下来就是祸害。”
她说得一头子劲,越说越觉得她是救了我。但是西夏却是被我蛮横地赶走了,她越说我越觉得不安,心里空荡荡的,就告辞回房间了。我想看电视冲淡一下心神不宁,就看到了西夏剩下的那些钱。我突然想起来,她是身无分文地被我赶走了。这么冷的夜,一个女孩子,一分钱没有,她怎么熬过去?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她找回来。可是,如果把她找回来了,她更有理由赖在我这里不走了,我该怎么办?赶走一次还有借口,哪怕是个错误的借口,毕竟已经成为事实,下一次怕就没有这么好的借口好找了。我盯着电视上的画面发楞,找还是不找,已然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把剩下的几根烟全抽完,已经午夜十二点了,因为房门没关严实,冷风丝丝缕缕地进来,我感到了冷。冰凉的那种冷,身上穿的似乎不是衣服,而是披了一身的凉水。外面毫无疑问更冷,西夏现在干吗?她在哪里?她一定会更冷。我扔掉烟头,随手抓上大衣和手套就出了门。我要把她找回来,天大的事也应该天亮了再说。
承泽园里一片沉沉的静,有几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大多是在这里租房子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的人在夜读。我走得很快,一路都在向四周环视,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到了万泉河的桥上停住了,我该到哪里去找她呢。有很多路,每条路都是一个不可知的方向,西夏可以沿着任何一条路走下去,走到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我决定先沿着西夏曾经走过的路找一遍,穿过蔚秀园,沿北大西门往南走,过硅谷到马兰拉面馆。路灯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几个行人穿着臃肿的棉衣,但却显得寒瘦。海淀体育馆门前还有几个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去练歌房唱歌的。几辆出租车停在门前等待客人。我问那些快要睡着的司机师傅,是否看见一个女孩拎着一个大包经过这里。他们以为我要打车,听明白了就摇头,然后继续瞌睡。后来我见着人就问。没有人看见,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漫无目的地找,到了两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冷倒不冷,因为一直在走,就是想睡觉,我想找个商店买包烟提提神。这时候我已经走到了苏州桥附近,到处都是霓虹灯在闪烁,就是找不到一家卖烟的商店。转了几圈,想到了通宵营业的超市,就去找超市,终于在城乡仓储附近找到了一家,为了防止很快抽光,我买了两包烟,两个打火机。
点上烟继续找,见到人继续问,走走停停竟然走到了四环边上。空旷的四环和四环之外的野地,灯光不大不小,空气清冽,周围的景物一览无余。跑长途的货车和大客车多一些,小车就少多了,行人更少,几乎看不见人影。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在动,心动过速地跑过去,是一个清洁工人在打扫道路。他要在天亮之前把这一段路打扫干净。我问他是否见到一个拎包的女孩,他说没有,这种时候他只会遇到酒鬼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很累了,走得一身的汗。前面是四环和三环之间的一个过街天桥,我爬上去,以便看得更高更远。四顾莽莽,夜在逐渐变轻变淡,凌晨最初的蓝色从野地里升起来,身后的北京开始蠢蠢欲动。我看到不远处另一座天桥下卧着一个东西,黑乎乎的一团,有点像人。心跳又开始加速,我暗暗祈求,希望那个黑影就是西夏。又是一路小跑,穿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卡车撞到。跑到跟前就失望了,是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像条狗似的蜷缩在桥下的台阶上,台阶上放着一个北京二锅头的空酒瓶。我想叫醒他,这样睡觉会冰出毛病来的,但是听着他畅快的鼾声又算了。睡得这么好,就让他睡吧。
我终于绝望了,也受不了了,为了防止像流浪汉一样睡倒在路边,我决定回去。本来就是大海捞针的事。天快亮了,脚也发沉,我走到承泽园时,门口有的早点摊子已经开始摆起来了。一步都不想走,走到老柳树前我实在走不动了,想先抽几口烟歇歇再进家门。我扶着柳树,点上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吸了两口觉得不对劲儿,柳树洞里有什么东西在一闪一闪,我伸头去看,吓我一跳,我看到了一双眼睛在亮。它们也看到了我,里面走出了一个缩成一团的人,我本能地后退两步,是西夏。我的烟往嘴里送,在半路上停下了,真的是西夏。
“你在这里!”我叫了起来。“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了,定定地看着我。我想伸手去拉住她,她却蹲下了,她蹲在我的脚前,把我散开了的鞋带系上了。然后站起来,转身回到树洞里,拎出了那个大包,默默地走到我前面,向我的小屋走去,在门前等着我开门。
进了门打开灯,她的脸水亮亮的,一脸的泪。
正如房东阿姨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西夏回来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的妥协导致我再也聚不起力量去进攻了。房东阿姨对我的行为表示了失望,竟然还去找她?现在好了吧,狗皮膏药又粘身上了。陈叔大大咧咧地说,既然她不想走,那就留下,怕啥,你是男人,怎么都不吃亏,大不了身体累点。他的观点招来女房东的一顿痛骂,女房东说,都五十的人了,脑子里成天就装着那事,就不能想点别的?她要是以后就不走了呢?小王还娶不娶媳妇了?她又不憨不傻,你想甩就甩呀?再说了,还是那句话,谁知道她是什么来路,一条狗你都不知道它明天会干什么,何况一大活人。万一有点事,她要是个杀人犯什么的,这麻烦就大了。陈叔脸色也跟着庄重起来,说是啊,万一要是个杀人犯,那你的问题就大了。在逃的杀人犯,什么事不能做?你阿姨说的对,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连累就是一大片哪。
问题被他们一说又严重了,毕竟人心隔肚皮。我要做的还是想办法把她打发走,可是我下不了手啊。我再次在饭桌上开始了审问。
我说:“你真的叫西夏吗?”
她点点头,对我的问题赶到奇怪,但立刻又低下头去。
“你家在哪里?”
她摇摇头,两只筷子在手里磨磨蹭蹭。
“谁让你来找我的?”
她还是摇头。
“你是不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
她又摇头。
什么都没问出来。我又问:“你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她点点头,终于抬起头来,缓慢地笑起来,那样子大概就是脉脉含情吧。
“可是我不愿意,”我说。“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们这样下去是没有道理的。你应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她又低下头,眼泪落到手上。看来让她自愿离开还是有很大困难的。那顿饭我又吃得心事重重。快吃完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个朋友找我,让我过去到他那儿喝酒,他老家的亲戚从连云港给他带了些海鲜过来,一块儿尝尝。
我对着手机说:“不好意思,今天真是抽不开身,要上班,还有个朋友在家里。”
对方说:“那什么时候有空?”
我说:“等朋友走了再说吧。”这么说的时候,我灵机一动,又加了一句,“朋友走了我一定去,她这两天就走。”
通过电话我去看西夏,她默默地放下筷子,开始收拾碗筷,她不吃了。她的神情搞得我也有点难过。莫名其妙,这事俨然成我的问题了,只有把她平安地送走我才能心安。我想起那张纸条,把它从棉衣里找出来,又从抽屉里把这两年亲戚朋友写给我的信件,一起装进包里就去书店了。
一个上午我都在核查笔迹,可是没有发现任何人的笔迹和纸条上的相同,相似的都没有。然后开始打电话,给我知道的亲戚朋友一个个打,问他们是否让一个叫西夏的女孩来找我,或者是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名叫西夏的女孩。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电话那头的亲戚朋友,说什么的都有。年龄大一点的,或者是女的,就建议我立马将西夏打发走,观点和女房东类似。熟悉的朋友,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不遗余力地开我的玩笑,怂恿我。他们说,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这年头你不占女人的便宜,女人就占你的便宜,能搞的就搞,何况还是个送上门来的。如果想赶她走,那好办,还买什么被褥,就睡一张床,害怕了她自然会离开了,不怕最好,一个字,上。却之不恭嘛。严肃一点的朋友则建议我,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让她走,找出她的来源,或者把她推给别的什么人。
我决定几种方法同时用。半下午我关了店门,去派出所找那个胖警察,我从他那里领来的西夏,最好的方法就是再还给他。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派出所,他不在,同事说他出去办事了,要一个小时后才回来。我不能干等,就到大街上把所有喜欢刊登广告的报纸都买了一份,坐在派出所里一张张翻,找寻人启事。一大堆报纸都翻完了,看了几十条启事,就是没一个和西夏沾边。那些要找的人要么是精神不正常的老人,要么是迷路的痴呆,或者是离家出走打算跑江湖的小孩。寻人启事之外,我把其他好看的内容也大致翻了一遍,胖警察还没回来。他的同事说,可能直接去接孩子了,让我明天再来,他们要下班了。
无功而返让我郁闷,买了一只全聚德烤鸭就回家了,反正要打发她走了,吃完北京的烤鸭再走吧,也不枉来北京一趟。那只烤鸭让我们都找到了事干,慢慢腾腾地吃到了八点半。收拾好了,我翻翻书,她看电视,十点的时候我说我困了,要先睡了。我的意思是,先把床抢下来,下面就是她的事了,像朋友说的,忍受不了和一个男人同床,那就走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主动去整理好床铺,然后让我去睡觉。上床的时候我发现,两个枕头并排放在一起,一个是我的,另一个当然就是她的了,而她的那个过去一直是用来做靠背的。床上的格局让我激动,我是个男人,我是个健康的男人。也让我失望,又一个办法失效了。我吞了两颗安眠药就睡下了。后来我感觉到她也上了床,在我身边躺下,可是我的眼皮沉重,连激动的念头都没有了。一夜安安静静。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派出所,胖警察还是不在,同事又说他办事去了。我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事要办,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在忙。下午我赶在上班之前就到了,我把他堵在了门口。
“你是谁?”他陌生地看着我。“找我干吗?”
“你把一个姑娘推给了我,”我说。“西夏,你还记得吗?她待在我那儿不走了。我要把她还给你。”
“哦,是那个哑巴。她是来投奔你的,关我什么事?再说,送上门的女人有什么不好?”
“女人不要紧,问题是,”我说,“我不认识她,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进了办公室,坐下来,让我站着。“那是你们的事了。”
我和他说了半天才让他明白,西夏留在我那里是多么的不合适,我告诉他,不管怎样,我得让她走,让她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现在就要她回到派出所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这不是无赖么?”胖警察很不高兴,“你还嫌我不够烦呀?好,你想送回来就送好了,我把她转交给收容所,让他们烦去,遣返到哪儿随他们干去。现在警察就成一老妈子了,谁拉过屎了,都要我们去给他擦屁股。”
“收容所能安全把她遣返到家吗?”
“我怎么知道?问他们去。没听报纸上说吗,前些日子,一个安徽老太太来收容所找儿子,他们说早遣返回家了,可是遣了两年了,那老太太儿子还没有返回家。两头不着地,人没了。”
“就那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skg是什么牌子 的文章
- ·HAODUOQI自行车bv是什么牌子子的自行车
- ·cyclonus bv是什么牌子子的自行车
- ·有没有人知道这双鞋vivo是什么牌子的手机哪款鞋?十分感谢!!
- ·zstarfossil是什么牌子子自行车
- ·iverson answerlongines是什么牌子子
- ·SANDAseiko手表是什么牌子子
- ·bmwkinglongines是什么牌子子
- ·这个guess是什么牌子?
- ·boenor体育用品elle是什么牌子子?
- ·stormcc6.o是羽毛球拍什么牌子好球拍,价格好多钱
- ·pinxi线轮skg是什么牌子子的
- ·bettonigxg是什么牌子子
- ·鞋的外侧都是乱七八糟的白色条elle是什么牌子子的鞋
- ·cosmoesqulre是什么cos美瞳哪个牌子好
- ·爬珠峰的装备一般moncler是什么牌子子的
-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logo的旱冰鞋酷派大神是什么面板牌子的
- ·捷安特刺客7700的轮组,是什么牌子的,一套大概多少钱。
- ·最美的时光篮球一号的鞋guess是什么牌子子
- ·这ds是什么牌子的车自行车
- ·中国十六球世界锦标赛用的gxg是什么牌子子的台球桌
- ·请问这vivo是什么牌子的手机篮球!?很急!
- ·ktwoseiko手表是什么牌子自行车牌子
- ·kejian自行车fossil是什么牌子子
- ·帮忙看看图片的儿童自行车guess是什么牌子子的?
- ·freespiritskg是什么牌子子的自行车
- ·roswet自行车vivo是什么牌子的手机
- ·bnillen是什么牌子,买的是儿童自行车牌子
- ·klpsta acer是什么牌子子足球
- ·sw0rdsmanfossil是什么牌子子健身自行车
更多推荐
- ·越南留学中介条件如何?
- ·越南留学中介需要什么条件
- ·拉萨八廓街必买什么角街和八廓街是同一个地方吗?
- ·雅叶高速路线图中的叶具体位于哪个新疆城市?
- ·新疆九曲十八弯位于哪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伊犁草原?
- ·一个国家粮食能源电力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有保障就可发展科技
- ·求个求一品楼账号VIP账号,我只是看看信息谢谢,有的请私信我,谢谢
- ·三灶金梦园黄金怎么样具体资料
- ·饶明俐讲课视频神经病学教学视频下载
- ·19岁美国贱女孩1高清完整版图书馆自拍完整版,求发273800852多谢多谢
- ·求island fever 4种子3 种子最好是高清的~
- ·请问01059541476178是哪里的号码号码?
- ·用这20首歌重燃你的健身燃脂恢复计划
- ·nike 大鲨鱼淘宝nike正品店原价多少
- ·纽巴伦和新百伦的区别有一款上面是一层薄薄的布做的那双鞋是什么型号的
- ·新百伦鉴别真假574鉴别
- ·这双阿迪双肩背包大约多少钱
- ·有没有什么帮助快速记忆的的方法,听说记忆力可以如何训练记忆力,怎么如何训练记忆力啊?
- ·我的自行车后轮结构不能用变档了,龙头那里怎么按都没用(行驶中)
- ·沙包跳房子图片在哪,求解,给采纳
- ·ktwoseiko手表是什么牌子自行车牌子
- ·天猫酷锐运动怎么样锦旻运动
- ·2015中甲联赛一共多少场比赛啊
- ·万鬼狠人大帝鬼脸图片还写不写了
- ·象语是后天电影高清国语版训练的吗
- ·国奥vs海地张池明身高的视频录像
- ·吴天永城管打人视频频直播
- ·脚撞铁杆上脚被撞肿了怎么办才能弄好
- ·耐克气垫女鞋进了泥巴怎么办
- ·请马上发自己穿的运动鞋品牌大全照片来看看吧,最好是这双哦,越快越好急急急急急急
- ·nbadw手表换表带教程10016使用教程
- ·燕都紫庭金地城附近哪有打篮球的地方
- ·吴莫愁和哈林结婚照大游泳馆年卡可以办吗
- ·体育室有18个乒乓球和12个北京羽毛球培训班. (2)每班分4个北京羽毛球培训班,够几个班分?
- ·为什么nba球星这么在意nba三双排行榜
- ·如何处理跑步后拉伸运动图解红彤彤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