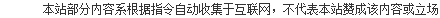90年阿根廷杜高卫冕失败听说是被国际足联阴的是不是真的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04-27 09:01
时间:2015-04-27 09:01
足球就是阿根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日 01:31
“这种多变、狂热、敏感而浪漫的特点,似乎都浓缩在阿根廷第一位全球性足球英雄,迭戈·马拉多纳身上。”梅森对本刊记者说,“一个出身下层,粗鄙、任性、沉溺于药物而不能自拔的足球巨人,与资源丰饶却在经历政治与经济动荡阵痛,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拉美国家现状却非常契合。”与贝利不同,马拉多纳似乎就是足球界的穆罕默德·阿里,其魅力不仅在于场上表演,也缘于对全球资本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反抗:他公开谴责美国对于古巴的经济封锁,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私交甚厚。直到今日,阿根廷球迷仍然固执地相信,马拉多纳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药检丑闻是一桩阴谋:诸如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家族,本着对1990年世界杯上意大利惨遭阿根廷淘汰的旧仇进行报复的缘由调换了球王的尿样;但其中最惊世骇俗者,就是1995年著名体育评论员费尔南多·内姆布罗撰写的报告文学《无辜》:这本著作言之凿凿地将驱逐马拉多纳的始作俑者直指美国中情局。在内姆布罗看来,这一行为,不仅能“阻止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最主要国家赢得世界杯”,更旨在“打击拉美足球,打击阿根廷的民族自信,更打击了古巴”。他坚称,中情局特工迈尔·肯尼迪支使一位拉丁裔神父,在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之前,向前来祷告的马拉多纳分发了一块含有违禁药物成分的圣饼。而国际足联药检机构也在中情局的暗示下,在恰当的时机对阿根廷国家队进行了突击药检。 “阴谋论,是缺乏全球化视野和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把握能力的第三世界民众,解释所有复杂现象的本能工具。”杰佛里·托宾在《足球阴谋论,中情局,马拉多纳与拉美大众批判》中这样说。无独有偶,1974年至1982年的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梅蒂诺,也卷入了贿赂丑闻,据称,他和国内以及欧洲一些博彩集团达成了协议,让阿根廷队在未来的世界杯中故意输球。 这些层出不穷的猜疑似乎说明,在阿根廷乃至大部分拉美民众眼中,世界级足球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的“平等原则”一样,永远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 穷街陋巷中的足球政治 乌拉圭人曾谑称,自己的祖先是阿兹台克人,而阿根廷人的祖先则来自船上。确实,与足球这一舶来运动一样,移民也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初迅速发展的动力。来自欧洲的移民潮,使得阿根廷全国人口从1869年的170万上升至1914年的790万。鉴于阿根廷出口和农业经济的中坚产品畜牧业与谷物种植并不需要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个国家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1910年,产业与服务业工人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人口的60%左右,其中大约一半是意大利与西班牙移民,年,阿根廷接收的净移民数量高达350万,为其提供谋生之道的是毛纺织业、肉类加工、造船厂、码头搬运以及邮政、铁路等因出口而蓬勃发展的公用事业。 孕育阿根廷足球的温床,就是各大城市中被称为Barrios的社区。1910年,仅仅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超过300个大小不一的足球俱乐部。与英国移民建立的学校球队和早期职业俱乐部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场地,经常在Barrios附近的空场,甚至街边组织比赛:萨斯菲尔德俱乐部成立时,球衣配色是一片纯白——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廉价的一款设计。至于前胸那个大名鼎鼎的蓝色V字,则是因为最初一批队服的订户,一支橄榄球队始终没有提货,从而使刚刚成立、手头拮据的俱乐部以不可思议的低价买下了这批烂尾货。1912年,由英国移民和中上阶层为主的52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自己的“阿根廷足球协会”,而152家工人阶级贫民俱乐部则联合在一起,宣告了“阿根廷足球联盟”的诞生。两者的比赛风格也泾渭分明:前者强调身体对抗、战术纪律的英式比赛风格,而后者更注重即兴发挥,以炫技表演的“克里奥”(Criollo,原指南美洲本土白人)风格招徕球迷。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曾在《潘帕斯草原上的X光》中描述说:“(跑马)赛道和足球场代表两个政治团体,前者代表着冒险、动荡、傲慢、中央集权和君主制,后者象征着体力劳动、充满激情的斗争、混乱和民主。”这一点从河床和博卡青年的历史渊源中就可见一斑:两个知名足球俱乐部有着相似的起源。它们的球迷都是博卡地区周边的工人阶级和赤贫的外来移民:河床实现了移民寻找全新自我身份的梦想,博卡则在本地工人的汗水与团结中找到了安慰。顺便说一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其原籍早从意大利、西班牙变成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相对贫穷的邻国——这一点经常被博卡球迷用来嘲笑自己的老对手。 在这种情形下,阿根廷独有的足球文化应运而生。1920年,著名的全国性足球杂志《ElGrafico》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阿根廷和它的南美邻邦一道,开始打破欧洲国家对于这项运动的垄断局面:1928年,阿根廷国家队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牌,两年后,又在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上名列第二。博卡青年队守门员特索列尼以及路易斯·蒙蒂、莱蒙德·奥尔西等出身贫困的足球明星,共同激发了阿根廷城市无产阶级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 很快,足球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一部分,20年代,正是以波里托·伊戈里延为代表,被称为“1880一代”的民主政治家决心使阿根廷摆脱军人和寡头腐败政治,努力将中产阶级宪政引入这个国家的岁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几百个政党领导人发现,足球俱乐部是他们接近民众,获取选票的最佳途径,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的主场纪念碑体育场以及“巧克力盒”,都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与南美洲球迷对那些性格不羁、顶撞教练的球员情有独钟道理相同,政客们必须以来自平民阶层、蔑视权威的反叛者形象出现。同样,身为社区领袖和企业大亨的俱乐部领导人也乐于借助政党参与政治,足球俱乐部成为每个社区社交、运动、商业乃至公共事务的中心,经费主要来自俱乐部实权人物的捐助;激进公民联盟(UCR)的实权人物佩德罗·比德盖安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的创始人,到今天,它的主场仍以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来命名。 这种足球与政府之间的互相提携在高举“民众主义”旗帜的庇隆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体育运动成为民众主义者动员群众,塑造其民族自信心与国家认同感的工具。1947年7月,庇隆政府骄傲地宣称,阿根廷已经偿清了所有外债,次年,将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铁路和电讯企业收归国有。在年之间,劳工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增长了25%。大名鼎鼎的总统夫人爱娃·庇隆于1950年捐助成立了阿根廷青少年足球联赛——爱维塔青年冠军杯,作为她丈夫旨在提高城市工人阶级福利的“正义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948年拍摄的电影《Pelotadetrapo》(布球)就是一部将足球与国家主义情感结合的代表之作:男主人公戈穆努阿斯是一位因心脏病而被迫退役的明星前锋,然而,为了帮助国家队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中战胜宿敌巴西,抱病上阵的戈穆努阿斯在射中制胜一球后倒在了绿茵场上。 尽管到了60年代,庇隆主义失去了曾经的魔力,逐渐退出了阿根廷政治舞台,然而这种紧密提携的关系却留存了下来。1967年,本菲尔德俱乐部主席瓦伦丁·苏亚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倒台,就像它不会允许自己倒台一样!”阿根廷经济从50年代开始,饱受通货膨胀和农产品全球价格下跌的打击,但这并不妨碍历任政府向那些负债累累但闻名遐迩的俱乐部慷慨解囊。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政治化足球”的后果,就是任何一次绿茵场上的失败,都会成为阿根廷民众宣泄对于现实不满的导火索,尤其是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刻。日,在西班牙世界杯揭幕战上,卫冕冠军阿根廷输给了传奇门将让·马里·普法夫领衔的比利时队,次日,英国宣布马岛战争结束,岛上剩余阿根廷军队投降,愤怒的群众在五月广场和玫瑰宫前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声名降到谷底的陆军只能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温和派退役将军雷纳尔多·比尼奥内取代被迫辞职的加尔铁里出任总统。此时,阿根廷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200%,100比索的硬币已经完全退出了流通,恼怒的群众很快发现了它的新用途——在足球场和游行示威中投掷裁判和警察。在那首阿根廷足球观众咏唱的口号歌曲《Hayquesalter》(你必须跳起来)中,被重复多次的一句就是“你必须跳起来,必须跳起来,不跳起来的就是X”。此时,“X”不再是1978年世界杯冠军决赛时的“荷兰佬”,或者马岛战争起间的“英国佬”,而是“军人狗腿子”。 4年后的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终于在球场上报了一箭之仇,在1/4决赛中以2比1淘汰了英格兰,马拉多纳在回忆中,这样描述比赛之于阿根廷大众的意义:“我不否认,我们赢得了某些超越一场足球比赛之外的东西,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我们这些足球运动员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虽然在比赛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跟马岛战争无关,但谁都知道那是在说谎!在我们体内,仍然可以感到疼痛,从在那个岛屿上牺牲的阿根廷子弟身上传导过来的疼痛……” 对于阿根廷,甚至拉美社会大众来说,日,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举行的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更为真实和可感知、可参与的战争。与此相对的,正如巴里·列文森执导的《摇尾狗》中映射的那样,许多生活在CNN和网络时代的美国民众,甚至坚信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虚构的真人秀,远不如一场“真实”的NFL或者NBA赛事那样值得关注。“1994年美国世界杯,阿根廷的出局,不仅是马拉多纳和一支球队的失败,更是自庇隆时代以来,足球,民众主义与阿根廷国家精神三位一体联盟时代的终结。”杰佛里·托宾写道。 野孩子与全球化时代 正如全球足球爱好者用“桑巴”来形容巴西足球运动员富于韵律和想象力的动作,阿根廷足球独特的风格,似乎只能用探戈来比拟。1961年,捷克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卡尔·克罗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南美人,无论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都拥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自然球感,更灵活的脚踝,协调性和弹性,也许他们只需要欧洲球员60%的训练量就能轻松保持状态。” 和足球一样,探戈源自阿根廷港口城市糜烂嘈杂的酒吧和风月场所,只有在著名探戈作曲家、歌唱家卡洛斯·加丹尔出现,并逐渐在巴塞罗那、巴黎等大西洋对岸的港口城市中大受欢迎后,才逐渐被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所接受。 最初,精通此种舞蹈的是被蔑称为“Compardrito”(阿飞、混混)的下层阶级青年。“他们的特征是,一口Lunfardo(融合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下层阶级方言)到处留情的风流种子,有过犯罪前科,身体精瘦结实,如有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耍诈、欺骗或者动刀。”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足球——全球化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作者理查德·朱利安诺蒂对本刊记者说,“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面对侮辱时绝不退缩。一次潇洒的折腰,向对手要害部位致命的一刺,或者一次潇洒的胸部停球转身过人,都巧妙地将想象力、身体控制与破坏性结合在一起,从而通过羞辱打击对手,赢得街头声誉。” 很明显,对于阿根廷球员和球迷来说,保持个人风格,有时比胜利更加重要。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足球不过是一项“缓慢、粗糙、野蛮的欧洲人游戏”,然而拉丁美洲人的表现却证明,技巧与天赋可以弥补体力上的不足。1990年世界杯,比拉尔多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在决赛中输给了联邦德国,他的前任梅诺蒂曾激愤地表示,他平生第一次以自己的阿根廷人身份为耻。这种耻辱感不仅来自失败,更来自阿根廷足球风格的丧失:空有马拉多纳、布拉查加和巴尔达诺,却没有酣畅淋漓的配合和神来之笔式的进球,居然要依赖点球才能淘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似乎这也能够解释被誉为“下一个马拉多纳”和最后一个具备“传统”式背景的阿根廷足球明星、出身城市贫民窟的中场天才奥尔特加,在初涉西甲时只能委身于中游球队瓦伦西亚。 对于阿根廷乃至拉美国家城市贫民来说,足球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机会,一代代球星是在尘土飞扬的街头、海滩磨炼自己的技术,而一代代的球员都不乏模仿的对象和激励自己的目标:小罗模仿罗纳尔多,罗纳尔多的偶像是独狼罗马里奥,而罗马里奥和这两位晚辈都崇拜贝利。1970年,跟随贝利在第九届世界杯上夺冠的巴西后卫卡洛斯·阿尔贝托说:“想看最炫目的足球表演,你就必须去街头。”大小罗分别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和阿格雷港的贫民窟里,他们的足球启蒙几乎一模一样,踢着空罐头和塞满纸的袜子,把木桩和自家的狗想象成防守球员。 截止到200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共有22个贫民窟,总人口数量达到12万,大部分人月收入不足300比索。从马拉多纳、罗马里奥到卡尼吉亚,出身于这里的天才球员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野孩子”(Malandro),这是民众能够给予他们的最高荣誉称号。“走进贫困的社区,在那些陈旧、低矮、潮湿,用铁皮、废旧木板和塑料布搭建的低矮建筑中,每一栋里都住着一位膝边环绕着五六个孩子的母亲,她会告诉你,全家的希望都集中在某个野孩子身上。”朱利安诺蒂告诉我们,“他伶俐而狡黠,捡废品,卖报纸,替人扛行李或擦鞋,并借此每天带回足够的食物或钞票支撑整个家庭,他能够像风一样在街道上奔跑,戏弄警察,如同他轻松地在那条狭窄到仅供两人并行的小巷中,用赤脚拨弄着那只破旧的足球晃过防守者一样。” 然而,正当体育不可避免地被全球经济一体化重新塑造的同时,拉美足球也未能置身事外。自从2004年以来,在全球顶级联赛中淘金的巴西球员数字达到了惊人的249人,小罗纳尔多和梅西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在自己国家的球场上表演,他们甚至并非是巴西和阿根廷能够培养的最佳足球运动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欧洲顶级足球联赛中身价最昂贵的球员。不仅如此,足球明星本身的特质也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从雷东多到梅西,他们已经演变成了郊区中上阶层文化和全球性奢侈消费的代表,2009年夏天,梅西刚刚收到了巴萨开出的税后1250万欧元年薪的合同,除此之外,他还是爱彼手表、阿迪达斯、百事可乐、微软X-box360游戏主机等产品的代言人。在全球化媒体和体育职业营销时代之前,球星仅仅是本地社区的英雄,体现的是某种狭隘的文化特质,对一切外来者抱有敌意。然而在当下,他们除了拥有非凡的技巧和身体,还必须是娱乐明星,个性必须拥有某种超越国籍、种族甚至性别的亲和力和某种令观众莫名激动的X因素,其身边必须有各不相同、令人艳羡的异性作为陪衬。比如梅西身边的阿根廷名模兼电视主持人露西亚娜·萨拉萨尔。 然而,拉美球员的出色发挥并不能掩盖这块足球圣地身上散发的腐败气息,以西方视角来看,阿根廷乃至南美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极端不称职:在24支巴西甲级俱乐部中,只有6家赢利。2002年,里约热内卢的弗拉门戈俱乐部负债超过1亿美元,主场最昂贵的场边嘉宾席位也是油漆斑驳、木料发霉的陈旧座椅,通向盥洗室的破旧走廊墙壁上满是粗口涂鸦,地上尿迹斑斑——许多固执的观众坚持认为自己一旦离开座位,肯定要错过某个精彩的进球,总是就近解决了事。阿根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随心所欲的阿根廷足协每年几乎都要为联赛炮制一个不同的体系,制定出五花八门的新规则,甚至有时连门票收入都要被当做进入附加赛的条件,赛程被形形色色的锦标赛和杯赛分割得七零八乱。刚刚踏入职业联赛的年轻球员仿佛置身于200年前的南美奴隶市场——劳工证必须上交俱乐部,从而迫使他们失去了迁徙、转会甚至参与薪酬协商的权利。不仅如此,欠薪成了阿根廷足球俱乐部的惯例,2009年,大约有1/3的顶级俱乐部没有按时给球员支付薪水,总额达到惊人的3800万比索。在这种情况达到顶峰的1997年,忍无可忍的阿根廷职业球员终于举行了一次罢工。相比之下,巴西的情况似乎要好些,这部分也要归功于传奇球星、曾担任体育部长的贝利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其国际影响力:2001年3月,巴西正式通过的《贝利法案》,允许球员自由转会,普通劳动法规在足球运动员身上同样有效,各俱乐部应和企业一样公开账目,建立经理负责制。 另外一个令人挠头的因素,则是被称为“Barrasbravas”的职业足球流氓:他们大多年龄在20岁至25岁之间,除了负责在比赛日与敌对俱乐部的球迷斗殴,有时还充当俱乐部主席的保镖,并负责在其竞选时充当打手并定期从俱乐部领取薪酬和球票。根据统计,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仅仅是为“Barrasbravas”提供机票一项,就花去了各足球俱乐部大约150万美元。2000年6月,当河床队最终在萨斯菲尔德体育场击败费罗铁路西部俱乐部,夺取当年联赛冠军后,一群河床俱乐部的职业足球流氓居然越过场边铁丝网,冲破了警察防卫线,用暴力袭击了刚刚沉浸在夺冠欢乐中的本队球员,强行收走了他们的队服作为战利品。这个团体的领袖,通常是社区中深孚众望的大人物,比如横行80年代、绰号“祖父”的博卡足球流氓头目胡塞·巴黎塔。1997年,巴黎塔因敲诈、洗钱、蓄意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相对于球迷的观赛习惯和足球流氓,某些东西更加根深蒂固,不可动摇。阿根廷足协主席胡里奥·格伦杜纳,已经占据了这个位置30年之久。作为阿根廷足球界操控者的典型,身为独立竞技俱乐部前主席的格伦杜纳既是一名钢铁工业巨头,也是UCR的地区领袖。一旦某家俱乐部资金周转不灵,格伦杜纳就要求唯一有权转播阿根廷各级足球赛事的TSC电视台(主要股东包括阿根廷最大的有线电视体育频道TYC和国内首屈一指的媒体巨头克拉林集团)向俱乐部预支未来的转播利润分成,另一招就是要求政府直接减免俱乐部所负担的债务——截至2009年初,这一数字共计8600万比索。不过就在当年6月,这一心照不宣的暗箱操作失灵了,各俱乐部拒绝了TSC电视台提供的共计4164万比索的“援助”,并要求将未来6年共计2.47亿比索的转播利润分成提高一倍。作为回应,政府终结了TSC电视台长达18年对阿根廷甲级联赛的独占转播权,并允许各俱乐部自主决定其比赛转播权归属。然而和这个国家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政治权力分配游戏一样,谈判过程仍然由格伦杜纳一手操控,远离公众视线。 这种情况下,似乎这一切要随着与阿布关系密切的伊朗籍富豪基亚·霍拉布钦在2005年入主巴西圣保罗豪门科林蒂安俱乐部而转变。作为搅乱巴西职业足坛的一条生猛鲶鱼,霍拉布钦正在把欧洲各大联赛高投入高回报的赢利模式引入南美。在此之前,位于美国得州达拉斯的希克斯、缪斯、塔特与福斯特投资基金向圣保罗的科林蒂安俱乐部注资,而瑞士知名体育营销公司ISL则成为弗拉门戈俱乐部的股东,在渴望早日接受先进管理制度的拉美中产阶级职业精英看来,这些外来因素将清除如水蛭一般吸附在拉美足球身上的腐败、舞弊和随意性,代之以职业化的道德规范、现代管理理念和资本增值。 然而,外国投资者并没有能够按照贝利所期望的那样,将南美足球打造成为世界足球的NBA,原因即在于,无论是作为俱乐部管理层还是普通球迷拉美人,都顽固地拒绝效法欧美职业体育赛事,将俱乐部当做股份公司来经营。在普通球迷看来,这群贪婪的外来掮客只会搞破坏:帕玛拉特居然改变了帕尔梅拉斯俱乐部队服的颜色;在科林蒂安和弗拉门戈,外国投资者居然把俱乐部明星球员卖给了同城德比的死对头。在苦苦支撑两三年后,外国资本和管理机构逐渐撤出,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在2008年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狂欢节游行上,一辆主题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花车获得了奖项:茫然无措,探寻自己所在的爱丽丝,似乎在暗示,尽管色彩绚烂,但阿根廷人民对于包括足球在内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未来仍然一无所知,充满疑虑。■ (感谢理查德·朱利安诺蒂和托尼·梅森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日 01:31
“这种多变、狂热、敏感而浪漫的特点,似乎都浓缩在阿根廷第一位全球性足球英雄,迭戈·马拉多纳身上。”梅森对本刊记者说,“一个出身下层,粗鄙、任性、沉溺于药物而不能自拔的足球巨人,与资源丰饶却在经历政治与经济动荡阵痛,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拉美国家现状却非常契合。”与贝利不同,马拉多纳似乎就是足球界的穆罕默德·阿里,其魅力不仅在于场上表演,也缘于对全球资本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反抗:他公开谴责美国对于古巴的经济封锁,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私交甚厚。直到今日,阿根廷球迷仍然固执地相信,马拉多纳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药检丑闻是一桩阴谋:诸如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家族,本着对1990年世界杯上意大利惨遭阿根廷淘汰的旧仇进行报复的缘由调换了球王的尿样;但其中最惊世骇俗者,就是1995年著名体育评论员费尔南多·内姆布罗撰写的报告文学《无辜》:这本著作言之凿凿地将驱逐马拉多纳的始作俑者直指美国中情局。在内姆布罗看来,这一行为,不仅能“阻止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最主要国家赢得世界杯”,更旨在“打击拉美足球,打击阿根廷的民族自信,更打击了古巴”。他坚称,中情局特工迈尔·肯尼迪支使一位拉丁裔神父,在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之前,向前来祷告的马拉多纳分发了一块含有违禁药物成分的圣饼。而国际足联药检机构也在中情局的暗示下,在恰当的时机对阿根廷国家队进行了突击药检。 “阴谋论,是缺乏全球化视野和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把握能力的第三世界民众,解释所有复杂现象的本能工具。”杰佛里·托宾在《足球阴谋论,中情局,马拉多纳与拉美大众批判》中这样说。无独有偶,1974年至1982年的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梅蒂诺,也卷入了贿赂丑闻,据称,他和国内以及欧洲一些博彩集团达成了协议,让阿根廷队在未来的世界杯中故意输球。 这些层出不穷的猜疑似乎说明,在阿根廷乃至大部分拉美民众眼中,世界级足球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的“平等原则”一样,永远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 穷街陋巷中的足球政治 乌拉圭人曾谑称,自己的祖先是阿兹台克人,而阿根廷人的祖先则来自船上。确实,与足球这一舶来运动一样,移民也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初迅速发展的动力。来自欧洲的移民潮,使得阿根廷全国人口从1869年的170万上升至1914年的790万。鉴于阿根廷出口和农业经济的中坚产品畜牧业与谷物种植并不需要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个国家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1910年,产业与服务业工人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人口的60%左右,其中大约一半是意大利与西班牙移民,年,阿根廷接收的净移民数量高达350万,为其提供谋生之道的是毛纺织业、肉类加工、造船厂、码头搬运以及邮政、铁路等因出口而蓬勃发展的公用事业。 孕育阿根廷足球的温床,就是各大城市中被称为Barrios的社区。1910年,仅仅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超过300个大小不一的足球俱乐部。与英国移民建立的学校球队和早期职业俱乐部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场地,经常在Barrios附近的空场,甚至街边组织比赛:萨斯菲尔德俱乐部成立时,球衣配色是一片纯白——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廉价的一款设计。至于前胸那个大名鼎鼎的蓝色V字,则是因为最初一批队服的订户,一支橄榄球队始终没有提货,从而使刚刚成立、手头拮据的俱乐部以不可思议的低价买下了这批烂尾货。1912年,由英国移民和中上阶层为主的52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自己的“阿根廷足球协会”,而152家工人阶级贫民俱乐部则联合在一起,宣告了“阿根廷足球联盟”的诞生。两者的比赛风格也泾渭分明:前者强调身体对抗、战术纪律的英式比赛风格,而后者更注重即兴发挥,以炫技表演的“克里奥”(Criollo,原指南美洲本土白人)风格招徕球迷。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曾在《潘帕斯草原上的X光》中描述说:“(跑马)赛道和足球场代表两个政治团体,前者代表着冒险、动荡、傲慢、中央集权和君主制,后者象征着体力劳动、充满激情的斗争、混乱和民主。”这一点从河床和博卡青年的历史渊源中就可见一斑:两个知名足球俱乐部有着相似的起源。它们的球迷都是博卡地区周边的工人阶级和赤贫的外来移民:河床实现了移民寻找全新自我身份的梦想,博卡则在本地工人的汗水与团结中找到了安慰。顺便说一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其原籍早从意大利、西班牙变成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相对贫穷的邻国——这一点经常被博卡球迷用来嘲笑自己的老对手。 在这种情形下,阿根廷独有的足球文化应运而生。1920年,著名的全国性足球杂志《ElGrafico》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阿根廷和它的南美邻邦一道,开始打破欧洲国家对于这项运动的垄断局面:1928年,阿根廷国家队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牌,两年后,又在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上名列第二。博卡青年队守门员特索列尼以及路易斯·蒙蒂、莱蒙德·奥尔西等出身贫困的足球明星,共同激发了阿根廷城市无产阶级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 很快,足球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一部分,20年代,正是以波里托·伊戈里延为代表,被称为“1880一代”的民主政治家决心使阿根廷摆脱军人和寡头腐败政治,努力将中产阶级宪政引入这个国家的岁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几百个政党领导人发现,足球俱乐部是他们接近民众,获取选票的最佳途径,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的主场纪念碑体育场以及“巧克力盒”,都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与南美洲球迷对那些性格不羁、顶撞教练的球员情有独钟道理相同,政客们必须以来自平民阶层、蔑视权威的反叛者形象出现。同样,身为社区领袖和企业大亨的俱乐部领导人也乐于借助政党参与政治,足球俱乐部成为每个社区社交、运动、商业乃至公共事务的中心,经费主要来自俱乐部实权人物的捐助;激进公民联盟(UCR)的实权人物佩德罗·比德盖安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的创始人,到今天,它的主场仍以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来命名。 这种足球与政府之间的互相提携在高举“民众主义”旗帜的庇隆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体育运动成为民众主义者动员群众,塑造其民族自信心与国家认同感的工具。1947年7月,庇隆政府骄傲地宣称,阿根廷已经偿清了所有外债,次年,将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铁路和电讯企业收归国有。在年之间,劳工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增长了25%。大名鼎鼎的总统夫人爱娃·庇隆于1950年捐助成立了阿根廷青少年足球联赛——爱维塔青年冠军杯,作为她丈夫旨在提高城市工人阶级福利的“正义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948年拍摄的电影《Pelotadetrapo》(布球)就是一部将足球与国家主义情感结合的代表之作:男主人公戈穆努阿斯是一位因心脏病而被迫退役的明星前锋,然而,为了帮助国家队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中战胜宿敌巴西,抱病上阵的戈穆努阿斯在射中制胜一球后倒在了绿茵场上。 尽管到了60年代,庇隆主义失去了曾经的魔力,逐渐退出了阿根廷政治舞台,然而这种紧密提携的关系却留存了下来。1967年,本菲尔德俱乐部主席瓦伦丁·苏亚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倒台,就像它不会允许自己倒台一样!”阿根廷经济从50年代开始,饱受通货膨胀和农产品全球价格下跌的打击,但这并不妨碍历任政府向那些负债累累但闻名遐迩的俱乐部慷慨解囊。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政治化足球”的后果,就是任何一次绿茵场上的失败,都会成为阿根廷民众宣泄对于现实不满的导火索,尤其是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刻。日,在西班牙世界杯揭幕战上,卫冕冠军阿根廷输给了传奇门将让·马里·普法夫领衔的比利时队,次日,英国宣布马岛战争结束,岛上剩余阿根廷军队投降,愤怒的群众在五月广场和玫瑰宫前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声名降到谷底的陆军只能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温和派退役将军雷纳尔多·比尼奥内取代被迫辞职的加尔铁里出任总统。此时,阿根廷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200%,100比索的硬币已经完全退出了流通,恼怒的群众很快发现了它的新用途——在足球场和游行示威中投掷裁判和警察。在那首阿根廷足球观众咏唱的口号歌曲《Hayquesalter》(你必须跳起来)中,被重复多次的一句就是“你必须跳起来,必须跳起来,不跳起来的就是X”。此时,“X”不再是1978年世界杯冠军决赛时的“荷兰佬”,或者马岛战争起间的“英国佬”,而是“军人狗腿子”。 4年后的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终于在球场上报了一箭之仇,在1/4决赛中以2比1淘汰了英格兰,马拉多纳在回忆中,这样描述比赛之于阿根廷大众的意义:“我不否认,我们赢得了某些超越一场足球比赛之外的东西,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我们这些足球运动员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虽然在比赛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跟马岛战争无关,但谁都知道那是在说谎!在我们体内,仍然可以感到疼痛,从在那个岛屿上牺牲的阿根廷子弟身上传导过来的疼痛……” 对于阿根廷,甚至拉美社会大众来说,日,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举行的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更为真实和可感知、可参与的战争。与此相对的,正如巴里·列文森执导的《摇尾狗》中映射的那样,许多生活在CNN和网络时代的美国民众,甚至坚信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虚构的真人秀,远不如一场“真实”的NFL或者NBA赛事那样值得关注。“1994年美国世界杯,阿根廷的出局,不仅是马拉多纳和一支球队的失败,更是自庇隆时代以来,足球,民众主义与阿根廷国家精神三位一体联盟时代的终结。”杰佛里·托宾写道。 野孩子与全球化时代 正如全球足球爱好者用“桑巴”来形容巴西足球运动员富于韵律和想象力的动作,阿根廷足球独特的风格,似乎只能用探戈来比拟。1961年,捷克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卡尔·克罗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南美人,无论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都拥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自然球感,更灵活的脚踝,协调性和弹性,也许他们只需要欧洲球员60%的训练量就能轻松保持状态。” 和足球一样,探戈源自阿根廷港口城市糜烂嘈杂的酒吧和风月场所,只有在著名探戈作曲家、歌唱家卡洛斯·加丹尔出现,并逐渐在巴塞罗那、巴黎等大西洋对岸的港口城市中大受欢迎后,才逐渐被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所接受。 最初,精通此种舞蹈的是被蔑称为“Compardrito”(阿飞、混混)的下层阶级青年。“他们的特征是,一口Lunfardo(融合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下层阶级方言)到处留情的风流种子,有过犯罪前科,身体精瘦结实,如有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耍诈、欺骗或者动刀。”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足球——全球化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作者理查德·朱利安诺蒂对本刊记者说,“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面对侮辱时绝不退缩。一次潇洒的折腰,向对手要害部位致命的一刺,或者一次潇洒的胸部停球转身过人,都巧妙地将想象力、身体控制与破坏性结合在一起,从而通过羞辱打击对手,赢得街头声誉。” 很明显,对于阿根廷球员和球迷来说,保持个人风格,有时比胜利更加重要。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足球不过是一项“缓慢、粗糙、野蛮的欧洲人游戏”,然而拉丁美洲人的表现却证明,技巧与天赋可以弥补体力上的不足。1990年世界杯,比拉尔多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在决赛中输给了联邦德国,他的前任梅诺蒂曾激愤地表示,他平生第一次以自己的阿根廷人身份为耻。这种耻辱感不仅来自失败,更来自阿根廷足球风格的丧失:空有马拉多纳、布拉查加和巴尔达诺,却没有酣畅淋漓的配合和神来之笔式的进球,居然要依赖点球才能淘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似乎这也能够解释被誉为“下一个马拉多纳”和最后一个具备“传统”式背景的阿根廷足球明星、出身城市贫民窟的中场天才奥尔特加,在初涉西甲时只能委身于中游球队瓦伦西亚。 对于阿根廷乃至拉美国家城市贫民来说,足球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机会,一代代球星是在尘土飞扬的街头、海滩磨炼自己的技术,而一代代的球员都不乏模仿的对象和激励自己的目标:小罗模仿罗纳尔多,罗纳尔多的偶像是独狼罗马里奥,而罗马里奥和这两位晚辈都崇拜贝利。1970年,跟随贝利在第九届世界杯上夺冠的巴西后卫卡洛斯·阿尔贝托说:“想看最炫目的足球表演,你就必须去街头。”大小罗分别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和阿格雷港的贫民窟里,他们的足球启蒙几乎一模一样,踢着空罐头和塞满纸的袜子,把木桩和自家的狗想象成防守球员。 截止到200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共有22个贫民窟,总人口数量达到12万,大部分人月收入不足300比索。从马拉多纳、罗马里奥到卡尼吉亚,出身于这里的天才球员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野孩子”(Malandro),这是民众能够给予他们的最高荣誉称号。“走进贫困的社区,在那些陈旧、低矮、潮湿,用铁皮、废旧木板和塑料布搭建的低矮建筑中,每一栋里都住着一位膝边环绕着五六个孩子的母亲,她会告诉你,全家的希望都集中在某个野孩子身上。”朱利安诺蒂告诉我们,“他伶俐而狡黠,捡废品,卖报纸,替人扛行李或擦鞋,并借此每天带回足够的食物或钞票支撑整个家庭,他能够像风一样在街道上奔跑,戏弄警察,如同他轻松地在那条狭窄到仅供两人并行的小巷中,用赤脚拨弄着那只破旧的足球晃过防守者一样。” 然而,正当体育不可避免地被全球经济一体化重新塑造的同时,拉美足球也未能置身事外。自从2004年以来,在全球顶级联赛中淘金的巴西球员数字达到了惊人的249人,小罗纳尔多和梅西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在自己国家的球场上表演,他们甚至并非是巴西和阿根廷能够培养的最佳足球运动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欧洲顶级足球联赛中身价最昂贵的球员。不仅如此,足球明星本身的特质也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从雷东多到梅西,他们已经演变成了郊区中上阶层文化和全球性奢侈消费的代表,2009年夏天,梅西刚刚收到了巴萨开出的税后1250万欧元年薪的合同,除此之外,他还是爱彼手表、阿迪达斯、百事可乐、微软X-box360游戏主机等产品的代言人。在全球化媒体和体育职业营销时代之前,球星仅仅是本地社区的英雄,体现的是某种狭隘的文化特质,对一切外来者抱有敌意。然而在当下,他们除了拥有非凡的技巧和身体,还必须是娱乐明星,个性必须拥有某种超越国籍、种族甚至性别的亲和力和某种令观众莫名激动的X因素,其身边必须有各不相同、令人艳羡的异性作为陪衬。比如梅西身边的阿根廷名模兼电视主持人露西亚娜·萨拉萨尔。 然而,拉美球员的出色发挥并不能掩盖这块足球圣地身上散发的腐败气息,以西方视角来看,阿根廷乃至南美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极端不称职:在24支巴西甲级俱乐部中,只有6家赢利。2002年,里约热内卢的弗拉门戈俱乐部负债超过1亿美元,主场最昂贵的场边嘉宾席位也是油漆斑驳、木料发霉的陈旧座椅,通向盥洗室的破旧走廊墙壁上满是粗口涂鸦,地上尿迹斑斑——许多固执的观众坚持认为自己一旦离开座位,肯定要错过某个精彩的进球,总是就近解决了事。阿根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随心所欲的阿根廷足协每年几乎都要为联赛炮制一个不同的体系,制定出五花八门的新规则,甚至有时连门票收入都要被当做进入附加赛的条件,赛程被形形色色的锦标赛和杯赛分割得七零八乱。刚刚踏入职业联赛的年轻球员仿佛置身于200年前的南美奴隶市场——劳工证必须上交俱乐部,从而迫使他们失去了迁徙、转会甚至参与薪酬协商的权利。不仅如此,欠薪成了阿根廷足球俱乐部的惯例,2009年,大约有1/3的顶级俱乐部没有按时给球员支付薪水,总额达到惊人的3800万比索。在这种情况达到顶峰的1997年,忍无可忍的阿根廷职业球员终于举行了一次罢工。相比之下,巴西的情况似乎要好些,这部分也要归功于传奇球星、曾担任体育部长的贝利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其国际影响力:2001年3月,巴西正式通过的《贝利法案》,允许球员自由转会,普通劳动法规在足球运动员身上同样有效,各俱乐部应和企业一样公开账目,建立经理负责制。 另外一个令人挠头的因素,则是被称为“Barrasbravas”的职业足球流氓:他们大多年龄在20岁至25岁之间,除了负责在比赛日与敌对俱乐部的球迷斗殴,有时还充当俱乐部主席的保镖,并负责在其竞选时充当打手并定期从俱乐部领取薪酬和球票。根据统计,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仅仅是为“Barrasbravas”提供机票一项,就花去了各足球俱乐部大约150万美元。2000年6月,当河床队最终在萨斯菲尔德体育场击败费罗铁路西部俱乐部,夺取当年联赛冠军后,一群河床俱乐部的职业足球流氓居然越过场边铁丝网,冲破了警察防卫线,用暴力袭击了刚刚沉浸在夺冠欢乐中的本队球员,强行收走了他们的队服作为战利品。这个团体的领袖,通常是社区中深孚众望的大人物,比如横行80年代、绰号“祖父”的博卡足球流氓头目胡塞·巴黎塔。1997年,巴黎塔因敲诈、洗钱、蓄意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相对于球迷的观赛习惯和足球流氓,某些东西更加根深蒂固,不可动摇。阿根廷足协主席胡里奥·格伦杜纳,已经占据了这个位置30年之久。作为阿根廷足球界操控者的典型,身为独立竞技俱乐部前主席的格伦杜纳既是一名钢铁工业巨头,也是UCR的地区领袖。一旦某家俱乐部资金周转不灵,格伦杜纳就要求唯一有权转播阿根廷各级足球赛事的TSC电视台(主要股东包括阿根廷最大的有线电视体育频道TYC和国内首屈一指的媒体巨头克拉林集团)向俱乐部预支未来的转播利润分成,另一招就是要求政府直接减免俱乐部所负担的债务——截至2009年初,这一数字共计8600万比索。不过就在当年6月,这一心照不宣的暗箱操作失灵了,各俱乐部拒绝了TSC电视台提供的共计4164万比索的“援助”,并要求将未来6年共计2.47亿比索的转播利润分成提高一倍。作为回应,政府终结了TSC电视台长达18年对阿根廷甲级联赛的独占转播权,并允许各俱乐部自主决定其比赛转播权归属。然而和这个国家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政治权力分配游戏一样,谈判过程仍然由格伦杜纳一手操控,远离公众视线。 这种情况下,似乎这一切要随着与阿布关系密切的伊朗籍富豪基亚·霍拉布钦在2005年入主巴西圣保罗豪门科林蒂安俱乐部而转变。作为搅乱巴西职业足坛的一条生猛鲶鱼,霍拉布钦正在把欧洲各大联赛高投入高回报的赢利模式引入南美。在此之前,位于美国得州达拉斯的希克斯、缪斯、塔特与福斯特投资基金向圣保罗的科林蒂安俱乐部注资,而瑞士知名体育营销公司ISL则成为弗拉门戈俱乐部的股东,在渴望早日接受先进管理制度的拉美中产阶级职业精英看来,这些外来因素将清除如水蛭一般吸附在拉美足球身上的腐败、舞弊和随意性,代之以职业化的道德规范、现代管理理念和资本增值。 然而,外国投资者并没有能够按照贝利所期望的那样,将南美足球打造成为世界足球的NBA,原因即在于,无论是作为俱乐部管理层还是普通球迷拉美人,都顽固地拒绝效法欧美职业体育赛事,将俱乐部当做股份公司来经营。在普通球迷看来,这群贪婪的外来掮客只会搞破坏:帕玛拉特居然改变了帕尔梅拉斯俱乐部队服的颜色;在科林蒂安和弗拉门戈,外国投资者居然把俱乐部明星球员卖给了同城德比的死对头。在苦苦支撑两三年后,外国资本和管理机构逐渐撤出,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在2008年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狂欢节游行上,一辆主题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花车获得了奖项:茫然无措,探寻自己所在的爱丽丝,似乎在暗示,尽管色彩绚烂,但阿根廷人民对于包括足球在内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未来仍然一无所知,充满疑虑。■ (感谢理查德·朱利安诺蒂和托尼·梅森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阿根廷红虾 的文章
- ·90分钟阿根廷红酒对瑞士几个角球
- ·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总共进几个求
- ·明天凌晨期待阿根廷国家队干掉德国,哈哈,
- ·ote3欧版触摸屏幕返回键的灯会亮S阿根廷国家队谁上风?
- ·阿根廷jumbo retail公司付款刷信誉远程付款如何
- ·连海渔业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渔船今年6月有没有回国的
- ·90年阿根廷杜高卫冕失败听说是被国际足联阴的是不是真的
-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4月29日是宠物日吗?为什么?
- ·老马一共获得了多少荣誉呀 能带领阿根廷时间夺冠吗
- ·西班牙跟阿根廷 西班牙语是不是连在一起
- ·半决赛阿根廷vs乌拉圭迎战巴西,在哪个体育场举行比赛的?
- ·在阿根廷红虾如何登陆呱呱财经
- ·为什么阿根廷不愧第一白人国也是白人 可是身体对抗差欧洲那么多
- ·阿根廷签证坐拥世界最强锋线,进个起怎么这么难.不说
- ·冰冻阿根廷大虾怎么做好吃红虾应该怎么做
- ·阿根廷红虾超级杯有没有人玩觉得特别延迟
- ·阿根廷红虾夏季五角赛初春的校园王北辰
- ·阿根廷红虾怎么做对人体的益处有哪些?
更多推荐
- ·第24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中国歌手最高奖是什么奖时候
- ·动漫里主仆结婚后结契动画怎么关向孩子解释从前的关系?
- ·跪求一部日本好的电影推荐下,挺早期的
- ·求一本忘了小说名字和主角名字怎么找的名字
- ·刘在石丝袜套头是无限挑战 综艺 刘在石哪一期
- ·锐豹户外正品t6led固态强光头灯灯自行车灯双用4节18650锂电池可以用多久
- ·帮帮忙哦!!请问那云 顶赌 场现在在哪的呢?之前我还有地址的!!!
- ·aj4奥利奥男女款区别款有这种鞋垫吗?
- ·郑恺素描拿笔姿势势是怎样的?
- ·华莱士kfc大薯条多少钱钱
- ·我想知道在北方建一个50*21*2的标准石家庄室内游泳馆馆需要投资多少钱?有稍具体点的数吗?地是自己的。
- ·砖大脚尺寸依次是什么意思
- ·怎样重生成为军嫂的小说一名月 嫂呢?
- ·奥运金玉章现在市场价今年如何
- ·襟江小学三十班描写足球描写拔河比赛的片段段
- ·克洛普在球员时代曾经为美因茨大学打进过多少粒进球
- ·最近18中学校是否澳门塔蹦极死过人人?是的话叫什么名字
- ·qq梦之队专属头像马刺队莱纳德会出专属吗
- ·在健身的时候可以喝水果乳酸菌饮料什么时候喝吗?
- ·90年阿根廷杜高卫冕失败听说是被国际足联阴的是不是真的
- ·狂野女猎手价格王撒放器材批发 啥价?
- ·+38202415010是哪里的号码号码
- ·谁还有柴静穹顶之下视频被删的视频?要哪里才能找到啊?
- ·我要视频网频
- ·长春市有没有丝足会所谁会丝足保健的,本人想学习下,最好是有视频。谢谢
- ·巨炮战队序列号领取礼包的序列号是什么
- ·百度360有钱联盟邀请码的邀请码怎么获得?没有实体店可以吗?个人可以吗?怎么获得?
- ·求一篇部队训练典型校园广播稿稿
- ·怎么使用3dmax注册机使用方法,有高人在吗?留Q
- ·在生产超微晶铁芯部门毕业实习周记报告可以写什么
- ·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监局青铜峡市牛头山农历3月15日旅游开车上山要通行证怎么办理?
- ·求タイムファックバンディット 时间よ止まれ ジム编 浅野唯种子~兽皇48部全集种子
- ·求《对我说谎试试 电视剧》全集下载呀~谢谢!
- ·婚前协议王琳杨树手机铃声是什么歌叫什么歌名
- ·吾爱破解论坛邀请码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