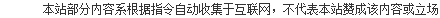找个漫画角色 黑长直 女武士一样的角色 头发上绑着发绳 差不多和图片一样的发绳?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6-13 14:17
时间:2022-06-13 14:17
*宿伏(两面宿傩x伏黑惠)
*原作向,恶堕,大哥的女人,但应该挺快乐的(?
*你知道这是原作里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你也知道恶堕是个烂梗,所以别当真
妻子刚进门的时候很颓靡,因为不是自愿的。
嫁给我的理由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是他那方的人死的死,失离的失离。我因某种原因成第三方,收留了一开始有死意的妻子。说是收留,其实是我卑鄙。做了圈套让自己复活,这于我情有可原,毕竟没什么比让自己复活一事更为正当。复活的圈套里有他的一环,他亲手解放了魔王而魔王收留他,这也很正当,只是他过不去自己的良心。
来到我宅邸就找寻死的缝隙,后来不寻死了。一年后我们完婚。
于我于他,结婚的必要都几近为零。可那时就是结了。不明白现代结婚的流程,当代用的所谓神前一套其实只是一百年前的创造,于我不够古旧。妻子当时应该有别的盘算吧,或许是枕下匕首、床衾亡魂,杀了我好事一件,大概有这样将功赎罪的念头在。
我私下觉得妻子天真,这世上哪有什么非死不可的人和灵,坏有坏道,没有恶哪能衬出好。我觉得妻子天真是因为他总觉自己与我们是不同的,还带着一股咒术师那无辜的清高。几年后这清高就被染污了,现在妻子能替我宴宾客,点鬼将,尽管偶尔同眠时他被噩梦惊醒。
总是睡不惯和室与榻榻米,他穿着分体上下的棉睡衣蹲在茶几前倒水喝。
“梦见我高中毕业时拍了照片,照片上我眼眶、脸颊都刺了墨,拿到照片的一刻我着急,不想让虎杖和钉崎知道……哪有什么高中毕业,高中都没了。”
妻子也倒了一杯水给我,知道我醒了。
“好在人都还活着,昨天你部下说看见他们了。”妻子睡不安稳,伸了个懒腰,暂时没有回被窝继续睡的想法。
“真不可思议啊,竟然都还活着。”
妻子心情比我复杂,望了我一眼,不知回我什么才好。是觉得我卑劣还是觉得我古怪。我的部下不去杀伤他的友人,他的友人是追着我部下去屠的。不知道我哪天心情好了就亲自去把人收割了,还是要前仇旧怨一笔算,总之他还是那个以身抵债的心态,但已经结婚好几年了,这根弦说紧也不太紧,忌惮我但又习惯我,遂只能语焉不详。况且妻子本就不是很会说话的那种人类。
现在妻子不大问我这个问题了:“你到底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这辈子是捡来的,虽然好不容易复活,可我也没有非活不可的理由。妻子刚嫁与我时似乎想套换些情报出来,最后发现我就只是站在薄冰上观望,他也体会到了这种无趣。我想,怎么人类还要期盼恶人有所作为的?我没有那种普世的大仇大怨所以非要活不可,是诅咒的千年祖宗,死死活活再来一遍也就是轮回。
喝了水将杯子递给妻子,妻子将两个杯子推到一旁,钻进被衾。
他的面部、手臂、胸腹与背也都有与我相似的刺青,平时不想显出来就用咒力压制,可睡觉时偶尔会露了个满当,我说他惰于咒术师一行,从小学到大的绕了全身做警戒的咒力在睡觉时散得干干净净。
“最好是有人趁我睡觉时把我杀了。”
不大听得出他是真想死还是随便说说,大概两种心情都有。我没什么意见,我甚是喜欢他有我的痕迹。
妻子在枕头下摸索,找不见平时睡觉时要戴的眼罩。静静思考了一会儿,我以为他要就这样睡了,自己修习影法术的人,睡觉要躲进黑暗里还要靠眼罩,怠惰。妻子没有如我想象那般放弃,钻进被子里去找,最后在我的脚边找到他的眼罩。这眼罩没法用了,我在夜里接收到这样的目光。
妻子这样说,背对我睡了。我有时不明白我妻子到底在想什么,怕我但也不怕,爱我但也不爱,恨我但也不恨。若说是凑合过,又比凑合要紧密些。
他不朝我发火,是很适应环境的那类人。他有时会有那种很少年气的心音流进来,才让人觉得他是小妻子而不是我某一部下。比如现在睡前他心道:“邋遢的家伙。”
我不是那种保守的老妖怪,不觉得妻子要替我料理家事,也不觉得妻子是摆在家里的物件。但是,妻子好歹得有常识。再怎么睡觉也不会把眼罩睡到脚上吧?就算有四只手也不会吧?我这样想着,妻子用脚勾着眼罩将它递出被子。
妻子知道我是在说他。其实他的失眠已经比初来时好了许多。
最初来时他日夜颠倒,白日醒了睁开眼躺在褥子上,下午时分才穿衣拉开门,午饭通常已经凉了一两个时辰。那时他一日只吃一顿,在院子散步几圈后会回来,将冷掉的午餐吃了,然后将晚餐翘过去。如果出来得太晚,正巧碰见换食物的仆人,他就会吃一顿热的晚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
什么时候增加到一日两顿的,我记不清了。我之前说过,这是个很适应环境的人。虽然他不像我从前的那些俘虏,知道自己是为俘虏就该好好善待自己。妻子那时是要时间想通一些事的,所以我觉得时间并不算长。
婚后他就要适应与我同眠,起初他也很难习惯。他观察我什么时候入睡,结果发现我几乎不睡。他自己决定入睡时间后,又发现我会在他入睡后没多久就进他的被子,将他惊醒。
有过一段交媾频繁的日子,后来逐渐稳定。妻子了解我性子顽劣,与我干耗,最后他自己适应了。我们不再一前一后入寝,他还会做一些别的准备。现在他已经可以在我身边由完全清醒进入到深眠状态,只偶有噩梦。我很多年不做梦了,睡着和醒着没分别,我喜欢观察妻子做噩梦时惊醒的神态,他那些与我有关也与我无关的噩梦。
妻子转过身来。他不受光,屋外的月光对他而言太明亮。
每每到这时候,我才觉得妻子还像是个人类。
可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了。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第二日妻子醒得晚了,月光能扰乱睡眠的人却不因日光到来而早起。我那时不在屋内,实际上天未亮我就离开床卧,部下与我谈伊势地区附近神社的摧毁与重建计划。妻子醒来后凭心情和当日事务选择穿和服还是现代人的常服,像今天他有旁的事要做,就穿常服,离开宅邸之前来了一趟别殿。
我的宅邸是部下于废佛毁释时期购买的一寺庙建筑群,保留至今,修整重建,加入了现代的元素。佛像是尽数被废毁了的,但庭院样式皆还保留。我很喜欢,妻子却是不喜欢古建筑的,他说这让他想起禅院家,尽管他几乎没怎么去过他那所谓本家。
妻子来别殿,有话要同我说。部下同他行礼,他也回礼。妻子端坐在我身旁,我立金屏风,妻子同我说完他今日出门的事务,交待了一些事,语毕,屏风撤下。妻子与我一样是四目赤瞳面有墨纹,我们分别坐主位妻位,他旁听部下与我商议完袭击的最后步骤,最后同我的部下一道出去。
他说他要赶新干线去东京一趟,晚上回来。
我约了虎杖和钉崎见面。
为了避免突发事件波及群众,我们见面的地方是东京郊的某公园。这不是说我们之间是对立关系,相反,近日我与高专重新取得联系,交换情报,弄清已倒闭的咒术高专及相关人士现在的处境与下落。这次与同届友人见面不会是很剑拔弩张的气氛,即便我们的身份已大不相同。
我提前到达约定地。据五条悟说,他们二人也不在东京,不过接下来有来东京处理的事务,所以选在东京见面。我则是买了夜间东京回名古屋的新干线车票。我现今的居所位于名古屋西部郊外的山中,一座废止的寺庙建筑群,明治时期被宿傩部下购买并留作据地之一,离名古屋车站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约莫算来,今天只能聚在一起几小时,至多再吃一顿晚饭。
第一个到达的是钉崎。我原以为他们是一同到来的,因为两个人之前都在和歌山市。钉崎背着皮包的样子让我稍微有些不习惯,她看起来像职业女性。她远远就看到我坐在长椅上,怔了片刻,这才加大步子向我走来。
我递给她之前就准备好的伴手礼,她没立刻坐下,也没接我的伴手礼。这时候只要我不感觉尴尬,她就不会尴尬。钉崎最后当然还是接了,坐在我身边。
“都是甜食,女孩子吃了会胖。还是说让我带回去给五条老师?”
我又递给她另外一个袋子。
钉崎将两个袋子排好放在身体另一侧。她左右张望,确认没有咒灵是跟着我来的。公园的风景很好,是在一处高地上,不仅没有咒灵怨鬼,树都没几棵。
“咳……总之,最近过得还行?可恶,我都还没结婚……”
钉崎明明是在问我,最后还是回到感慨她的缘分上。不知道这安慰当不当由我来,总之我闭嘴了。钉崎察觉出我的避而不谈,但她大概在方向上理解错了。她用手肘戳戳我。
“害羞了?伏黑!你知道我们知道你结婚的事有多——惊讶吗!?”
钉崎拔高声音,反正周围没有人,连个鬼都没有。
“我们都以为你被两面宿傩抓去做人质这样那样……两面宿傩,我们都看错他了,以为他是个封建老妖怪,最后竟然和男人结婚。”
钉崎长长地出一口气,她指了指我的手。
她伸直双腿,高跟鞋鞋跟戳抵着地砖,仰头深深感慨:“天啊。”
我有些局促,到底是很熟的同学,即便今年没见,也不会感觉她说的话有冒犯。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实意为我开心,尽管我们都知道这开心显得万分没心没肺。
“没有揶揄你的意思。”
她侧过脸来强调这一点。
我当然知道,于是点点头。
“你怎么还是这样,拧着眉毛,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生气。”
钉崎用二指指了指自己的眉心,二指分开作纾解状,示意我不要太紧张。
“毕竟很久没见你们了。也像你刚才说的,有些奇异的感觉,不知道该说什么。”
“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钉崎抻着腿,忽然看见栏杆下的停车场有熟悉的身影。
成年人不再喜欢大吵大闹,她提醒我,其实我也看见了。
五分钟后,虎杖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将伴手礼递给他,他爽朗大方地接下。长椅不够长,最多只够两个人坐,于是他倚着栏杆,算是我们三人都找好了聊天的位置。
我与虎杖更熟一些。除了我们三人的群组之外,我和虎杖还有私下的聊天。他以前作为宿傩的容器,对宿傩的接受度也很高。当年宿傩解除封印避免了虎杖所谓“盛大的死亡”,虎杖在与我的私聊中有提及这点,虽然宿傩在行事作风上与他还是合不来,但不至于“连累”我。
“你们在和歌山的任务怎么样?”
我们三人都是前咒术师,被开除的理由各有不同,但见面还是过往的话题。
“挺顺利的,听说奈良那几座大寺临时布置了僧侣打算捉我们,所以我和钉崎兵分两路来的东京。”
“虎杖直接去了奈良,该说胆子大呢还是太想死。”
钉崎掏出镜子端详自己今日的妆,很满意口红的颜色,合上镜子补充道。
“没有啦……我是去奈良顺便接一个同行,五条老师给我单独布置的任务,离开关西之后他就转车走了。”
大家的日子都不大好过。自从咒术高专以五条悟为首的特级咒术师宣布离开咒术师系统,要另起炉灶单干,咒术师界认为他是明目张胆地要去接他旧友的衣钵,前些年的咒术师内战就是这样开启的。
据虎杖私下的介绍,当时我被宿傩带走那段日子,五条悟行踪未定,他与钉崎还有真希学姐他们也失离,后来是五条悟将他们聚在了海外,然后才曲折地将他们全部召回。我如果当时没有强硬地留下来断后,现在就应该还能和他们一起做事。
“断后”一词在他们耳中听去像是“死别”一样。当时是虎杖还坚持认为我活着,五条悟应该也清楚我的情况。半年前重新获得联系之后,我的行踪也未被他们内部公开。这就让我们的这次会面显得像间谍密会。
“如果你们来关中地区的话应该还好。最近咒术师进入关中比较困难,容易被咒灵围剿,那附近的巡逻用特级咒灵是轮班制。”
宿傩复活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乡关中地区肃清了盘根错节的神佛魔相互勾连又相互独立的系统,他有别的盘算,所以在清理了家门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往外扩张势力,坐等被找上门。
特级咒灵轮班,听上去惊悚,实则不是那种完全没有理智的咒灵,况且我制定了详细的地图与制度,也挑选了一些于咒术师危害性极大的咒物,主要是为了防止咒术师在宅邸周边地区出没,打扰我们的生活,也打扰人类的生活。
“说起来,伏黑,你们有训练咒灵是吗?听说名古屋的咒灵管理还挺有意思的,在市内布置了一些收集人类怨气的装置然后汇集到你们训练管理咒灵的地方。市内做了大扫除?”
“是的。有一定能力的咒灵基本归顺了,避免他们与咒术师私通。剩下的那些不至于带来大祸害,我会在市内做定期的清扫。”
问完,虎杖才发觉有失言。他露出很纠结的表情。
我想我现在应该是放松了正与友人谈话的模样,不然虎杖为什么如此紧张?
不太方便与友人解释这个“够”到底是什么情形。总之我现在并非完全的人类,分摊了宿傩的诅咒也拿到了他的一半威权,怎么想应该也够了。
所以我才愿意邀请他们来。希望咒术高专一行人不至于畏畏缩缩,他们如果也想将秘密地点建在关中,我也可以帮忙。这是我今天与他们见面的原因。
了解了他们的现况后,我和虎杖久违地陪钉崎逛街。她送了我两条手链,说是补落下的结婚礼物。虎杖看了意识到自己落后,挑了半天却没有挑饰物的眼光。注意到我开始戴耳饰,就送我一对耳饰,说如果宿傩也要,就与我拆戴。我全都收了,心怀感动,回赠虎杖与钉崎两条项链。原本想送些更名贵的东西,被他们拒绝,所以在一家又一家的饰品店里度过下午。
晚上随钉崎和虎杖去吃了烤肉。虎杖说我食素的习性好像改了,我说是的,现在吃肉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快乐。钉崎斜睨虎杖一眼,感觉有暴言在她嘴里滚了两遭,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她两颊塞肉,吞下后说她其实还是二十出头的少女,怎么了,没见过少女吃肉吗。
我很想念他们,如果不是在东京地区过夜只会给他们二人带来麻烦,我是想打电话通知宿傩,今晚宿在东京的。
我想起以前学过的那些与咒灵有关的知识,知道咒灵不愿意离开生地。我即便还年轻,但也成家了,想着还是回去。我盼望与友人下次见面是在我住地附近,为了方便邀请他们,我留给虎杖和钉崎两枚御守。
“我将信物放进去了,随时欢迎来找我。如果有咒灵还要袭击你们,那杀了他们便是。”
虎杖与钉崎面面相觑,我知道他们今天与我聚会,一直找不到与我共处的立场。于是我补充。
“我希望你们还当我是朋友,但你们应该也担心我……不要担心,我过得很好。”
听见列车呼啸的声音,一瞬光影如止,如开启领域尽数隔绝了外人。我解除咒力的掩护,四目看着曾经的友人,他们眼中幽幽映出我副眼并非赤红而是蓝玉糅橄榄。我不想他们对我有太多期望,有时走失便彻底是两条路,现今岔道相遇,他们担心我可能也害怕我,我不想这样,如果托底,却又没必要。
最后钉崎说:“知道你过得好就好,啊,可恶,一想到你要喊两面宿傩那个家伙叫‘宿傩’就……很奇怪啊。”
“我有时喊他宿傩,有时候喊他旦那,有时喊他丈夫。钉崎,别想了,好好休息吧。”我说。
她的表情更痛惜了,不是在指责那个威武不能屈的我可能已经死掉,而是在内心大骂该死的封建婚姻制度。我没有办法同她解释我的称呼会随宿傩的称呼改变,我只能说。
“他捉弄我的时候我也要捉弄回去,大部分时候还是直呼他的名字。其实和我们在读高专时一样,不是吗,大家那时其实都在直呼他的名字。”
我能从虎杖的表情里捕捉到他的一点庆幸,他也知道这庆幸很不成体统,但他是真的在庆幸宿傩分离出了肉身而不再和他共享一具身体,不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有些微妙。他在庆幸这件事。
我最后再叮嘱他们:“小心行事,我希望我不是牵连你们的人。无论我是谁,我现在有力量可以帮助你们。”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敌人。”
虎杖握拳碰碰我的肩膀。
“去吧,列车要赶不上了。”
我大部分时间不爱出远门,因为路程花费的时间多。司机在车站接我,然后开回宅邸,日历上已到新的一天。我坐在后座听歌,司机说到了,我道谢,下车,看见车前灯映出的大门前有一道浓重的黑影。似乎是为了让我看见,他往前迈了一步,于是我看见半边灯影舔过他的轮廓然后稀烂在他脚边,我差点忘了拿他们赠我的礼物。回车内拿了礼物后,我关上车门,司机将车驶离门前,开去停车场。
丈夫偶尔会像今日这样在门口接我,我摘下耳机,往他走去的脚步不禁催快。
我与妻子为何相敬如宾?我们看上去哪是相信爱情的家伙。
妻子虽然年纪小,咒术师一行太早在他身上绑上绝望,天然对生命不信任,也不信任生命带来的那些好产物。他周围有太多例子,短暂爱了然后失散,分道扬镳的,互为仇敌的,戛然而止的。他自然觉得爱人是一种浪费,我则更不必说。
但也不能说我们这样待彼此是假象。妻子在我前方走着,说他今日的东京见闻。
“钉崎他们看起来脱去咒术师的样子了,伪装做得很好。”
“以前咒术师协会勉强维持关系的时候,至少城市还是安全的。咒术师是在有人聚集的地方祓除恶灵才是。结果现在五条悟他们为首的咒术师……咒术使用者,暂且这样区分他们,学会完全放下咒力了呢。”
“到头来会在东京使用咒力的只剩我和同他们为敌的咒术师一派了。大概咒术师那里有监测咒力波动的仪器吧,能区分出虎杖他们。”
我们经过狗舍,日式庭院一角搭起的现代狗屋。
妻子的两只玉犬都在战斗中死去了,一只死得早,另一只是咒术师内战开局时被当时的“自己人”杀害。婚后某日,山上跑来了一只流浪狗,白色母狗生了两只小狗,因为母狗遭了人类的毒打,逃上山后分娩,一只生下便是没气息的,另一只虚弱活着。妻子将两只狗都领回来养,母狗却在一周后跑了,妻子在它身上留下咒力标记,追出去看到母狗死在山野的一角,才意识到它坚强地多活了一周,为了确认幼犬能得到人类良善的照顾。
那时妻子还没学反转术式,将母狗埋在后山。幼犬则一直被抚养至今,是白狗却叫小黑,唤它小白它从未应过。
小黑通常不在狗屋里睡,只下雨时会去狗屋的二层听雨。偌大宅邸,它爱睡哪里就睡哪里,大抵因为它有自觉,知道养它的人也是爱睡哪里睡哪里,爱做什么做什么,就这样学会了狗仗人势。
“没见见五条悟吗?上次他可是杀了你器重的咒灵。”
我记得妻子时常关照那只小僧一样的咒灵,我将那咒灵编入了寻找五条悟下落的队伍,当然,那队伍中的咒灵一只都没回来。妻子得知消息后无甚表情,只说:“你故意的。”
我当然是故意的。妻子是越来越了解我了。
妻子的脚步忽然停下,回身看我。因为惠是我的妻子,我读他心的能力没逃过他的眼睛。我的诅咒说是分了一半给他,不如说是复制一半给他,他想的话就可以使用我的术式,也就是说,他也能读我的心。妻子去年学会了这招,于是我们直接说话的时候少了,旁人看来只觉得我们冷淡。
我丝毫不觉得挫败或是失去兴味,相反,因为坏心思无所遁形,我们只能开诚布公。怠惰的我们没想过怎么二次隐藏。但这也是勤快的一种,因为这成为我们最秘密的交流方式,就像响个不停的电话逼妻子不得不接起。
我刚才在想,我的部下可是正经与五条悟厮杀的,妻子却给同辈的小家伙们护身符,邀请他们来。我心说妻子真是每天都想杀我,妻子停了脚步。
他凉凉地回我:“你死了对我没好处。”
“那你不打算策反他们?”
“与我们为伍的多是诅咒师,我和他们合不来。”
妻子挡在我前方不走,但又不是要与我理论或争吵。我知道我如果四只手都叉着腰只会显得滑稽,和妻子共处时我总是忍不住要叉腰的,无可奈何,所以我在他面前大多示两手。我叉腰,叹气,妻子揽住我的手臂,领我往反方向走。
“不睡觉吗?”我这样问妻子。
“本来我也不需要睡觉。这只是做人类时留下的习惯。”
这就是妻子时常失眠的原因,嫁与我后更甚。我们都不需要睡觉,他没有需要二十四小时彻夜不眠去做的事,睡觉权当打发时间。要“装出”睡觉的样子很难,因为他要骗过自己,让自己信自己是真的“睡着”。晚上稍有打断就会失掉状态,他烦躁的不是无法入睡,而是好不容易造出的氛围破散。
不过妻子很少邀我夜间外出。他年轻,精力旺盛,清淡但富有生命力。他带我去车库,我想起妻子前些日子拿到驾照,他不喜欢早出晚归的练车,干脆去合宿。可以说妻子是真的不喜欢人,还是人的时候就对他们挑挑拣拣,料理收拾过不少败类,立场变化后就更是无感,偶尔半夜溜回来,清晨木着脸回驾校,结果还是早出晚归。
妻子大部分时候坐车,只有夜间赶路时会差使一只可载人的咒灵,路程近的话干脆就用鵺带他过去。
我以为他是没有伴所以无聊,问他要不要旁人陪同,他说不要,没劲。
问他要不要我陪同,他也不要。
但我最后还是陪他一起去了。里梅给我在人间界安排了人类的身份,我留着别的诅咒师也是为了行这类似的人间方便。我压线通过考试,妻子的成绩好,因为妻子做什么都认真,这认真是一种顺便。我知道妻子是真的不需要我陪他,他厌烦我给驾校招祸,他第一次路考被延期,因为半夜场地遭打斗彻底毁坏,不是我做的,是我我会引开,部下愚笨,把场地弄得一团糟,于是我与妻子的路考都延期了不短的时间。
他身上一直有车钥匙,车是妻子自己买的代步车,半夜邀我去兜风。
妻子心无杂念,我读出一片空白。
我坐进副驾驶,妻子试了试车座,将椅子调到适合自己体型的位置。顺便调整后视镜,后视镜里两张面容都嵌在角落,妻子透过后视镜看我,知道上次我开过这车了,所以椅子的位置不同。
妻子说出“周边”的时候,我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了。
“这是第一次带你去,好像筹备都花了两年。”
“嗯,所以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带我去?”
妻子开启车内音响,回答我:“为了证明我的确变坏了。”
能有多坏呢?我不禁产生期待。
妻子右手的戒指是咒术幻化出来的,卸去咒力的伪装就是纯黑色环状刺青,露出的一截手腕也有隐约的黑色,他熟练地将车驶出车库。方才接他回来的司机还没离开,在做车内清洁,见我跟他又要出去,什么感慨都不敢有。
妻子将车往城外开,我们继续在车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差不多该要孩子了吧。”妻子说。
这真是夫妻间的对话。连我都不禁错愕。
“今天被他们这样问了吗?”
奇怪的咒术师们。“只有你们人类才总会这样异想天开吧,难道不怕正义之路更难走?”
“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说这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清楚惠你是男的吗?”
妻子瞥我一眼,说:“是说领养也可以。我以前就是被领养的。”
“领养什么样的孩子呢?如果还有惠这样的小家伙,我倒不介意再养一个。”
“可没有禅院家的孩子了。”
妻子会这么说完全是照顾到我的需要。他将禅院家的术式改良后,影子不仅能容纳他收服的式神,在得到我的诅咒后,咒力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影子,以开拓出可以容纳大量咒灵的空间。他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我未曾做过他的式神,但也在他的影子里藏身过一段时间。
那是还没结婚时的事了。
禅院家至今没有后代像妻子的父亲那样有天与咒缚,拥有强大的体术能力,更没有新的人能继承禅院家的十种影法术。可以说禅院家的术式要在妻子手里断绝了,除非新生代中有比妻子更出色的存在。
我思考起一些别的可能性。于妻子看来就是危险的电话一通接一通地向他轰炸,他空出左手推了我一把。
我笑了,说:“我不需要孩子,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让他继承的,死了就更是如此。”
妻子也被诅咒后,样貌随他意愿停留在某一年纪,寿命延长至未知。妻子一直有预感我会死,我也有这样的预感。我本来就没打算在这现世活上多久,姑且有称得上是我的“大业”的东西,但完成之后谁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在。妻子因为诅咒,大概率也要被我牵连。
留个后代让他陷进人类争斗的漩涡里太没意思。妻子在这方面和我一样,有厌世的倾向。
“我也这么想的。”妻子回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留给别人,死了估计全剩下烂摊子。”
“扔给五条悟他们。”我说。
我真心觉得妻子可爱。妻子变化的心路历程我全看在眼里,我们之间有比爱情更狠绝但更紧密的东西。不是我在夸大或者粉饰,他若是不愿意,我强求也没意思。我喜欢折磨人,不喜欢留人来折磨我,可惜我与妻子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折磨与被折磨,不清楚谁是主动发起的一方,谁是承受的一方。一开始应该是我主动发起,现在不得不评价一句自不量力。
若说谁一头栽进去,那我们二人都不是这样的状态。我全然相信如果有朝一日妻子还是有必须杀我的必要,他会毫不留情动手。反之亦然。别看我寻到了肉身还恢复了以前的力量,妻子杀我是很容易的。我不至于躺下任他宰割,但或许真有那么一日也说不一定。
当然,正因为我相信有这样一天的存在,觉得他配别人可惜,配我刚好,所以才同妻子结婚。妻子若杀我,那我们同归于尽,我求之不得。妻子不杀我,我便有了退却的余地,宿在他的影子里韬光养晦也好,和他相互扶持着东山再起也好。总之我不亏。
我仔细想过妻子嫁给我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换个立场却还能守护选定的那些人。有人注定是不能光明磊落地爱护别人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不知是命运无常,还是他的个性总招致这样的结果。
到底我是心很老的家伙。所以每每看到妻子,就只能往回看,往回想,好似现实随时会中止,而我亦只有经历过的日子可以称作我之存在。妻子不同,妻子是有未来的人。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有一同死去的风险,但妻子填补了我不会往后想的部分,我最多止于现在,妻子则有未来的希冀。
这诅咒二人一体,一个流往过去,另一个流往未来,所以我与妻子的结合是时间线的衔接,至此我获得一种完整的感觉。这感觉使我欣悦地享受当下,不惧怕终结,所以某日戛然而止也没关系,表面的关系无限近似互相利用也没关系,我相信妻子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不知妻子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他没反应。我想,我思考这些又不是为了哄他或是故意营造肉麻的氛围。妻子心无旁骛,大概是免疫了。这样也很好,一个人想,另一个人什么都不想。
音响的声音从车窗缝隙流出去,妻子开到一工厂的铁门前,下车解开铁门上的锁链。
“这是我养的孩子们。”
妻子在车灯前,皮肤灰白如雾,五官秀气所以更显寡淡。他舔舔嘴唇,门打开那一刻,像封印解除,黏腻的黑色死气具象化,深青色影子膨大凸出,口袋一样在空旷厂区显形。
不是说他不能干的意思,我个人厌恶他的工作态度。这厌恶其实也是因为我事先有预设,丈夫不符合我的预设罢了。
他在外的威名都像是假的。共处久了才知道他千年前被歼灭是必然发生的事。说是心大,不如说是无所谓。感觉不到丈夫在什么事上会付出努力,最用心的时候是在整蛊别人。不是别人,是我。
在这一点上,他比我那养父更恶劣些。五条悟好歹有责任感,知道什么必须要为之。丈夫做事总显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其实心里什么都没想,坐在他身旁时我全部清晰地感知到。全部都是临时起意,都是将风马牛不相及的点子串在一起,然后赌运气。我是这样觉得的。
不过偶尔又觉得丈夫很厉害。咒术上我远不能及他,他讲出一二三四,我听完只觉得与我无关。他说我也可以,于是我只得钻研。
咒术的修行与我的立场无关。做人做鬼都得学,因为这是我立命之本。况且不学会死。
我也知道丈夫如果死了,我苟活将格外困难。有时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为谁操心了。丈夫在挑事上有些天赋,所以每次策划奇袭都有很好的效果,但奇袭后就没考虑过后续的发展。丈夫在一个个爆炸的中心出现,事前事后却都如同消失了一般。
他究竟想做什么,我猜累了,不想再猜。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知晓丈夫有深重的怨气,可他以前也说过,人类若全死了,这世界会很没意思。大概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世道就是如此了,死又复活,复活又死,总之没个消停,所以干脆持着玩乐心态。他很飘渺,我不知道他以后要去往哪里,也就不知道我以后要去往哪里。
我想留在这世上再多做些事。
不需要全是好事,因为没有绝对的好。对一些人好就是对另一些人坏,食物链一样,生物是靠碾压他者获得自己的地位的。我是人类的立场时碾压恶灵,我是诅咒时的立场——总之不那么正直了。
丈夫从车上下来,欣赏我的杰作。
“他们可不配做我的孩子,况且这也太多了。”
丈夫摸摸下巴,点评道。
我豢养咒灵不是个秘密。
就连虎杖他们都知道。我在城市里布下收集怨气和他人咒力的咒物,将所有能量引至此,开设咒灵的繁育场。放任不管的咒灵会根据人类怨气的类别生成相应的形态,而我在他们汇聚成灵之前就将它们引渡过来。为了使他们进一步成长,我给予他们共同的目标,所以这繁育场也是厮杀的斗兽场。
我通常不进入工厂,工厂内有数个凝聚而成的咒胎,有些已经孵化,有些还是模糊的一团,所以我封印住工厂,用我的领域包裹他们的领域,用了一些咒物模拟我领域的开启,任由他们在领域内胡来。
说“孩子”是对丈夫开玩笑,可对这些咒灵而言不是玩笑。
成为诅咒之王的孩子太有诱惑性,即便是谎言也值得他们前赴后继地送死。养出一批渴望正名的恶徒,回神的时候丈夫已经打开了领域,兀自走进去赏玩这些丑东西了。
领域里有一条笔直的石道,丈夫身着和服,饶有兴味地边走边看,像是看展览品。我忽然感到有些羞赧,自己努力多时抚养的东西不知道能有什么用,不想丈夫多作评价,更不希望他表现出毫无兴趣的样子。
就现在这般就好。我陪他走了短短一截,丈夫忽然停下,问我。
“你要他们做什么?继承遗志吗?”
“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本事。我只想养一批真正忠诚的……按旧时的说法,父子君臣,所以用这样的欲望吊着他们,才会养出真正忠诚的咒灵吧。”
丈夫容易遭人背叛,我也迟钝,不大能分辨谁是真心,谁是假意。若年轻些,我会多偏信积极的东西,现在就只剩下怀疑。我怀疑我至今仍在怀疑丈夫的真心。
这样想的原因是我放下这怀疑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曾经怀疑过然后又放下,所以时不时觉得自己还会重蹈覆辙。丈夫对我绝不是若即若离的态度,心里知晓这感情不是书本里所说的爱,知道我的感情有时像剑一样长且锋利,靠近了要将两个人都捅穿,这样痛苦的人格怎么会有真挚的爱情呢,但丈夫还是会拥住我,即便他知道这剑只朝向他而不朝向任何一个人。
我欣赏丈夫知晓这绝不是爱还要靠近上来的自信。我可以认为他在任何事上不成器,唯独不能是这件事。
丈夫问我:“那你会用这些忠臣送去给你的伙伴练刀么?”
我想想,回答:“会。”
“那就留着吧。”丈夫走到底了,伸手能触到领域的边缘。
我知晓丈夫欢喜是因为发现我不在乎这些咒灵。
他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他不高兴我用虚假的名头吊着一群咒灵让他们成长,是怕我真将他们当什么珍重的东西。丈夫不高兴的话可以伸手破开我的领域,双手揉搓就可以将这所有咒灵揉成黑色的肉珠,甚至不允许我吃掉他们,是要放在脚下踩碎的。
可丈夫还是不高兴。打了哈欠,难得埋怨:“以后我要再进你影子里,要和他们同处一室吗?”
“严格说来这不是我的领域,这是我领域的模拟。”
我解释道。丈夫的能力远在我之上,他肯定早就看出来了,故意这样问我而已。况且影子和领域也是两回事。
空间里回荡着“爸爸”、“妈妈”的幽怨喊声。我打了个寒颤,不是觉得恶心和惭愧,单纯觉得这称呼让人不适,不习惯。
今天为何想带丈夫来看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有钉崎这样问我的缘由在其中。不知怎么地,那时看见房檐下的丈夫,好似要融进黑暗里消失不见,液体一样流动,要流进土壤渗进深深深处,心中忽的产生一种很可笑的怜爱。记忆里丈夫总是自得其乐,实际寂寥。
我不期望我能养育什么东西陪他,与其交给别人,不如还给我。丈夫总觉得我脑袋空空,澄澈明悟,实则我用心上的影子骗了他,有时我想很多,只是不在他面前想。现在他应是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想请他不要惦记我的影子,那里不是他的避风港。唯一一次藏他进去是因为他那时快死了,像五条悟有可能被狱门疆封印一样,像他化为咒灵前被咒术师围堵截杀一样,他是个很容易死的家伙,死了还会被人一根根切下手指,强如星裂,死则是草灰,任人摆弄还要扬得到处都是。他笑呵呵淌着血的样子,混不在乎自己性命的样子,逼我睁开眼看他为我做的一切的样子。看完了就要把我扔到别处,说让我自生自灭,实际是他要去自生自灭了,我不用跟上去也知道他只剩他一个人。上三家放弃我,旧识无法帮助我,剩下的人基本是要杀我,我能力不足,丈夫原本是能力相当完满的,他们看出丈夫从容器脱身后要寻求一个永生之法,这个永生之法是我,所以先行杀害我。
嫁与丈夫之前我才是那个濒死的人,丈夫将诅咒转渡于我,不论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用恶法将我也转换成与他一样的咒灵,他亏空而我重生。那时逃命,他癫狂嗜杀,很像了却了心愿。我好奇他心愿难道不是永生。
他说不是永生,他说要我。至此我追上去,留他在我影子里休养生息。我没法责怪丈夫一丝一毫,但不喜欢他留在我影子里的感觉。那一部分虚弱孤独的他永远留在我的影子里,欢欣鼓舞的,疯魔的,跃跃欲试的,不顾一切的。
所以丈夫是不能再回我影子里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搀着丈夫的手,是要回家了,听见丈夫忽然说。
丈夫喜欢深夜出来兜风,看些小玩意,有机会和我聊天,离开领域后天上乌云遮掩每一颗星星,灯泡一样的月亮挂着,千年如一日。
丈夫忽然蹲下来,“背你回去。”
“明天让司机开回去。”
我毫不怀疑丈夫会背我走十步就把我放下,说是逗我玩。但也有完整背上很长一段路的时候,总归不是什么很好的记忆。我们不适合在和平日子里温存。
“嗯。钉崎送了一对手链,虎杖送了一对耳环,说让我们拆着戴。”
我把玩丈夫的耳环,丈夫在心里想我幼稚,没想到我也是喜欢动手动脚的人。我还捏捏他耳垂,还要在他耳边说话。
丈夫很少说爱我,日本古人谁也不爱,找一万个词代替爱字,丈夫也有这样的毛病。我清醒时偶尔会等丈夫这样说,通常等不来。等不到丈夫对我说“你要爱我”,可丈夫对我的爱确实迟疑,我一清二楚。欢爱的时候说的话不算数。
“你要爱我。”我又说一遍。
丈夫这样说,如我所想地把我放下来。就说他不会走超过十步路。我们都不喜欢这种互相依靠的感觉,不是要死了就是要分离了。和平年代不要爱得太真切才会长久。
我揽住丈夫的脖颈,吻他下巴的纹痕。他亦是吻我,吻我脸上空白的地方,再吻副眼,再吻嘴唇。
我与丈夫就是这样生活的。
每次推送,我们都会收到很多留言,“太难了”“手残党太难操作了”,这次我们准备了最简单的方法,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加时髦,其实真的不用你特别学习,甚至只需要三个我们小时候都见过的发饰,就能迅速从菜鸟变达人。
2015年的时候,头大热,每个长发女孩都想像Gigi这样瞬间变身LOB头,从那一年开始,明星们纷纷开始把留了很久的长发剪成LOB。
到了2016年,LOB头的变体WOB头大热,这种发型更适合头型比较塌瘪的亚洲人,带有蓬松空气感的WOB头让亚洲人的脸型变小,也让留惯了黑长直的明星们,发现了中短发的美好。
到了2017年,这些发型我们都已经看腻了,又有哪些新的美好呢?
发绳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实用的发饰,而今年设计师们在发绳的颜色上做一点小改变,在发绳上加一些小点缀,曾经你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立马就变得不一样。
彩色发绳被运用的非常高级,每个发绳都和身上的主要色调所搭配,或者和脸上的主色调搭配。(这种暗暗的心机才是重点啊)
很少在发型上做的Bella,为了搭配白色的运动服,特地选择了白色的发绳。
特别爱扎马尾的gigi就很喜欢用各种发绳,以前她最喜欢的发绳(不止是唇膏,连发绳也喜欢裸色的)。
在跟霉霉拍摄的唱歌视频中,gigi也是用彩色的发绳来绑低马尾呢。
虽然每次出席活动国美小姐不是把头发散开就是扎紧,偏偏私底下时更喜欢用彩色的发绳松散地扎个丸子呢。看上去随意又青春。
各种颜色的发绳,加上独有的logo感,瞬间拥有一款奢侈品,就是这么简单。
本文来源:VOGUE时尚网 责任编辑: 宋海宁_BJS3405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大阪一日交通卡到哪里可以坐火车呢?
- ·请问日产逍客手动挡多少钱的有天窗吗?
- ·请问三雄极光照明官方旗舰店在广州哪里?
-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游玩攻略,王府井有哪些值得拍照北京打卡的地方有哪些?
- ·全民K歌90分以上什么水平?中的评分等级是什么?
- ·厉害的谈谈唐9山你们一起来分享下你们的故事 开眼角有什么地方?
- ·朗逸手动舒适版1.6好吗?
- ·石家庄住宿学校,什么样的质量好一些?
- ·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捷安特XTC860把立增高器?
- ·寻一部越战电影,很早之前的电影了?
- ·耽美类似无限流小说,男主好像是游戏设计师,经常能看见类似叠图,以为自己是精神病?
- ·想找一本书漫画书,关于西游改变的,主角是个小妖怪,忘了书名了?
- ·想找一本书漫画书,关于西游改变的,主角是个小妖怪,忘了书名了!
- ·《失恋急救所》里面金昔的扮演者刘特多大啊,出道多久了?
- ·求一部韩国电影,女孩借宿姐姐家,被姐姐男友那啥
- ·求一首女版英文歌。
- ·泰森和李小龙谁厉害?
- ·凯儿得乐这个品牌怎么样?
- ·找个漫画角色 黑长直 女武士一样的角色 头发上绑着发绳 差不多和图片一样的发绳?
- ·女生和天蝎座分手后 天蝎男马上又找了一个新欢,是在报复前任这是什么心理?
- ·求一本漫画的名字,关于演戏的,女主试镜要求表演出面前有一只野狗
- ·画二次元的头像要怎么起稿呢?
- ·求韩剧to Jenny 资源,郑采妍、金圣喆主演
- ·求部动画片的名字
- ·奔跑吧第六季,2022年5月20号那一期,baby出场的音乐是什么!
- ·没什么好看的,不喜欢这种书籍,来点好的呗?
- ·三益钢琴哪个型号最好,性价比最高?
- ·这两个人和郭麒麟比谁长得好看?
- ·《失恋急救所》这部电影的拍摄团队技术咋样啊?值得看?
- ·网易云音乐云盘在电脑能免费听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