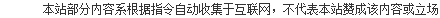我们同居了一年多,怀孕两次了。结果都胎停了。她说想去看看大师,看八字合不合?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7-03 15:40
时间:2022-07-03 15:40
我和高先生领了结婚证。一早就去了民政局,居然没有人,我们是第一对。
不用排队,我们去一楼拍照片。拍照片的小屋极其简陋,是一位和善的大姐主持工作,墙上挂着观音像,一派迷离祥和。
我正犹疑拍照的背景在哪。
大姐呱嗒从观音像前拉下一块红布,让我们在红布前面的圆凳坐好。
背挺直,头互相歪一歪,靠近一点,笑一笑。
大姐尽职地指挥着我们摆POSE。
我们摆好了,就在即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大姐又走过来,把我的长头发拉到前面,善良地说,头发遮住脸,小一点。
很好,照片里高先生又瘦又长略微蜡黄棱角分明的英俊,匹配着被适度遮挡还圆如银盘的白胖喜庆的我的脸,绝对没有PS,拍得平凡和谐,大姐有功。
楼上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小本本上盖上钢印,睡眼惺忪地递给我们,就像是80年代买了国营电影院的门票。
高先生说,你查没查黄历,这日子吉利不吉利。
我摆出汉口泼妇的样子,跟老子结婚你还敢挑日子。
高先生一脸讪笑,是是是,您说得极是,要不咱吃个包子炒肝烧饼夹油条的京派早餐庆祝一下可好。
我们进了窄巷子,在高先生熟悉的居民区里的小破店坐下,不仅包子炒肝,还大气地要了豆泡汤。
已经是3月中下旬,春天的迹象开始明显,我们拿着红本本白天在父母家显摆一番,晚上开车回自己家的时候,下起了大雪,白花花的一个世界。
我们俩不知道天高地厚地讥笑老天爷给的礼物。
我和高先生领了证不几天,就吵了一架,为什么吵,我实在不记得了,但是吵得很激动,我抄起手边的结婚证就撕了。唉,肯定是刚领证,得瑟,一直把它们摆在桌面上耀眼,也不及时收好,所以让我撕得这么顺手。
高先生有点懵,毕竟还是年轻,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拿起一块抹布,走进厨房,开始擦灶台油烟机,使劲擦,很卖力,仿佛想讨好我,也仿佛是自己解气。他擦到天快亮了,才卷到沙发上和衣睡觉。
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主动找我说话,我还是没好脸色,拿着劲儿。
我们单位前几天安排我们去体检中心体检了。
今天那个体检中心有个大姐给我打电话。
她说,小伙子,你先别害怕,也许是我们体检中心弄错了,可能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大姐说我的血液检测有一个项目,CEA,很高。
正常值小于5,我300多。
那就是他们弄错了呗,一个体检中心,又不是什么医院,出错是经常的吧。
我轻描淡写地回应,似乎有些没消气,对于高先生找的话题有些不屑。
嗯,我也这么想。那个大姐让我再去正规大医院查一查。
高先生去朝阳医院又验了一次血,CEA果然奇高。
给他验血的医生说,你体检时没查过甲状腺么,摸着不太好。
你知道北京有两个肿瘤医院么,W医院和E医院,你去看看,哪个都行。
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对肿瘤医院,我们一无所知。
我给李老师打电话,他母亲经历过乳腺肿瘤,我问他有没有熟悉的路可以指一指。
李老师打探一番,给我回了电话。
你们明天一早去W医院找A主任加号,早点去,很早,不早加不上,就说是乳腺科的赵大夫介绍的。
这么容易就能搞定挂号这种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自己人脉了得啊,我颇为得意。
一大早,我和高先生开车从望京奔到医院。太早了,我们要赶在医生屁股刚刚坐在椅子上开门迎客之前加上号。
我们到得够早,加号很顺利。
过了七点半,乌泱泱的病人,挤满了医院门诊大厅。看起来,他们仿佛都哭过,一张张丧气的脸,满是悲伤。
我之前不是很明白肿瘤医院和别的医院是这么不同。
我窝在车里,不肯下车,起得太早了,我恨早起,我睁不开眼睛。
我恹恹地跟高先生说,我眯会儿,你差不多时间自己去排队嘛。看完赶紧回家。
我们冷战了好几天了,难得这么早一起出门,高先生似乎找到融冰的切口,屁颠颠去医院东边200米路边的小脏摊买了豆浆油条,4月的北京清晨微凉,塑料袋油腻腻热烘烘的,他跟我说。
我像一只被娇惯的猪,皱眉哼哼。
大约两个小时后,高先生回到车里。
我还睁不开眼睛,半梦半醒之间。
呵呵。医生说的,你看。高先生掏出医生开的住院通知书。
一张B5大小的黑白单子上,诊断这一栏写着:甲状腺髓样癌?
我揉着眼睛勉强看了看。
为什么有个问号。大夫凭什么打问号。
大夫说这是基本判断,他说凭经验就是这个了,但是要等手术后做病理分析。
什么大夫。他没开玩笑。
看上去还挺严肃的,找他的人挺多的,是主任医生。
那还怎么着,回家收拾东西,住院呗。
咱俩还得分别回单位请假。
那大夫没搞错吧,别让我们折腾一通,他又说搞错了。他就摸摸,也不让你再化个验么。
我彻底醒过来了,还是一脸不相信地问。
高先生发动车,脸上挂着笑。
我说话不再阴阳怪气了,宣告我们吵架后的冷战结束。
我们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们。
从医院出来,我们懒得吃午饭,分别回单位请假,高先生后来告诉我,就是那天他去单位请假的那条路,他开车开得有些难受,心里堵着,无从说起。
回到家,我偷偷把撕坏的结婚证粘了起来。
你怎么想的呀。你不会找好一点透明一点的胶条么,粘这么丑。
我觉得天衣无缝啊。我摇头晃脑地欣赏自己的技术。
屁。你粘得这么丑,都不完美了。
我们俩和好。我把结婚证放进抽屉。又拿出来看看,嗯,是挺丑的,我手真是欠。我又放进抽屉。
其实吧,愚蠢的男人们,吵了架,不论女人歇斯底里或者撕心裂肺,吵完了,你们还是要去抱着她睡,面子先放一放,反正她也见过你拉屎放屁打嗝抠脚了。
想过和不想过了,态度是截然的。
我收拾了简单的洗漱用品,高先生藏好烟,我们去医院住院。
A主任说,要尽快手术。
办理好各种手续,高先生住进一个宽敞干净的六人间,护士立刻就不准他离开医院了,也要求我遵守探视时间,不得随便进入病房跟他亲亲抱抱的。
一开始,高先生颇有微词,后来看到护士小姐姐,眼睛极大,露出来的皮肤都白皙,头发利落的别进帽子里,脖子也是颀长的,他安静下来,嗯嗯,我不出去了。
做了各种检查,A主任把高先生的手术安排在了周五。
手术的前一天下午,护士小姐姐要给高先生备皮,刮掉脖子上面脑袋两侧的头发,便于手术。
那个下午,换药室里阳光很明媚,护士小姐姐亭亭玉立,高先生穿着病号服,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微微闭着眼睛,享受暖意和轻柔。
我声明一下,高先生很帅,182,大眼睛深酒窝,下巴有角度,没肚子有屁股,腿长到我的胸,头发浓厚。唯一的缺点是,瘦。不过,该有肉的地方,都不少,整体效果真是让人垂涎。
我后来想,他长得好看大概是当我面对一切不堪都不觉得害怕的动力。
备皮后,我的天,护士小姐姐给高先生理了一个莫西干人的发型,这叫一个帅,欢喜得我当时就想抱上去亲。
由于多次换手机,这张照片我暂时找不到了,哪天等到我找了,我一定发出来。
你们想象一下,一个穿着条纹病号服,英俊略带羞涩的莫西干男人,坐在阳光里,身边一个穿白裙的姑娘,轻叹着摆弄他的头发,是不是油画。
傍晚,护士嘱咐高先生洗澡清肠,也让我回家,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我在西三环上开着车,还唱着歌,什么口水歌我也不记得了,我的歌声多难听,我是记得的。
我想起来,明天就要手术了,我们还没有把这事儿告诉父母。
高先生的爸妈,平凡朴实,一辈子默默过日子的人,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能承受独生子的病况。
我打给了高先生的姑姑,她是老高家的主心骨,跟高先生也非常亲。
怎么了,感冒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季节不能随便脱秋裤的。
姑,高鹏明天要做个手术。
姑,高鹏得了癌,可能是癌,做了手术才知道确切是不是。
甲状腺髓样癌,大夫说的。
在哪呢,你们,我们现在来找你们。
姑,我在回家路上,明天一早您到医院吧,明天手术,不知道几点,说是要排队。
姑,您别直接告诉他爸妈吧,您说呢。
开着车,我开始有点难受,是不是该哭一场了。
天一亮,我就奔赴医院,赶上护士小姐姐给高先生做手术前的准备,插尿管。
六人间,隐私用挂帘隔开,我把头伸进帘子。
高先生一脸不好意思的愤怒,说。
护士小姐姐握着高先生的小弟弟,专心插管子。
那什么,护士,不能不插尿管么。
高先生龇牙咧嘴地问,可能有点疼。
不能。到时候你弄一世界,谁收拾。
护士小姐姐一口京腔,好犀利,我喜欢。
姑也到了,提着好多吃的。
高先生的妈妈也到了,显然是哭过了。
姑,妈,他不能吃,他等着手术,昨晚清肠了,水也不能喝。
不由分说,我在病房香喷喷吃起来。
高先生烦躁不安,忍不住骂我。
你还是不是人啊,我昨晚6点以后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还清肠了,你当着我吃这么香。你还减肥不减肥了。
病房里其他老头也哀叹,是啊是啊,你干嘛吃这么香,还吧唧嘴,不道德。
姑和妈,不说话,或者说两句闲话就问他,疼不疼,哪里疼。
高先生特别无奈,我还没手术呢,我疼什么呀。
快到中午了,高先生还没排上手术,一直饿着。
我擦了嘴上的油和牙齿上的香菜,去找Z主任。
A主任刚从一台手术上下来,在办公室里休息。
我只好厚着脸皮开门进去。
A主任趴在桌子上,抬起头,有点不耐烦地看着我,他好累的样子。
A主任,我是1病房6床的家属。
A主任,给,您多费心。
你再休息会儿,我跟他说再等等。
A主任这个好字,说得温柔。
桌子上是我包了3000块的信封,也不知道这算是多还是少,我有点忐忑,放下信封快速闪出了他的办公室,好像是第一次干坏事,自己脸红心跳的。
走到病房门口,就听到护士小姐姐严厉地批评高先生。
你怎么回事,你这都要上手术台了,还把烟放在枕头底下。你是要在手术台上抽呀。
高先生死皮赖脸,笑得挺好看。
哎哎,别拿走别拿走,我,我最后再抽一颗。
你瘾这么大呢。赶紧的啊。
抽完这颗烟,高先生就被推走了。
我和姑一直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不是电影中的样子,那个走廊里全是人,站没处站,坐没处坐。天不是很热,空气中还是有馊味儿,等候的家属们表情麻木,也交谈也哭泣。
我不知所措,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等待,每每和姑的眼神相撞,就肤浅地微笑。
姑,没事的。一会儿就出来了。
姑也很配合,平时爱大声说话的爽气人,现在一言不发。
等了好几个小时,好多家属都被通知可以走了,我们还在等,等到了座位,等到走廊里几乎没有人。
手术室的门开了,A主任端着一个不锈钢的医用腰形盘招呼我过去。
这是从他脖子里切除下来的组织,你看看,右边甲状腺全切,淋巴锁骨都做了清扫。
盘子血呼刺啦一大堆,黑红黑红的,是动态的,滴滴答答,刚切出来的新鲜。
你看看你看看呀。A主任催我。
你睁大眼睛别看我,你看看我切下来的东西。
我,我不敢,我小时候晕血。
会有报告。回病房等着吧。
高先生躺在病床上,麻药还没有醒,他不帅了,头发乱七八糟,脑袋上脖子上全是纱布,鼻子里插着管子,手背上戳着打点滴的针。
姑和妈看着他,姑变得镇定,妈一直抹眼泪。
我又敲开A主任的办公室门。
A主任趴在桌子上,抬头看我。他的眼睛肿胀,揉着睛明穴,一副特别特别累的无奈。
我又递上了一个信封。办公室里没别人。
A主任,我是1病房6床的家属。
您辛苦,我来谢谢您,您别介意。
红包不用给两次。A主任说得直白又大气。
A主任,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您辛苦,也问问我先生的情况。
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医院治疗。
他是比较严重,两个月后还要做第二次手术,你准备准备。
嗯,很好,我给两次红包,一点也不亏。我心里赞美着自己何其聪明。
A主任,他这么年轻,为什么。
现在的人生病,原因很复杂。
不是,但是这个病有可能是家族性的。就是有可能他们家亲戚有,而他父母没有。也有可能他们家谁也没有,他基因突变。
张主任知道我没什么医学常识,尽量把话说得简单。
这个医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洁有力,我都不知道下一句怎么问。
A主任,网上说甲状腺的肿瘤都不是什么大事。
我用google,不用百度。
A主任笑了笑,懒得理我的样子。
甲状腺肿瘤也分很多种,髓样癌是凶险性比较高的。高鹏的比较典型也比较严重,肿瘤侵蚀了很多地方,包裹了喉返神经,所以只能都切下来。
您是说您切了他的喉返神经?
嗯。右侧的。比起救命,喉返神经只能这么处理。
哦,您切得对。切得对。那以后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该再问什么了。
A主任也皱起眉头,很累很累。看在信封的面子上,我已经占用他很长时间了,他也对我够温柔了,把一半不耐烦藏了起来。
过了五一你们可以出院,两个月以后再来,切左边的。
A主任,他以后需要忌口什么的么。网上说不能吃海鲜海带。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不顺耳。
高先生终于醒过来,发现自己说不出话,呼吸憋气。
高先生求助的眼神看着医生,指着自己的喉咙,极其沙哑地问。
我的嗓子什么时候恢复。
恢复不了。以后也不会比现在好。
A主任斩钉截铁,说话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绝不给你任何不必要的希望。
高先生开始闹情绪。开始跟他妈妈和我发脾气,不吃东西。
他的注意力全部在嗓子上,根本不管癌不癌的。
我说不了话了,我以后就是哑巴了。
你不是,你只是声音沙哑,你又不唱歌。我继续以鄙视的方式安慰他。
我唱什么歌,我要说话。
我知道。你这不是说着呢嘛。
你根本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瞧瞧,高先生双鱼座自虐式的多愁善感又开始占上风。
我以后也不唱歌,陪你。
滚。你本来就唱得难听。
护士小姐姐看不下去了,也来呵斥高先生。
你得吃饭啊,吃饭才能恢复得快啊,不吃饭给你注射营养液了啊。
别别别,这么贵。我赶紧拦着。
姑去朋友家偷来好多散养的鸡下的蛋,蛋黄极黄,看起来非常有营养,临床的病人看她蒸的黄澄澄的鸡蛋羹,羡慕不已。
高先生发脾气,嫌自己妈妈给家里装修买了个便宜的马桶,妈哭了一场。
八杆子打不着的大小事情,高先生烦了一个遍,根本不管癌不癌的。
我也生气了,可是我没哭。
我给我自己的爸妈打电话,刚领证他就得癌,这种事情总归还是要通知一下家长的。
爸,高鹏是癌症。已经做了手术。
嗯,我去百度了,也查了查书,还问了问我的同学以及在医疗系统的学生们,结论是这个癌根本不可怕,切完就好了。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你要多鼓励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另外,我给你点钱。
爸,医生说他这种相对比较严重。
那就吃好一点嘛。我多给你点钱。
很好,我爸到底是老师,说得有理有据有科学高度,还攒了不少私房钱。
啊,这么帅,得了癌,不可能吧。
我大概知道我喜欢漂亮男人是谁遗传的了。
癌怎么了。我告诉你,现在社会稳定,医学昌明,管他什么癌,分分钟就治好了。怕什么怕,有什么好担心的,医生切哪里了,伤口看不看得出来,留不留疤,等他做完手术还是那么帅就行。另外,我给你点钱。
我妈一向说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排比句,非常解气。
你有什么可担心,他比你小,长得又好看,你占这么大便宜。我给你钱,你去给他买吃的。
我妈无所畏惧聪明伶俐,真是让我的世界开阔无比。
是啊,有什么啊,我先搞定高先生的吃饭问题,我爸妈说了,这是头等大事。
医院对面有一家气派的便宜坊,我连哄带骗藏好病号服躲过护士,牵着高先生走了进去。
高先生脖子上围着纱布,手背上还插着输液针头,张牙舞爪,满嘴流油。
一整只烤鸭,片甲不留。
芥末鸭掌火燎鸭心,卷了饼还喝了汤,爷是开了闸了。
你嫌医院的饭太素,你丫早说啊,至于伤心到全世界都不了解你的苦么。
自那天起,高先生是给什么吃什么,大口大口,不计后果。
看着他狼吞虎咽吃相丑陋,我们家这几个女人都十分满意。
我声明一下,我觉得A主任很好,不废话,不论是否收红包,对病人一律严肃冷漠直白准确,以自己的专业技术给你有限的安全感,斩断病患及家属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他的工作风格以及混世的态度,我是欣赏的。
作为一个肿瘤医院的医生,悲悲切切的同情心是最要不得的东西。
两个月后,我们去了E肿瘤医院做第二次手术,换医院是因为我们对第一次的仓促有些心悸,再加上有朋友、朋友的朋友在E肿瘤医院疏通,我们奢望会被照顾被重视,被医生体恤得更好。
第二次手术我们跟医生的沟通和相处也多少有了些经验。
看病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遇到的人各有不同。
高先生经历了多少苦,我没必要扒出来反复自怜,你们知道我最不擅长写苦难博同情。
那些会留在我的脑子里,多是好玩的人和事情。
E肿瘤医院的病房高级一些,都是两人间,还有独立的卫生间,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一对父女。老父亲是病人,喉癌,已经做完手术了,女儿嫁到了杭州,刚生了孩子不久,狠心断了奶,来北京照顾她爸。
看我们进来,这对父女很热情地欢迎我们,跟我们打招呼。那个女孩儿特别白,南方姑娘的秀气,一脸笑摸样,身上完全没有刚生完孩子的肿胀,她利索地收起地上的行军被褥。
高先生除了好看,敏感又善良,我这么夸他,不知道他会不会骄傲。
他看到行军被褥,赶紧跟那姑娘说。
我是北京的,还没排上我手术,晚上我回家,你就睡我这张床上,没关系的。
他看出姑娘照顾爸爸守夜,是睡在地上的。
没事没事的,我这几天都是睡地上的,没关系的,你不在我也不睡床的,医院不让的,床是干净的,你们快收拾收拾,好休息。
我们手里一边收收捡捡,一边聊起来。
她爸爸喉癌手术被割开了气管,现在气管上插着呼吸机,也靠这根管子进流食。平时这姑娘要给她爸吸痰喂营养液,慢慢地一点点灌进去,不能呛着,夜里也要经常起来检查管子是否通畅,呼吸机是不是运转正常。所以她晚上就躺在地上,躺在她爸的床脚边,她爸稍有动静,她就蹭一下站起来,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睡过了。
爸爸能比划,也能发出特别低沉的嗯嗯的气声。
他们很乐观,姑娘说话一直带着笑。
一天,她好高兴地跑进来,大声笑,爸,爸,大夫说你能吃香蕉了,我打碎放进营养液你就能喝下去了。我,我快去买香蕉。她又高兴地跑出去。
吸痰拍背喂流食擦洗身体,天气好扶她爸出去转转,她每一项都做得比专业护工还好。
比起她,我真的没那么辛苦。
她跑到卫生间,我有点恨自己嘴贱。
出来后,她说,我好想啊,想得我都涨奶了,哈哈哈,好丢人。
又过了大约一周,那姑娘突然跑进来,大叫,爸,爸,医生说你能出院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爸,你倒是笑笑啊,你不高兴么,我太高兴了。
她疯了一样地大笑,然后开始打电话。
妈,哥,快来接我们吧,我爸能出院了。我太高兴了。
原来她还有个哥哥,在北京工作,成了家,有自己的房子。
从我们住进这个病房,不曾见过这个女孩的哥哥和妈妈来探望一次。认识他们的十来天,这姑娘天天睡地上,没人换过她。
高先生说,我以后得生个女儿。一定得生个女儿。
B教授是高先生的第二个手术医生,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是他的主治医生。
B教授是知名专家,不是找了人,托了关系,我们可能也挂不上他的号。他已经退休了,被医院返聘回来,一周坐诊一次,就一个上午,你们没见过那一个上午有多少人排在诊室门口,就为了跟他说不到5分钟的话。我每次和高先生看诊时买给他的水都被他搁置。他说他一上午都不会喝水,以免去厕所。
B教授花白头发,说话中气很足,白大褂里面是干净的格子衬衣,年轻的时候应该很英俊。
他看了高先生在上一个医院的病例,摸了摸高先生的脖子,说。
去建大病历,办住院手续。我亲自给你手术。
整个过程可能都不到两分钟,我也没说上话。像其他病人一样屁颠颠进来,屁颠颠出去。
我们俩真正给他留下印象,是因为跟护士站的实习医生吵了一架。刚住院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实习医生来问病史,等了很久,也很饿,实习医生不来,在护士站耗着。
我们去问了几次,实习医生都非常不耐烦地说着什么急,回去等着。
最后一次,不知道实习医生说了什么怠慢和蔑视的词,压倒了高先生的稻草,高先生哑着嗓子咆哮起来,我也冲了过去,高亢辅助,这种时候,一定要上阵夫妻兵。
医患关系紧张啊,听说耳鼻喉头颈科的医患关系尤其紧张,因为这个科室抑郁患者更多。
一阵叮哩咣当后,B教授让冷静下来的高先生在病房等着,拎着我去了办公室。
你们以后要长期跟这个科室打交道的,你不要火这么大。
手术以后要观察,长期观察,随时有问题随时住院。
就是有了肿瘤就切,有了就切,没什么好办法。
您看看我们上次的手术,做得怎么样。喉返神经被切了。
是我也这么做。肯定是命要紧。
两天后,高先生的手术过程中,B教授在扩音器里叫我。
之前我已经了解一些手术的方案,具体的问题和状况也是要切开看的。
隔着一个巨大的玻璃,B教授在手术室,我在家属等候区。
现在手术正在进行,你们上次切右边,这次切左边。左边也不乐观,现在也发现肿瘤侵蚀了左侧喉返神经,你决定一下,切还是不切。
我已经不是两个月前的我了,我敢看医用腰形盘里的任何东西。
高先生的姑姑和爸妈站在我身后哭。
两侧的喉返神经都切断,就会引起窒息,要切开气管。
我想起了杭州姑娘切开气管的爸爸以及高先生因为说不出话来给我甩的脸子,我很坚定地说,不切。
我回头看姑,她抓着我的胳膊,怯怯地说。
我再看高先生的爸妈,他们一直哭。
你们快一点,高鹏还在手术台上等着。
我拍着姑的肩膀,像个领导。
姑,他想活得有尊严,他死要面子的,切开了气管,他会想不开的。
第二次手术结束,所有的人在慌乱中暂时平静下来。
嗯,他这么年轻,现在切了,以后怎么办。
你是对的,喉返神经和气管附近的肿瘤部分是良性的。但是一般医生都会切,因为这样是对患者保命最好的处理。
反正你签字了的,是你自己对你爱人负责,呵呵。
B教授比张主任温柔太多了。他用了爱人这个词,像个老派的绅士。
你跟我女儿一样大。她在国外。
嗯,您上回说过的,您女儿比我厉害。
她不厉害,没用得很,上次怀孕还胎停了,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这哪是医生该说的话。我彻底放松了。
B教授,我们也想要孩子。
他这样了,你还要什么孩子,以后一个人带孩子怎么办。
您要不要说得这么直接。
我这么说不是为你好么。
电视上演,医生说病人能活3个月或者3年,那都是骗人的,没有医生下这样的结论。我们对癌症患者的说法是,五年存活率。
这样说吧,五年之后,他还活着,说明医生的治疗是成功的。
五年之后就算是治愈么。
理论上是这样,但我们不提治愈,我们说存活率。
好,我明白了,反正活过五年之后,您就算功德圆满,就不是您的事儿了,对吧。
B教授居然当着我的面,抽了根烟,他的中指焦黄,是老烟民。
B教授,高鹏抽烟喝酒,他的病跟这些有关系么。
该抽抽,酒少喝点。跟这些都没关系。
想吃什么吃什么,是吧。
后来,我自认为跟B教授成了朋友,每次高先生复查,他都先跟我打招呼。
然后捏着我的大胖胳膊,笑。
挺好的,您看我白白胖胖的,这么操心也不瘦。
胖的好啊,胖了才好看啊。是吧,高鹏。
唉,果然还是个老人家,喜欢又白又胖的。
高先生无奈地呵呵呵,每次我跟B教授交谈的那5分钟里,高先生就成了局外人。
我要是没陪高先生去复查,B教授会问。
你媳妇呢,你媳妇没来啊,问她好啊。
高先生只好无奈地呵呵呵。
每逢年节,我们都会给B教授准备两条好烟,别的礼物他也不在意,我眼见着他把办公室成堆月饼送给保洁阿姨。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今年是第五年。
除了前两次慌张的手术经历,高先生在这五年中又住了好几次院,接受了好几次大手术,有惊心动魄的,也有平淡无奇的。
传说甲状腺手术后要去协和的内分泌科长期监测激素状况,我们又削尖了脑袋,挂了个号。
各种化验后,内分泌的大夫说。
你住个院吧,你可能有嗜铬细胞瘤,不知道在你身体的哪儿,要住院找一找。
好嘛,新名词,又挑战了我的医学知识,我赶紧去google学习。
在协和住院了一个月,高先生修身养性,看完了《白鹿原》。
同一个病房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得了糖尿病杵着拐杖走不了路的北京大爷,大夫让他控制饮食,他天天要吃红烧肉,他老婆不许他吃,她女儿偷偷送过来。
另一床是一个东北来的消防员的儿子,小男孩儿每天喝很多水,去很多次厕所,他因此上不了学。我很喜欢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带了很多书给他,终于有一天,他浓重的东北口音跟我说,姨,你陪我打个扑克,我不看书。他出院回东北的时候,跟他爸去故宫门口买了个漆器的首饰盒给我,大红的那种。我给他的书,他说太重了拿不动,全部留在了病床上。
那是8月份,我每天下班去找高先生,然后一起溜达到东方新天地看喷泉。制服笔挺的保安说,请大家不要在酒店前的台阶上随意落座。我们俩就是要坐,还抱在一起,牵着手,亲来亲去,素质真是不高。
一直坐到医院病房锁门的时间。
一个月后,医生通知我们出院,我问嗜铬细胞瘤找到没。
可能你们住院之前那次化验,吃了巧克力什么的,化验结果的数字没搞对。当然嘛,现在没事了,回去吧。
我不敢相信这是一出荒诞剧。好安慰。
高先生好几年都没吃过巧克力了。
反正也挺高兴的,至少高先生看完了一部那么重要的文学作品。
后来我们又经历过两次在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住院,因为缺少喉返神经,高先生一直憋气,不仅嘶声,呼吸都困难,我们希望通过手术缓解。这两次同病房的病友都是来治疗打鼾的,我们知道了打鼾是个特别大的事儿,这个鼾打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可是最后同仁医院也没把高先生的嗓子治理妥当,我们还是求告号贩子,去了协和,有一个著名的老医生从高先生肚脐眼上切了点脂肪填到了他嗓子里,声音还是哑,但是不憋气了。
再后来,高先生的肿瘤又被发现走向纵隔,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开胸的手术。
至此,高先生全身都是疤,特别有《古惑仔》里郑浩南的风采,以前是多么文弱的帅哥,现在一光膀子,连肚脐眼都能震慑坏人。
这五年中,我们俩不仅奔走了京城各种正规医院,还在我执着的错误领导下,也干了不少违背科学的事情。
比如我刚开始经常去庙里求神拜佛,还发愿不再吃肉,我还要高先生也去雍和宫逐一跪拜,高先生义正言辞地骂我。
你不要让我去跟菩萨做交易!平时你不拜,你现在才想起让菩萨力挽狂澜,你太自私了!
我觉得他骂得好有道理,我又赶紧去了朋友所在的教会,想跟上帝走得近一点。
朋友也告诫我,上帝不可试。你要信就信,你不能跟上帝说,您先帮助了我,我再信您。
我一想,也对,我这也是跟上帝做交易呢,不合适不合适。
除了西医,我们也见识了各种中医、神医,正规的不正规的,有执照的没执照的,反正都试了试。
高先生最恨我的是,我有一次听说山东特别偏僻的一个村庄里有治疗他这个病的偏方,我不顾他再三反对,逼他驱车前往,并让赤脚大姐(都不敢说是赤脚大夫)用灵丹妙药给他的小腿上烫了一个碗底大疤,并且流脓三个月。
最后去了医院,医生痛心疾首地说,你媳妇也是读过书的,怎么就好意思相信这样的事情。
至今,高先生小腿上一个圆圆的大疤,我再敢拿什么偏方或者保健品BB他,他就一伸腿给我看看疤。
这五年,我们还干了很多跟医学无关的事情。
比如高先生鄙视我求神拜佛,我就带他去找开了天眼的大师,问问我们俩到底是不是八字不合。
大师说,你们怎么敢在那个日子领结婚证,大凶。
你瞧瞧你瞧瞧,我说什么来着,当时让你挑个日子,你还骂我。
我很镇定,啪,拍了一摞钱在桌子上,大师,我们总不能离了再结,你说怎么破吧。
大师又算了个吉日,让我俩举办个婚礼冲喜。
我们这两个读过书的人还真办了,热闹非凡,正好借机感谢了一路帮助过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这五年,我们在国内经历过的所有医生,我都送过红包,我心甘情愿。
我真心不认为收红包的医生就是坏人,他们也是凭本事,世道就是这样,他们如果不收,作为病患家属,我更会忐忑烦躁,不知如何是好。当然,我不是要赞美这种社会风气,就像高先生十分憎恨号贩子,但是我们也的确从中受益,虽然这个益处也是用钱换来的,至少这么多年我们只尝试过一次通宵排队挂号还没挂上的悲凉。
多次奔波于医院,我已经练就了送红包的本领,只要涉及高先生的手术,主刀医生、缝合医师、麻醉师、实习医生、护士长,大大小小的医护人员无一例外,我会在合适的时间找到要送的人,快速消除他们心里的芥蒂,截断他们短暂的推辞,极其顺滑地将信封送入白大褂的大口袋或者办公桌的抽屉里,让收到的人舒服并有安全感。
我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表演如跳梁小丑,多少还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可爱又聪明。
只有一次,我把信封快速放入一个白大褂口袋后,我回到病房才想起来,我忘了在信封上写名字,我努力回忆自己当时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医生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谁的家属,要是他不知道是谁送的,我不就是傻逼么,我特别想大嘴巴抽自己。
也好,有了这次的教训,打那以后,我能把这事儿办得滴水不漏。
其实这五年中,还有很多故事,我实在写得太长了,你们肯定看不下去了。你们对哪个环节感兴趣,我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讲讲。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把这事儿当作了不起的谈资。
重要的是,到今年6月,就是高先生第二次手术后的整整五年了,你们能理解吧,也就是在理论上,高先生算被治好了。
虽然高先生每每复查,关于他癌症指标的数字还是居高不下,甚至不断增长,但是高先生活得很有尊严,该吃吃该喝喝该耍帅耍帅,每周踢一次足球。
B教授说,我解释不了,医学就是这么奇怪。
这五年中,我跟高先生依然会吵架,会冷战,会摔东西,我尽量摔便宜的。我才不会因为他有病就让着他,所以他经常骂不过我的时候,就说我有病。
我们的相处也很浪漫,高先生双鱼座啊,眼泪很多的,情绪一上来就感慨人生。
他搂着我,十分深情地说,要是哪天我万一……
我反应很快,万一什么,万一个屁,你要万一,你就早点万一,我六七十岁还怎么改嫁,我肯定是要找男人的。
我继承了我妈妈噼里啪啦的风采。我一直就是以这么犀利的方式撕碎高先生自我迷恋的忧伤。
高先生特别无奈,煽情的话完全说不下去,只好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老子要熬到你八十。
这五年中,他长大了,有责任有担当,注意力不再总是放在自己身上,当然他绝对没有五年前那么帅了,他肚子上些微有一点肥肉了。这五年中,我也长大了,鱼尾纹法令纹揉也揉不下去,以前骄纵的我总算理解,婚姻中和男人的相处不是要把他踩在脚底下,也不能一言不合就撕本本。
另外,我明确地认识到做什么都不能得意太早。
我和高先生是不是应该互相颁个奖,纪念一下。
这五年,没有眼泪,只有笑话。
吃奶后呕吐是新生儿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有的属于正常生理情况,称之为漾奶;有的吐奶从数量到次数与一般漾奶不同,就可能是有病,应及早诊断治疗。新生儿吐奶有一种是生理现象,这与新生儿的解剖生理特点以及喂奶方式有关。新生儿由于卧位为主,所以胃的形状和位置是横位, 所以喂奶后婴儿一活动,奶就很容易从胃中又返流到食道、口腔,这就造成漾奶。漾奶量一般比较少,漾出奶量多见几口,由于奶已进入胃后,与胃酸结合,故有时吐出奶有奶块。但婴儿无任何其它症状,也不影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大多数新生儿呕吐虽不是漾奶,但也不是病理现象,主要与喂养不当有关。如喂奶量过多,奶瓶嘴扎的孔大大,喂奶过多,喂奶时奶瓶中的奶没有充满奶头,婴儿在吸奶时同时吸进很多空气,其次是母亲乳头过小且短,婴儿吸母奶时不能将母亲奶头充满口腔,婴儿吸奶时用力,同时吸进空气,另外在喂奶时翻动小儿过多,或婴儿边哭边吸奶都会引起吐奶。这些只要改进喂养方式即可纠正。正式喂奶时,母亲取坐位,把婴儿放在一侧屈曲的时上,婴儿体位稍侧位,然后把母亲奶头或奶瓶奶头塞入婴儿口腔,喂奶量要依据日龄特点,新生儿第一天约每次30毫升~40毫升,到一周未逐渐增加到75毫升~100毫升。主要是应符合胃容量,当然每个婴儿个体也有差异。每次婴儿吃饱后,将小儿竖抱起,头放在母亲肩上,轻轻拍背,最好等婴儿打呛后,即把胃中气体暖出后再放在床上,有些小儿容易呕吐者,最好取右侧卧位,喂奶后尽量不要多翻动和逗婴儿,以免奶液溢出。
我要回帖
更多推荐
- ·五一要几号免高速免费费吗
- ·新疆有哪些民族哪个是姓名
- ·乌鲁木齐到喀什旅游攻略最佳线路多少公里
- ·新疆自驾游攻略有哪些公路
- ·新疆天山天池在新疆的什么位置哪个城市
- ·求一本古言小说
- ·国内有什么付费的音乐下载网站? 要求: 1:歌曲比较全 2:音质高,一般都有flac这种
- ·“雪莲文学”是什么?为何突然火爆?
- ·阿蛮歌库显示不完歌库数据歌曲怎么回事?
- ·有没有非爽文修仙小说推荐?
- ·有没有足控的哥们儿知道 这篇小说叫什么?
- ·这个女的眼尾面相如何,是平直的还是上翘的还是上扬的,又什么说法?
- ·求一本小说名!
- ·pygame播放MP3时如何调播放位置?
- ·堂弟说我爱情剧看多了,是什么意思?
- ·陈明栋和王芮佳这个名字配不配?
- ·唱歌可以出字的软件自己唱歌可以出字的?
- ·我们同居了一年多,怀孕两次了。结果都胎停了。她说想去看看大师,看八字合不合?
- ·2021大刚读可以升请换转业吗?
- ·阴女,金4局,生肖兔命宫-亥 ,身宫-亥命主-巨门,身主-天同什么意思?
- ·Dilemma是什么电视剧里的音乐?
- ·这个女人老公人品如何,看八字说一下啦,葵酉,甲寅,己未,庚午?
- ·有师傅会看手相吗?
- ·四川省青少年足球遴选怎么才能参加?
- ·有哪些好看到炸的欧美明星?
- ·大家有存的让你觉得惊艳的女明星礼服图吗?
- ·徐沐婵 会不会 成为第二个张曼玉?
- ·梁朝伟和梁家辉谁的演艺生涯更厉害?
- ·我和男朋友说很多消极的话我说被他害了我问他爱不爱我了 他说他想si?
- ·大家怎么看待张国荣的演技呢?
- ·ikon是几代男团?
- ·属蛇农历八月晚上七点出生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