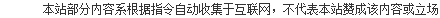夜郎音乐是真人演唱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9-22 15:04
时间:2022-09-22 15:04
南国早报 ■ 南国早报记者 李岚
萧十三郎的演出现场。 资料图片
编者按:或许,广西不是这些音乐人生长最好的土壤;又或许,音乐注定是他们漂泊在路上的一种追求。这些年,带着音乐梦想去流浪的广西原创乐队或者独立音乐人,散落在全国各地不计其数。只是,在他们的演出现场,他们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乡梓情怀。每当他们在舞台上唱起歌,熟知他们的歌迷会说,哦,这个某某,他(她)是广西仔。
“萧十三郎”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几年前,记者出差到广州,在一个昏暗的酒吧内看到一个双目微闭、气质脱俗歌者在吟唱。彼时,有人说,这就是广州民谣圈里有名的夜郎,广西合山人。
“其实,‘萧十三郎’这个名字,是在萧玲的名字和我名字里各取一个字,我们有一首作品是用《萧十一郎》里的著名小诗改编谱曲的,叫《前世之歌》。”夜郎说。漂泊在广州的夜郎,等了多年,等来了萧玲的声音。2010年,“萧十三郎”横空出世,爱恋如电光石火,歌唱亦琴瑟和同
小时候,夜郎在广西合山矿务局长大。地处桂中腹地红水河之滨矿务局,混杂了各地的矿工,也交融了各种文化。在有一首叫做《回家吃饭》的歌里,夜郎还能依稀却真切感受到当年那个大院里温暖气息:“放学了,阿合,你怎么还不回家;连猪崽都回来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从前见到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但我爸从来没拉过。”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工友才告诉夜郎,父亲生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单位文工团演奏乐器,但他的正职是钳工,操作机床时不小心夹断了食指,从此拉不了二胡,也吹不了箫笛,离开了文工团。
记忆中,只读了小学的父亲很特别。“我从小就觉得我爸跟其他家长都不一样,就算做养殖,也养一些特别的,反正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从来不跟风。”但父亲脾气很“梗”,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人,没人敢反对。“我接他接得很彻底,跟我爸是同一类人,几乎没有和颜悦色说过话”。
“那一代小孩,基本上在摔打中长大。父亲反对我玩任何游戏,希望我好好读书考个大学之类的”。但貌似冷硬的父亲也有可爱的一面。他一直偏爱民族音乐,对夜郎买回来的一百多盒以港台流行音乐居多的磁带殊无好感。但某天,听到录音机里传来林子祥的歌,居然定定地听了很久,然后夸赞不错不错。
后来,夜郎渐渐长大,读武侠成为他中学时代的一大爱好。“那时的心中,江湖还很迷人,恩怨都是别人的事,最向往十八般武艺皆备,独行天下。”现实是不“武侠”的,夜郎毕业后,被分配到水泥厂上班,做化验员,研究水泥配方。这个“要穿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工作”让很多人羡慕。身为化验员的夜郎,闲暇之余仍不忘拉几个当地音乐爱好者组乐队,练琴。
1996年,夜郎从家乡水泥厂辞职,在家练了一年琴,用双卡录音机录了第一张作品小样。那时的夜郎,能想到的“大城市”是南宁,就带着小样来南宁“考察环境”,发现这里没有能令他的音乐生存的空间和土壤。再后来,有个在广州做平面设计师的表哥,貌似跟音乐圈里的人关系不错,就叫夜郎去广州。“于是便阴差阳错地在广州一直呆了下来,到现在正好十六年。”
从“南蛮乐团”到“萧十三郎”
在广州,夜郎组过一个乐队叫“南蛮乐团”,但因为乐手生存的压力,“南蛮乐团”被迫中断。后来的“萧十三郎”,因为爱情,也因为“二人组合相对来说更自由随意些,无论去哪儿演出都比较方便,不用因为乐手没法离开工作而失去演出机会”。
乐器有鼓、吉他、口琴、尺八……很多时候,“两个人就能把全部乐器带在身上走”。有次坐飞机,那只非洲鼓不能托运,“一扔肯定会破掉”,只能随他们进了机舱,行李架上也放不下,最后勉强挤进了空姐的工作室。
“萧十三郎”也回过南宁演出,依旧在北湖明秀路口明湖大厦那个昏暗的地下停车场。舞台上,夜郎和萧玲光着脚,盘坐在地上,像一幅画,纤尘不染。一首《寂静欢喜》拉开了演唱序幕,有歌迷记得,最后他们还唱诵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萧玲接连不断吐出的歌词如同诵经般祈祷吟唱,那听不懂的歌词更令人心生安详”。
回过头看,为音乐漂泊的日子仍历历如昨,而十多年已经真切地过去了。“2007到2009年,最黑暗的时光。做音乐这么多年,身体也熬坏了,音乐也没有给我带来应有的回报。很绝望,不知道该怎么走。”很难去追溯一颗灰寒之心如何慢慢升温回暖,也许遇上了某个对的人,也许是后来内心的某种醒悟。“如同植物,在潮湿的南方,灰烬中亦有生机勃发的种种可能”。
现在,萧十三郎是个全新的组合,他们刻意搬离广州市区到了“地图上快要看不到的地方”,与白云山日夜相对,呈“半隐居”状态。爬山、打坐、练琴、研习佛理。
听过他们唱歌的一些乐评人,往往更感叹于夜郎个人的转变。有一篇乐评说:“在‘萧十三郎’这个组合里,夜郎更多居于幕后,主要负责演奏、和声,隐藏在萧玲出尘、清澈的声音后面,愈加悠扬、深远,流露着平静的禅意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美得一塌糊涂。”
对话夜郎:来这里,或许是为了离开
记者:从夜郎,到南蛮乐团,再到萧十三郎。这十多年,您个人的音乐起了哪些变化?
夜郎:这样形容吧,这三个阶段的音乐就分别像是泉水、沸水、纯净水。第一阶段就像是刚从山上打下来的泉水,看着很清很干净,但实际没多少人会直接喝它。正如一个单纯的少年靠着某些天赋或者受听过的歌曲的潜意识的影响,本能地写出了一些很单纯好听的歌;第二阶段是把泉水煮沸的过程,南蛮乐团时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乐风和很多种不同的中西乐器,试图把自己所学的很多东西融汇在一起,就像滚烫的水一样充满了激情和火热,当然杂质也开始浮现;而萧十三郎这个阶段则像是纯净水,从形式上说是个从激情到平静的过程。现在,萧十三郎的乐风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内心的安详宁静,不依赖更多的乐器和手法。
记者:你们现在在广州生活的状态是怎样的?可否描述一下?
夜郎:每年我们大概巡演三到五个月时间,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深居简出。说到创作什么的,除了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外,萧玲平时练她的南箫和手鼓,我则终日打坐吹尺八,同时手上戴着几公斤的沙袋,偶尔弹弹古琴,也有站桩和练些简单的拳脚打沙袋。对我们来说重中之重是要练好气息和定力。
记者:作为从广西出去的音乐人,广西这片土壤对您的音乐风格形成,影响大吗?
夜郎:影响当然是有的。广西一向以山歌出名,在旋律感方面很多人都有天赋,我知道的不少广西的音乐人和乐队,他们的旋律感都相当不错。我更想在旋律感的基础上去探索根源性的东西,也尝试过用桂柳话和壮话来创作。但应该说不算很成功吧。总体来说广西的音乐人都欠缺好的音乐土壤的培育。希望以后这方面能够慢慢改善。
记者:禅学一类的东西,对音乐境界有怎样的影响?
夜郎:我对传统的儒释道哲学很感兴趣,稍有涉猎。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练习着“一心多用”,比如说我平时练尺八的时候,基本上都同时一边看围棋对局讲解,一边放音乐听,一边打坐。只有到夜深人静心有所想时我才放下一切,专心吹尺八。尺八是中国一种古箫,因为太难学所以在中国失传了八百年,近十几年来才开始慢慢复兴。尺八目前来说是我最重要的禅修乐器,而实际上在生活处世中,棋道对我的影响更深,如果晚生十几年,赶上围棋的大好时代,我现在一定是个棋士,而不是音乐人。
记者:每次回广西演出的感受如何?
夜郎:其实我们这三年来每年都巡演到南宁,第一次是在地下车库的“候朋现场”来了很多人,也很安静,第二年演出质量更好,我们完全进入状态,现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只是观众减少了,大概是觉得很难做到两三个小时下来都静静的聆听。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画了一本小插画记事本送给我们,上面写着对我们音乐的感受。
记者:广西漂在外地的音乐人,是否也有一个圈子?
夜郎:在广州独立音乐界里,圈子的概念并不明显,相反广州的独立音乐人大多都不屑于混圈子,基本上都以各自发展的方式存在并努力着。在广州我平时也是偶尔和米粉乐队的叶宏钢,瓦依那的韦家园来往,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在做民谣学尺八,也都说同样的桂柳话,更容易交流吧。个人觉得广西的音乐人普遍来说旋律感都很好。
成员:夜郎(原名余志合) 萧玲
音乐出发地:广西合山、广东电白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甩葱歌真人版谁唱的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如何预约去香港需要预约吗现在?
- ·中国经济什么叫货币化化意义?
- ·拉萨大昭寺详细介绍值得一去的原因有哪些?
- ·大陆居民去内地到台湾需要什么手续哪些证件?
- ·济宁最好的养老院养老机构哪家比较好?
- ·nova5pro听歌如何使屏幕不亮?
- ·穿到疯美渣a失控前小说?
- ·癸酉丁巳甲辰庚午男这个八字格局如何,有大师帮看看吗?
- ·昨日留声馆开放在哪看?
- ·谁有2018年吉林省第二届初中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的支撑文件?
- ·八卦图写轮眼是谁的?
- ·2022年农历7月18日是属什么生肖?
- ·这个八字,喜用是啥?
- ·读书亦是读人是什么散文类别?
- ·如果赵丽蓉还在90岁的他还会不会再上春晚?
- ·2022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怎么报名?
- ·影视后期难吗?在好影课堂能学会吗?
- ·哪位师傅帮忙看看女八字?
- ·欲贷款买车,哥瑞,思域,本田XR-V选哪个?
- ·毛毛虫点读笔操作简单吗?质量怎么样?
- ·夜郎音乐是真人演唱吗?
- ·毛毛虫点读笔怎么样?有没有了解的?
- ·由“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你联想到哪位诗人的哪首诗又联想到春天的哪一位使者由“你是春天派出的153?
- ·求《揽娇》,作者林中有雾,谢谢啦
- ·求2007辣味言情小说600部
- ·戌不离兔亥逢龙什么意思?
- ·有没有大佬《医学统计学》王彤姚应水版的电子书,谢谢
- ·动漫设计是什么?
- ·求一本玄幻小说,内容是男主可以入魔越阶杀人,认识一个女的是墨教传人
- ·影视动漫是学什么的啊?
- ·影视动漫专业怎么样?
- ·现在阳光书吧受欢迎吗?
- ·有知道汇汇米老是抢不到电影怎么办?
- ·非法入境越南不交罚款会怎样?
- ·从长寿北站到长寿菩提树下农家乐怎么走,马山菩提树下农家乐有哪些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