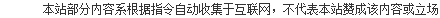你知道九鼎记漫画期刊杂志社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4-05-30 07:46
时间:2014-05-30 07:46
2013.06《教育与探索》杂志征稿
《教育与探索》系中国教育工作者协会会刊,创刊于2006年10月,由中国教育工作者协会和岁月杂志社联合举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23-1142/I,国际标准刊号:ISSN,邮发代号:14-171。
本刊已被龙源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网络媒体全文收录。在本刊发表的论文符合中、高级职称的评审,可以作为参加评职评优的参考依据。
征稿对象:
全国教科研工作者、广大教师、各级科技与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科研院所、科技教育人员、科教领域管理人员、各大院校的在读博士生、研究生及社会各界关心科教工作的人士。
栏目设置:
本刊主要栏目有:教育管理、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学科教育、高等教育、创新探索、科教信息、会员作品、学校风采等。
投稿须知:
<font COLOR="#、来稿请尽可能发电子邮件,文字稿须以Word文档形式作为附件发送,文中如有图片,应以JPG格式作为附件发送,不得粘贴在Word文档中,并应确保图片清晰。
<font COLOR="#、作者文责自负。杜绝一切不严肃的引用和抄袭,对于剽窃他人成果者,本刊将予公开曝光。
<font COLOR="#、在不改变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本刊保留对稿件的删节、修改权,以及对已在本刊刊发文章的电子版权和结集出版权。如不同意请在来稿时特别注明。
投稿信箱:&
&咨询电话: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国内 有哪些期刊杂志社?_百度知道
中国国内 有哪些期刊杂志社?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青少年书法报 书法报 书法导报 杂志;J
这都是和书法相关的,比如书法——机构刊号:期刊——媒体名称;J 中国书法11-1136/J 青少年书法41-1054/,就太多了报纸;C 书法31-1067/,如果找和文化相关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机构查询——期刊/期刊社查询——所属类型;J 书法丛刊11-2827/J 书法赏评23-1313/J 中国钢笔书法33-1036/,你自己到出版总署网站查询吧:填上你要找的关键字:解放军美术书法11-5949/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其他1条回答
环球观察,青年文摘最广泛吧
凤姐爱看的故事会,知音
还有人物读者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回答者: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燕京学堂笔谈(《读书》杂志201409)
假如我办燕京学堂
(《读书》2014-09)
”,就是不可能的意思。既然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何还要如此自作多情?因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相对来说,批评畅快淋漓,建设则困难得多。那就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是北大校长,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很有挑战性的
“燕京学堂 ”计划,应该怎么做?不提 “战果辉煌 ”,就说 “实现既定目标
”吧—为何如此低调?因北大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在享受恩宠的同时,被全国人民拿着放大镜观察、挑剔、评论,稍为偏离既定的航道,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状态下,只能小心翼翼,平安驾驶,很难期待惊天动地的制度性创新。
可是,我们又都希望北大能奋起直追,迅速地 “世界一流
”。不动制度,通过增加经费,是能提升若干水平的。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制度非动不可,这个时候,牵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及习惯思维。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谋定而后动
”。可以不断地打雷,好一阵子下不来雨;但不能没做任何预报,就来场正义的滂沱大雨。雨是迟早要下的,但怎么下、下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量、有无节奏感等,都必须认真考量。不仅要驰想
“春雨贵如油 ”的妙境,还得防止决堤溃坝的灾难;“有百利而无一弊
”的改革,那是神仙才能碰到的。很可惜,北大这回创办燕京学堂,明显低估了其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难度,未曾做过认真的 “沙盘推演
”—我说的 “沙盘推演
”,是指主事者自我设置对立面,站在另一个角度立论,来回辩驳,直到基本上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
筹巨资创建一个新的教学机构,对于北大是件大事,事先其实征求过不少中层领导及名教授的意见,不可能是校长脑袋一拍就出来的。问题在于征求谁的意见,以及如何征求,程序正确不等于效果就一定好。做过行政的人都明白,讨论同一件事,找谁不找谁,谈论宗旨还是敲定细节,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说,中层领导怕校长,普通教授则不怕,更有可能直言不讳;而同样是名教授,有人习惯于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则热心公共事务,就看你能否及时发现潜在的 “反对派
”。若真想征求意见,应该多找有勇气、有见解、有担当且历来特立独行、敢于自我立论的普通教授,既给他们解释,也听他们抱怨,甚至允诺一切可以商量,大不了推倒重来。若怕人多嘴杂,想快刀斩乱麻,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来努力解释,希望广大师生
“顾全大局 ”,这在别的学校做得到,在北大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一所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学。
平心而论,从社会募集巨额经费,创办培养国际人才的燕京学堂,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好事。可如今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对北大声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何当初匆忙上马,高调宣布,而不可以稍微等一等,多邀请敢于直言的反对者参与协商,或吸纳意见,化解对立;或调整节奏,优化计划?那样做肯定效果更好。问题在于,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初被征求意见的诸君,大都并没意识到事情竟然这么复杂。
这就说到北大人的特点,无论校方还是教授,多志存高远,擅长侃侃而谈,看不起斤斤计较,尤其不太注意细节。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
“细节决定成败 ”—谁能想到一张 “流光溢彩
”的静园修缮效果图,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我相信北大校方之创办燕京学堂,确实是用心良苦;问题可能出在悬的太高,用力太猛,操之太急,加上论述时的若干瑕疵,以致引起部分师生及校友的猛烈批评。不想
“高屋建瓴
”地说风凉话,我希望站在建设者的立场,帮着出出主意,看能否进一步完善此计划。相关意见适时提交给了校方,至于是否被采纳,不在我考虑范围内。选择九月方才刊行的《读书》杂志发言,是假定那时大局已定,风波也基本上过去了,发文章只是为了
“立此存照 ”。
都是模仿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着眼于培养国际化的
“各界领导精英 ”;也都是一年制的学习计划,为何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波澜不惊,北大的燕京学堂却风急浪高?除了两校师生处世及表达风格的不同,更因清华计划可操作性强,北大则过于理想化,不太可行。后者选择了学校中心且带有标志性的静园六院来建寄宿制书院,乃极大的败笔,此举引发了学生及校友的公愤,学校不得不做出妥协。如此
“败走麦城 ”,不全然是思虑不周,还是我所说的用力过猛,即太想把事情办好,以至于不考虑前后左右、上下里外。
在我看来,这燕京学堂即便圆满达成目标,也只是为北大增加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成为整个大学的中心。顺便说一句,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一个以英语讲授、以国际学生为对象、“肩负提供世界级中国研究教学重任的中国研究中心
”,但在整个大学处于很不起眼的位置。
我想辨析的是,为何北大这升级版的国际化计划不太可行,以及到底该如何修正。具体论述时,不断以清华计划为参照系。说北大创办燕京学堂是为了与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竞争,这本身没什么不对;两校之间你追我赶,是个好现象,只是不要因急功近利而脚步变形。记得当年北大刚创办文史哲实验班时,清华提出的追赶方案是文史哲再加中外文,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我提醒清华校方注意:学生只有一个脑袋,且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这回清华走在前,北大为了赶超竞争对手,把好几个功能不同的计划糅合在一起,表面上是
“高大上 ”了,实则模糊了战略目标,留下不少招人攻击的把柄。
首先必须搞清楚,北大筹办的燕京学堂,到底是 “中国体验 ”,还是 “高端学术
”。对照燕京学堂的官网,英文称 “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 ”,与中文的强调 “高端学术研究
”,明显对不上号(参见高峰枫:《谁的 “燕京学堂”?》
)。二者之间,我并不厚此薄彼,只是认定功能不同,不宜混淆。而且,我相信英文的介绍是有所本的,因那正是清华走的路:“五十年内,将有逾一万名学生从这个占地二点四万平方米的书院中毕业,他们会与自己在书院的同学和清华大学其他学生建立起私人的朋友关系,在遇到问题时,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可以
‘直接打电话讨论
’。”(参见《清华获三亿美元捐建苏世民书院系研究生培养特区》)这明摆着不是培养专家学者,并不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长期的感情投资。只不过作为后来者,北大希望更上一层楼,话说得太大、太满,反而弄得不可收拾。无论校方如何辩解,这一年制的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化的硕士课程,是不可能成为
“高端学术
”的。一定要这么做,只有两种可能性,或学校降低水准,法外开恩;或学生拼了小命,最终也达不到预想目标。
第二,这到底是 “学者项目 ”还是
“硕士项目”?同样是面向全球顶尖大学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清华开设的是 “苏世民学者项目”,没说给不给学位;北大非要标新立异,说是
“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 ”,马上引来很多质疑。先不说 “中国学
”,就说这一年制的硕士课程,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因北大校内现有两种不同的硕士学位课程,一是学术型,学制三年;二是专业型,学制两年。一般认为三年的比两年的好,如今再来个一年速成的硕士,还说是
“高端学术
”,确实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再说,国外大学的一年制硕士,大都属于创收性质,不怎么被看好,我们为何会格外优待,且高看一眼呢?&
第三,这“中国学 ”到底是 “课程 ”还是 “学位
”?按照相关法规,北大可独立开设新的二级学科,但颁授 “中国学硕士
”,必须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二○一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独立出来,成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换句话说,我们国家颁授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只能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中的一个。前些年关于
“国学 ”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给不给颁授独立学位,曾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否决。北大这回的“先斩后奏
”,我不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能接受。
第四,在中国大学里设置 “中国学
”,这到底是扬长补短,还是东施效颦?清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已有的学科体系中运作;北大非要棋高一着,弄出个
“除了要文、史、哲贯通,还要中西学术贯通 ”的“中国学 ”。无论校方如何强调 “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问题的主体性
”,这用英语教授的 “中国学 ”,怎么看都是舶来品。中国都这么强大了,还有必要搁置现行学科体制,引进欧洲的 “汉学 ”或美国的
“中国学 ”吗?我很怀疑。打破凝固的学科边界,建立一个开放的教学科研体系,这与抄袭美国的 “中国学
”,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北大百年校庆开始,我就不断强调,放眼各国好大学,其外国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研究,与本国语言 /文学
/文化研究,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该以哈佛东亚系或牛津汉学系的立场及趣味,来评价北大中文系,反之亦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绝不是移植汉学系或东亚系的眼光能解决的。若这么做,不仅不能
“迅速地融入世界 ”,反而丧失了自家的学术立场与比较优势。
第五,既然主要目标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而是抢 “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那就不能要求人家预先学过汉语。基于这一特点,清华实行全英文授课,首期设置的公共政策、经济管理、国际关系这三个领域,全都属于社会科学。北大希望发挥自家人文学功底深厚的优势,于是设计了
“哲学与宗教 ”、“历史与考古 ”、“文学与文化 ”、“经济与管理 ”、“法律与社会 ”、“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
”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打出来的旗帜是兼及国际化与本土性。殊不知这么一来,用什么语言上课成了大问题。讲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只说英语,似乎不太对劲;可中英文兼修,学生受得了吗?让这些
“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临时抱佛脚,在一年时间里,又学汉语又赶专业,做得到吗?即便学生咬牙跺脚表决心,没日没夜地赶工,有这个必要吗?两相对照,你会发现,清华的计划基本可行,北大的设想则过于天马行空了。
第六,清华只是笼统地说请大师来讲课,不提待遇,也不说与清华原有教授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项目,授课者是否拿高薪,跟局外人没关系。北大可好,把底牌都翻出来了
—为这一百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北大准备从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公开招聘 “杰出学者 ”二十人,并邀请
“国际顶尖访问教授
”二十人,并允诺为这些教授提供高薪。七十名教授,一百位学生,如此师生比,很容易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加上后来有关人士不太恰当的解释,坐实了校方想用这
“校中校 ”来改造北大人文学科的猜忌。
总的感觉是,清华引进了 “苏世民书院
”,没动自家根基,却坐收渔利。北大含辛茹苦,自筹经费,创办燕京学堂,但因立场摇摆,思路不清,论说含糊,留下了一大堆争议,实在很可惜。
若要我提建议,那就将燕京学堂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大块,第一块是办一所面向国际的高端的寄宿制学院的原计划,但定位改为类似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
”。也因此,第一,只发毕业证书,不谈学位问题。这么一来,可化解很多矛盾,也避开了若干激流与暗礁。至于担心因此削减了竞争力与影响力,那是多虑了。因为,在欧美学界,硕士本就不是重要的学位。在北大拿了个一年制的硕士,对于日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可以说不值一提;而对于从政或经商者来说,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第二,既然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可采用全英文教学,但局限在社会科学三个领域,取消原先设计的
“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 ”、“文学与文化
”,改为开设若干人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理由是,若专修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完全不学中文,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第三,取消这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国学生,以免成为
“留美预备班 ”。第四,不要再纠缠什么中国特色的 “中国学 ”了,没这个必要,且容易贻笑大方。
第二块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学家
”,那就按北大的学制及标准,考核及格的方才颁授相关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既然拿中国学位,必须学中文,学校不得放水(没听说在哈佛用中文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给愿意到北大来留学的各国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奖学金,尤其关注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如非洲以及目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东欧国家),这比跟哈佛、牛津抢
“最聪明的学生
”要有意义得多。目前在北大就读的留学生数量不少,但多属于自费,某种意义上乃学校的创收项目。改变这个思路,招收留学生时,更多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或学术发展需要。我相信,北大这么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三块是努力促成 “高端学术
”的诞生。说实话,研究中国问题,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不该过多寄希望于美国的中国学或欧洲的汉学,中国大学应立大志向,励精图治,方能重铸辉煌。我多次谈及中国学者如何
“不卑不亢
”地走出去:“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参见《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如何与汉学家对话》,收入《读书的
“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与目前国内各大学之纷纷催逼教师留洋相反,北大完全可以做成吸纳国内精英从事专业研究的平台。考虑到北大已有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有所长的国内学者(含台港澳)来燕园从事一年的专题研究,既出成果,也培养人才,更是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何乐而不为?
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初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七月三十日改定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读书》2014-09)
“改革 ”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
当“改革 ”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 “改革
”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 “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 “改革
”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 “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
”。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
“国际一流 ”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
”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谁是 “弄潮儿 ”?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 “知识人
”,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 “企业家 ”,讲“中国好大亨
”。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 “弄潮儿
”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 “出身海归
”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 “不被理解的改革派 ”。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 “保守派 ”强烈反对,最后 “被上头牺牲掉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 “逻辑 ”和“效率
”的改革。
谁是 “保守派”?张鸣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
“温和自由派 ”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 “只剩躯壳
”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
”,“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 ”,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 ”也好,“海龟 ”代“土鳖
”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 ”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
”是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
“升官图 ”,“升官图
”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 “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
”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
”。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
”,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 recycle一下,就叫
“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
“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
“好洋喜功 ”。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
“好古喜功 ”。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 “国际化
”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
—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它是以人文精神而见称于世的。我知道的北大人,无论负笈海外、取经回国,还是坚守本土、埋头苦干,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效力,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一切靠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钱在账上,不能不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燕京”本无事
(《读书》2014-09)
听说北大搞燕京学堂,没啥感觉,各高校都心仪这类项目。后读北大教授高峰枫《谁的
“燕京学堂”?》,两个提问让人联想起一些题外话来。“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
”(引自高文),一个自清朝建校,便是国立京师大学堂,另一个是私立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大学,北大占用燕京校址,后者早被撤销,缘何为燕京招魂?另一个问题,北大有全国最强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中哲、中国史各科建制齐全,为何叠床架屋,大张旗鼓再搞
“中国学”?
“中国学”?谁都说不清。似乎接续西方汉学、日本中国学或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倒也未必非得明确皈依哪个门派,但肯定不在中国本土学术脉络上,不然北大三个人文系顺手接管了。&
“中国学 ”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方法不同,它把 “中国
”客体化,像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观察土著一样。我们自己的人文学,以继承或反思中国传统为主,这与英美国家的英语系、历史系对待本国文化的方式一样。既然燕京学堂对接海外
”,须移情到外人视角中,想象自己是费正清、竹内好、顾彬,以冷眼旁观中国。这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与自我异化的能耐,土生土长,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学者,架势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易。如今中国高校不差钱,风闻北大间或延聘西方汉学家来京,用英语给外国学生讲中国文化,可保证原汁原味,避免
“中国学 ”洋泾浜化。
虽说苦心孤诣,若让欧、美、日去研究他们的 “中国学
”,咱们不掺和,本可省去种种麻烦。萨义德说,亚洲研究之类的学科,不关乎对象国,只处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着眼点在西方内部。北大的创意是把东方学移植到东方本土,怕会
“见光死 ”。凡事怕倒过来想,假如哈佛大学乐意,北大派些英语系教授赴哈佛,在它的英语系外另设 “海外英语系
”,教师从中国请,学生是华人,上课用中文教英语文学,哈佛作何感想?国人怕也嘘声一片:坑人呀,谁还费那么大劲送孩子上哈佛?学术造假到美国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比附有何道理?人家强,我们弱,岂有对等之理?中文系怎比海外
“中国学”?一门心思想与人家列坐抗礼,根底是义和团的脾气,不识相,不理性,不服必然规律。亚历山大大帝驰骋欧亚,希腊就是普世文化。罗马帝国疆域辽阔,拉丁语便是欧洲学术通用语。新一波全球化(西化)浪潮已冲击百年,英美两个帝国前后相继,其势汹汹,远过历史上任何扩张性文明。中国的教会学校,是新型帝国文明的远东前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取缔它们,不过一时之逆流。如没有
”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中国没在东方阵营的荫蔽下,若非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搞不定小小的朝鲜半岛,无暇顾及教会产业,谅你不敢下此狠手。汉学家修中国史,当笔涉西方侨民遭逐、教会学校被废,每每欷歔不已。冷战一结束,全球沉浸在携手共赢的一个梦想中,不断有人呼吁给传教士正名,恢复教会学校名誉。重启
“燕京 ”之名,为人心所向也未可知。
当下评判对错的标准:不论事之功效,只问美国之有无。每与人家争辩,我精心罗列一堆论据,结果人家一语定音:这类事在美国如此这般。一言九鼎,在座无不服膺。按此逻辑,我试问:怎么就不能开设
“中国学 ”呢?美国不也有 American Studies吗?
深究 “美国学
”的学科史,便知两边的初衷不同。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愈发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好事者不满美国学院继承欧洲学术传统,于是挖掘美国精神内核,从本国的主体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成为头号强国,重新修史的冲动愈难遏制。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
”正式建制,发展出 “神话与象征 ”的系统方法论,弘扬美国文学巨匠如爱默生、梭罗、霍桑等,打造新的 “美国文明
反观燕京学堂 “中国学 ”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避免本土知识的
“不兼容性 ”。聘汉学家按 “国际规范 ”来华授课,带动中国学界走向 “世界
”—具体到哪儿,地点不详,但别当真以为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忽略不计,只几富国撑起 “国际
”或“世界”的语义。更重要的,外国学生来华深造,可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地位,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际学生。为吸引国际学生,只能学美国的
“中国学 ”,以英文授课,交英文论文。&
有人或许会说:西方人学中文确实难,中西分属两个不同文明体系,印欧语与汉语之间又没有亲缘关系,思维方式南辕北辙,学对方语言一定不容易。可反过来,对中国人也一样难呀!多少中国留学生涌到欧美,没见谁给中国学生开小灶,上中文课。更没听说哪位东亚系的留学生提交中文论文。
美国人用英语学中国文学,我们学英语文学却禁用中文,在家里搞不平等。中国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学生曾一度从本科到博士一律英文做论文,文献、索引也随之源自英语世界,原汁原味才正宗。于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国外,本土学术圈没有讨论平台,也无独立于英语世界的学术关切。所以,最高目标是追逐
“国际前沿”,结果东抄西凑,无所建树。研究生答辩时,教授们不厌其烦地挑剔论文的语法、拼写错误,博士论文权当英语大作文。有人戏称中国外语类研究生教育是:上完大四上大五,接着大六、大七、大八……多亏北大外语学院早觉悟,要求博士论文用中文。
这么一比,还得佩服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家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视域,在借鉴大陆、台湾的成果之上,仍未偏离独立的立场,以“亚洲研究协会
”(AAS)为交流平台的共同体内,中国研究学者相互切磋、促进,成果显著,虽然在美属边缘学科,如今却反过来影响大陆、台湾主流学界。我们的外语界并不边缘,原创性的成果乏善可陈。只知译介、照搬,求知动力何来?三十多年延宕在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不能自拔,为何总进入不了 “漫游时代”?
比来比去,无非还是 “美国有无 ”的标尺,支持 “燕京 ”也罢,反对也罢,逻辑一致
—向美国看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境:不凭自己想要什么,只眼盯着别人如何行事;别人的眼光规定着我们的行为,他人的看法,塑造我们的形象。自晚清落后挨打,一步步迷失天下图景的坐标,惶惶然向异邦寻图存之道。从此落魄失魂,耳目不能自主,只想给人留下
“印象 ”。&
奥运开幕式大搞 “印象中国
”,不查自己有什么文化,一心琢磨西方想象的中国情调。结果外宾大饱眼福,印证固有的偏见。我们也欣赏异域情趣的自我,还惊喜地 “发现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 ”,打造 “国际形象
”,一套套说辞包装自己,表演性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百姓日常伦理。家长拼孩子升学、留洋,有多少是为子女深造,多少是给自己
“挣脸”?国外疯狂购物,竟被吹成 “为国争光的爱国之旅 ”。北大排名本无可争议,非在国际排名榜上争 “世界一流大学 ”,结果被 “燕京
”闹得惶惶不可终日。
搞人文的,成果该让同仁分享,可校方非要求在国外发表,才算货真价实。结果,读者与作者万里相隔,没交集,更无对话。论文既不为探讨问题,难免东拼西凑,组装一件,形式大于内容,发表高于一切。笛卡儿说
“我思故我在 ”。我们说:你承认,我才在。
目睹几十年之怪现状,燕京学堂算什么?随大流而已,“燕京”本无事,众人借题发挥。说些雅人不愿闻、智者不屑讲的怪话何用?现实比牢骚更怵目惊心?以前听
“历史大潮滚滚向前,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的口号,只觉得虚张声势,这次全球化大潮到来,才知此言着实不虚。
国际化的歧路
(《读书》2014-09)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方案里,“国际化
”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它融手段与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纲要
—“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国学生,英文教学,住宿式学院,预算比照 “哈佛大学的标准
”……又是理想蓝图和完成后的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叫“愿景
“国际化 ”的流行,不过几年。早些年头,中国大学的通行说法叫“和国际接轨
”,虽然指称的概念上了档次,内容却一袭其旧。如果仔细咀嚼其中细微的心态差异,“和国际接轨 ”或还带有一丝被动、落后的意味,那么
“国际化 ”则因为站在纵览中外大学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而多了背水迎战的决心。简言之,“国际化 ”是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公理,是“赶超型大学
”唯一能够搭上的末班车。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它实践上的
ABC,也有它理论上的建构。当国际化的话语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它就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秩序、规范。中国的大学正是以此为镜,在凝视镜中那所理想大学的同时,也产生出对
“国际化 ”的匮乏,这大概就是燕京学堂宣称要将 “主体性 ”和“国际化 ”相结合的原因。
国际化果真如此不言自明吗?让我们打碎这面镜子,看看镜子后有什么。
诚然,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场名为 “国际化
”的疾风骤雨,从社区学校招收的大批留学生,到一批公立或私立大学相继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建立卫星校区,开设合作学位项目,变化尚未完成。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纽约大学,这所过去的地方性大学,如今却因为激进地拥抱
“国际化 ”而成为全球大学 “开放
”新尺度的标杆。国人大多了解纽约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却未必了解其在校长塞克斯顿(Sexton)治下高歌猛进的扩张史。目前纽约大学已经在阿布扎比和上海有两所分校,这还不算因财政或生源因素已经关闭的位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校区。而他曾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远程教育技术将分布在全球的卫星校区联结起来,使纽约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全天的二十四小时内与世界同步上课。世界公民,全球课堂,至此可谓尽善尽美。&
纽约大学的案例被写进了一本叫作《伟大的智力竞争:全球型大学如何改变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的书中。作者本 ·维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踏破铁鞋,奔波在纽约、德里、阿布扎比、上海和新加坡之间进行采访调查。他发现,学生、教师的流动正以越来越 “自由
”的形式实现,特别是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新加坡、海湾地区发展出的卫星校区模式,人才流动的节点从过去的欧美中心向此外的地区扩展,流动的路线也变得更加复杂。他将这种流动称为
“智力的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n
mind)。在他看来,一个平滑的全球教育市场正在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接受跨境学习提供空前的机遇。
然而,大学的国际化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自由贸易
”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出大学国际化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学生成为付费的买主,建立海外分校这样的行为就必须纳入到市场框架下予以思考。同时,民族
—国家自身角色的转型,以巨额投入打造属于自己的 “世界一流大学
”,也在推动后发国家主动地接纳美国式学术体制,其结果便是教育主权话语的衰落,以及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它宣称
“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也属于全人类 ”。国际化并没有填平中心与边缘间的鸿沟,而是在更为分散的诸多节点上不断地复制中心
/边缘关系。在全球型大学的时代,越来越多具有 “飞地
”性质的校区开始出现。二○一三年,总部位于北京的某地产集团透过其名下的基金会,斥资两千六百万美元在美国新泽西购地,并建立了一所
“普林斯顿数理国际中学 ”。该校的合作伙伴包括人大附中,其计划招生的一半为国际学生,这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如果说这是一次 “逆袭
”,而斯坦福的北大中心乃至此次的燕京学堂则更像一次怪诞的自我殖民,是大学改革者引以为傲的招商引资行为。不难理解,改革者所强调的 “开放
” 总是迎合那些使资本得到巨大 —显性或隐性,经济或政治
—回报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应该赋予他们更快的流动性、更低的门槛和更集中的特权。不仅如此,要保持资本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改革应该调动那些能够直接被
“品牌化 ”的象征 —如“燕京”或者静园
—却又必须掏空其内核。而要确保资本的密集投放,那么就只能惠及最精英的少数人。在向外部开放、拥抱大同的同时,却不断造就内部的隔离、分裂,这就是燕京学堂国际化的悖论。
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导教育改革的强势思维,大学的国际化或许尚未培养出 “世界公民
”,便已沦为自身的一场噩梦。大学的管理方式正在不断向经济学靠拢:作为涉及人文学科的改革项目,燕京学堂的主事者主要来自北大的经济和管理学院,并非偶然。大学正在被“去地方化
”:无论是向外扩张的海外分校还是重构内部的国际化项目,都对传统大学的想象构成挑战。应该如何看待一所大学的空间、历史、人文传统同这些飞地之间的联系?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否被化约成跨国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完成原料购买和组装?大学改革同时也在沦为一项炫耀性的媒体
“景观 ”:燕京学堂的项目方案细节千呼万唤不出来,据说这符合 “务实低调的做事风格
”,但其设计效果图、网站和宣传片倒是先声夺人,美丽的 “愿景”掩盖了本该严肃进行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问,驱动 “国际化
”改革的动力,是否本身就来自大学对内部危机的转嫁?在美国诸多大学全面国际化的背后,掩饰不住难言的尴尬。面对政府拨款急剧削减的现实,吸收海外生源或建立海外分校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公立大学为了招收中国学生,雇佣教育中介并偿付回扣,已并非秘密。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大学内部的民主传统正受到严重威胁,学费猛涨、学生贷款压身已经成为令政府头疼不已的社会问题。就在纽约大学大举海外扩张的同时,纽约大学约半数的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贷款,人均负债水平近乎哈佛大学的两倍。而正是这位被视作革新者的塞克斯顿校长,在教师看来更像一位铁腕专断的独裁者和标新立异的
CEO。他仅倚重少数几位教授,却对大多数教师的意见置若罔闻,甚至在重大决策上先斩后奏,使美国大学的民主传统徒成具文。二○一二年底,纽约大学最大的文理学院为此发起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以表达对他的抗议。
改革本是为了兴利除弊,却引发更为深广的危机,同样的脚本在燕京学堂争议中再次上演。以“国际化
”为改革旗号,以更多的高校自主权为吁求,要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实则是既否认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基层师生的主体地位,又视校内民主程序和师生应有的民主监督为无物。其结果大概可以预见,就是让极少数的教授享受
“哈佛预算 ”水准的薪资,让极少数的 “未来领袖
”占用本已十分稀缺的教育资源,而不去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机制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让大学的整体改革依旧步履蹒跚。
X光片,燕京学堂的宣传片透视出中国大学改革的普遍病理:短片中罗列了蔡元培、胡适等北大诸多杰出校友的名字,却如幽灵一般浮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礼堂、草坪上,这样一座光洁亮丽然而无人的校园,正是奉献给国际学术精英的
“特区 ”。纵观燕京学堂争议,作为大学的真正主体,师生们的退场
/隐形是这场改革患上精神分裂的最大症候。不去触及大学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妄想通过国际化来确立一种新秩序,不过是又一种剜肉补疮的天真。
中国大学积弊深重,这是大家的共识,批评燕京学堂并不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回复老路。在静园改建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这次争议足以成为一个伤口,警醒我们去思考,大学的国际化向谁开放,由谁主导,对谁负责?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教育与探索》系中国教育工作者协会会刊,创刊于2006年10月,由中国教育工作者协会和岁月杂志社联合举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23-1142/I,国际标准刊号:ISSN,邮发代号:14-171。
本刊已被龙源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网络媒体全文收录。在本刊发表的论文符合中、高级职称的评审,可以作为参加评职评优的参考依据。
征稿对象:
全国教科研工作者、广大教师、各级科技与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科研院所、科技教育人员、科教领域管理人员、各大院校的在读博士生、研究生及社会各界关心科教工作的人士。
栏目设置:
本刊主要栏目有:教育管理、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学科教育、高等教育、创新探索、科教信息、会员作品、学校风采等。
投稿须知:
<font COLOR="#、来稿请尽可能发电子邮件,文字稿须以Word文档形式作为附件发送,文中如有图片,应以JPG格式作为附件发送,不得粘贴在Word文档中,并应确保图片清晰。
<font COLOR="#、作者文责自负。杜绝一切不严肃的引用和抄袭,对于剽窃他人成果者,本刊将予公开曝光。
<font COLOR="#、在不改变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本刊保留对稿件的删节、修改权,以及对已在本刊刊发文章的电子版权和结集出版权。如不同意请在来稿时特别注明。
投稿信箱:&
&咨询电话: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国内 有哪些期刊杂志社?_百度知道
中国国内 有哪些期刊杂志社?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青少年书法报 书法报 书法导报 杂志;J
这都是和书法相关的,比如书法——机构刊号:期刊——媒体名称;J 中国书法11-1136/J 青少年书法41-1054/,就太多了报纸;C 书法31-1067/,如果找和文化相关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机构查询——期刊/期刊社查询——所属类型;J 书法丛刊11-2827/J 书法赏评23-1313/J 中国钢笔书法33-1036/,你自己到出版总署网站查询吧:填上你要找的关键字:解放军美术书法11-5949/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其他1条回答
环球观察,青年文摘最广泛吧
凤姐爱看的故事会,知音
还有人物读者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回答者: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燕京学堂笔谈(《读书》杂志201409)
假如我办燕京学堂
(《读书》2014-09)
”,就是不可能的意思。既然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何还要如此自作多情?因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相对来说,批评畅快淋漓,建设则困难得多。那就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是北大校长,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很有挑战性的
“燕京学堂 ”计划,应该怎么做?不提 “战果辉煌 ”,就说 “实现既定目标
”吧—为何如此低调?因北大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在享受恩宠的同时,被全国人民拿着放大镜观察、挑剔、评论,稍为偏离既定的航道,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批评。这种状态下,只能小心翼翼,平安驾驶,很难期待惊天动地的制度性创新。
可是,我们又都希望北大能奋起直追,迅速地 “世界一流
”。不动制度,通过增加经费,是能提升若干水平的。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制度非动不可,这个时候,牵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及习惯思维。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谋定而后动
”。可以不断地打雷,好一阵子下不来雨;但不能没做任何预报,就来场正义的滂沱大雨。雨是迟早要下的,但怎么下、下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量、有无节奏感等,都必须认真考量。不仅要驰想
“春雨贵如油 ”的妙境,还得防止决堤溃坝的灾难;“有百利而无一弊
”的改革,那是神仙才能碰到的。很可惜,北大这回创办燕京学堂,明显低估了其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难度,未曾做过认真的 “沙盘推演
”—我说的 “沙盘推演
”,是指主事者自我设置对立面,站在另一个角度立论,来回辩驳,直到基本上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
筹巨资创建一个新的教学机构,对于北大是件大事,事先其实征求过不少中层领导及名教授的意见,不可能是校长脑袋一拍就出来的。问题在于征求谁的意见,以及如何征求,程序正确不等于效果就一定好。做过行政的人都明白,讨论同一件事,找谁不找谁,谈论宗旨还是敲定细节,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说,中层领导怕校长,普通教授则不怕,更有可能直言不讳;而同样是名教授,有人习惯于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则热心公共事务,就看你能否及时发现潜在的 “反对派
”。若真想征求意见,应该多找有勇气、有见解、有担当且历来特立独行、敢于自我立论的普通教授,既给他们解释,也听他们抱怨,甚至允诺一切可以商量,大不了推倒重来。若怕人多嘴杂,想快刀斩乱麻,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来努力解释,希望广大师生
“顾全大局 ”,这在别的学校做得到,在北大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一所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学。
平心而论,从社会募集巨额经费,创办培养国际人才的燕京学堂,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好事。可如今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对北大声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何当初匆忙上马,高调宣布,而不可以稍微等一等,多邀请敢于直言的反对者参与协商,或吸纳意见,化解对立;或调整节奏,优化计划?那样做肯定效果更好。问题在于,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初被征求意见的诸君,大都并没意识到事情竟然这么复杂。
这就说到北大人的特点,无论校方还是教授,多志存高远,擅长侃侃而谈,看不起斤斤计较,尤其不太注意细节。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
“细节决定成败 ”—谁能想到一张 “流光溢彩
”的静园修缮效果图,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我相信北大校方之创办燕京学堂,确实是用心良苦;问题可能出在悬的太高,用力太猛,操之太急,加上论述时的若干瑕疵,以致引起部分师生及校友的猛烈批评。不想
“高屋建瓴
”地说风凉话,我希望站在建设者的立场,帮着出出主意,看能否进一步完善此计划。相关意见适时提交给了校方,至于是否被采纳,不在我考虑范围内。选择九月方才刊行的《读书》杂志发言,是假定那时大局已定,风波也基本上过去了,发文章只是为了
“立此存照 ”。
都是模仿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着眼于培养国际化的
“各界领导精英 ”;也都是一年制的学习计划,为何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波澜不惊,北大的燕京学堂却风急浪高?除了两校师生处世及表达风格的不同,更因清华计划可操作性强,北大则过于理想化,不太可行。后者选择了学校中心且带有标志性的静园六院来建寄宿制书院,乃极大的败笔,此举引发了学生及校友的公愤,学校不得不做出妥协。如此
“败走麦城 ”,不全然是思虑不周,还是我所说的用力过猛,即太想把事情办好,以至于不考虑前后左右、上下里外。
在我看来,这燕京学堂即便圆满达成目标,也只是为北大增加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成为整个大学的中心。顺便说一句,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一个以英语讲授、以国际学生为对象、“肩负提供世界级中国研究教学重任的中国研究中心
”,但在整个大学处于很不起眼的位置。
我想辨析的是,为何北大这升级版的国际化计划不太可行,以及到底该如何修正。具体论述时,不断以清华计划为参照系。说北大创办燕京学堂是为了与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竞争,这本身没什么不对;两校之间你追我赶,是个好现象,只是不要因急功近利而脚步变形。记得当年北大刚创办文史哲实验班时,清华提出的追赶方案是文史哲再加中外文,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我提醒清华校方注意:学生只有一个脑袋,且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这回清华走在前,北大为了赶超竞争对手,把好几个功能不同的计划糅合在一起,表面上是
“高大上 ”了,实则模糊了战略目标,留下不少招人攻击的把柄。
首先必须搞清楚,北大筹办的燕京学堂,到底是 “中国体验 ”,还是 “高端学术
”。对照燕京学堂的官网,英文称 “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 ”,与中文的强调 “高端学术研究
”,明显对不上号(参见高峰枫:《谁的 “燕京学堂”?》
)。二者之间,我并不厚此薄彼,只是认定功能不同,不宜混淆。而且,我相信英文的介绍是有所本的,因那正是清华走的路:“五十年内,将有逾一万名学生从这个占地二点四万平方米的书院中毕业,他们会与自己在书院的同学和清华大学其他学生建立起私人的朋友关系,在遇到问题时,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可以
‘直接打电话讨论
’。”(参见《清华获三亿美元捐建苏世民书院系研究生培养特区》)这明摆着不是培养专家学者,并不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长期的感情投资。只不过作为后来者,北大希望更上一层楼,话说得太大、太满,反而弄得不可收拾。无论校方如何辩解,这一年制的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化的硕士课程,是不可能成为
“高端学术
”的。一定要这么做,只有两种可能性,或学校降低水准,法外开恩;或学生拼了小命,最终也达不到预想目标。
第二,这到底是 “学者项目 ”还是
“硕士项目”?同样是面向全球顶尖大学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清华开设的是 “苏世民学者项目”,没说给不给学位;北大非要标新立异,说是
“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 ”,马上引来很多质疑。先不说 “中国学
”,就说这一年制的硕士课程,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因北大校内现有两种不同的硕士学位课程,一是学术型,学制三年;二是专业型,学制两年。一般认为三年的比两年的好,如今再来个一年速成的硕士,还说是
“高端学术
”,确实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再说,国外大学的一年制硕士,大都属于创收性质,不怎么被看好,我们为何会格外优待,且高看一眼呢?&
第三,这“中国学 ”到底是 “课程 ”还是 “学位
”?按照相关法规,北大可独立开设新的二级学科,但颁授 “中国学硕士
”,必须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二○一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独立出来,成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换句话说,我们国家颁授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只能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中的一个。前些年关于
“国学 ”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给不给颁授独立学位,曾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否决。北大这回的“先斩后奏
”,我不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能接受。
第四,在中国大学里设置 “中国学
”,这到底是扬长补短,还是东施效颦?清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已有的学科体系中运作;北大非要棋高一着,弄出个
“除了要文、史、哲贯通,还要中西学术贯通 ”的“中国学 ”。无论校方如何强调 “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问题的主体性
”,这用英语教授的 “中国学 ”,怎么看都是舶来品。中国都这么强大了,还有必要搁置现行学科体制,引进欧洲的 “汉学 ”或美国的
“中国学 ”吗?我很怀疑。打破凝固的学科边界,建立一个开放的教学科研体系,这与抄袭美国的 “中国学
”,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北大百年校庆开始,我就不断强调,放眼各国好大学,其外国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研究,与本国语言 /文学
/文化研究,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该以哈佛东亚系或牛津汉学系的立场及趣味,来评价北大中文系,反之亦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绝不是移植汉学系或东亚系的眼光能解决的。若这么做,不仅不能
“迅速地融入世界 ”,反而丧失了自家的学术立场与比较优势。
第五,既然主要目标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而是抢 “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那就不能要求人家预先学过汉语。基于这一特点,清华实行全英文授课,首期设置的公共政策、经济管理、国际关系这三个领域,全都属于社会科学。北大希望发挥自家人文学功底深厚的优势,于是设计了
“哲学与宗教 ”、“历史与考古 ”、“文学与文化 ”、“经济与管理 ”、“法律与社会 ”、“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
”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打出来的旗帜是兼及国际化与本土性。殊不知这么一来,用什么语言上课成了大问题。讲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只说英语,似乎不太对劲;可中英文兼修,学生受得了吗?让这些
“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临时抱佛脚,在一年时间里,又学汉语又赶专业,做得到吗?即便学生咬牙跺脚表决心,没日没夜地赶工,有这个必要吗?两相对照,你会发现,清华的计划基本可行,北大的设想则过于天马行空了。
第六,清华只是笼统地说请大师来讲课,不提待遇,也不说与清华原有教授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项目,授课者是否拿高薪,跟局外人没关系。北大可好,把底牌都翻出来了
—为这一百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北大准备从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公开招聘 “杰出学者 ”二十人,并邀请
“国际顶尖访问教授
”二十人,并允诺为这些教授提供高薪。七十名教授,一百位学生,如此师生比,很容易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加上后来有关人士不太恰当的解释,坐实了校方想用这
“校中校 ”来改造北大人文学科的猜忌。
总的感觉是,清华引进了 “苏世民书院
”,没动自家根基,却坐收渔利。北大含辛茹苦,自筹经费,创办燕京学堂,但因立场摇摆,思路不清,论说含糊,留下了一大堆争议,实在很可惜。
若要我提建议,那就将燕京学堂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大块,第一块是办一所面向国际的高端的寄宿制学院的原计划,但定位改为类似清华的
“苏世民书院 ”,“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
”。也因此,第一,只发毕业证书,不谈学位问题。这么一来,可化解很多矛盾,也避开了若干激流与暗礁。至于担心因此削减了竞争力与影响力,那是多虑了。因为,在欧美学界,硕士本就不是重要的学位。在北大拿了个一年制的硕士,对于日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可以说不值一提;而对于从政或经商者来说,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第二,既然不是培养汉学家或中国学家,可采用全英文教学,但局限在社会科学三个领域,取消原先设计的
“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 ”、“文学与文化
”,改为开设若干人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理由是,若专修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完全不学中文,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第三,取消这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国学生,以免成为
“留美预备班 ”。第四,不要再纠缠什么中国特色的 “中国学 ”了,没这个必要,且容易贻笑大方。
第二块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学家
”,那就按北大的学制及标准,考核及格的方才颁授相关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既然拿中国学位,必须学中文,学校不得放水(没听说在哈佛用中文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给愿意到北大来留学的各国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奖学金,尤其关注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如非洲以及目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东欧国家),这比跟哈佛、牛津抢
“最聪明的学生
”要有意义得多。目前在北大就读的留学生数量不少,但多属于自费,某种意义上乃学校的创收项目。改变这个思路,招收留学生时,更多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或学术发展需要。我相信,北大这么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三块是努力促成 “高端学术
”的诞生。说实话,研究中国问题,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不该过多寄希望于美国的中国学或欧洲的汉学,中国大学应立大志向,励精图治,方能重铸辉煌。我多次谈及中国学者如何
“不卑不亢
”地走出去:“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参见《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如何与汉学家对话》,收入《读书的
“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与目前国内各大学之纷纷催逼教师留洋相反,北大完全可以做成吸纳国内精英从事专业研究的平台。考虑到北大已有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有所长的国内学者(含台港澳)来燕园从事一年的专题研究,既出成果,也培养人才,更是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何乐而不为?
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初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七月三十日改定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读书》2014-09)
“改革 ”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
当“改革 ”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 “改革
”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 “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 “改革
”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 “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
”。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
“国际一流 ”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
”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谁是 “弄潮儿 ”?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 “知识人
”,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 “企业家 ”,讲“中国好大亨
”。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 “弄潮儿
”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 “出身海归
”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 “不被理解的改革派 ”。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 “保守派 ”强烈反对,最后 “被上头牺牲掉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 “逻辑 ”和“效率
”的改革。
谁是 “保守派”?张鸣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
“温和自由派 ”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 “只剩躯壳
”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
”,“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 ”,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 ”也好,“海龟 ”代“土鳖
”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 ”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
”是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
“升官图 ”,“升官图
”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 “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
”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
”。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
”,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 recycle一下,就叫
“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
“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
“好洋喜功 ”。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
“好古喜功 ”。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 “国际化
”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
—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它是以人文精神而见称于世的。我知道的北大人,无论负笈海外、取经回国,还是坚守本土、埋头苦干,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效力,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一切靠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钱在账上,不能不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燕京”本无事
(《读书》2014-09)
听说北大搞燕京学堂,没啥感觉,各高校都心仪这类项目。后读北大教授高峰枫《谁的
“燕京学堂”?》,两个提问让人联想起一些题外话来。“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
”(引自高文),一个自清朝建校,便是国立京师大学堂,另一个是私立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大学,北大占用燕京校址,后者早被撤销,缘何为燕京招魂?另一个问题,北大有全国最强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中哲、中国史各科建制齐全,为何叠床架屋,大张旗鼓再搞
“中国学”?
“中国学”?谁都说不清。似乎接续西方汉学、日本中国学或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倒也未必非得明确皈依哪个门派,但肯定不在中国本土学术脉络上,不然北大三个人文系顺手接管了。&
“中国学 ”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方法不同,它把 “中国
”客体化,像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观察土著一样。我们自己的人文学,以继承或反思中国传统为主,这与英美国家的英语系、历史系对待本国文化的方式一样。既然燕京学堂对接海外
”,须移情到外人视角中,想象自己是费正清、竹内好、顾彬,以冷眼旁观中国。这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与自我异化的能耐,土生土长,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学者,架势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易。如今中国高校不差钱,风闻北大间或延聘西方汉学家来京,用英语给外国学生讲中国文化,可保证原汁原味,避免
“中国学 ”洋泾浜化。
虽说苦心孤诣,若让欧、美、日去研究他们的 “中国学
”,咱们不掺和,本可省去种种麻烦。萨义德说,亚洲研究之类的学科,不关乎对象国,只处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着眼点在西方内部。北大的创意是把东方学移植到东方本土,怕会
“见光死 ”。凡事怕倒过来想,假如哈佛大学乐意,北大派些英语系教授赴哈佛,在它的英语系外另设 “海外英语系
”,教师从中国请,学生是华人,上课用中文教英语文学,哈佛作何感想?国人怕也嘘声一片:坑人呀,谁还费那么大劲送孩子上哈佛?学术造假到美国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比附有何道理?人家强,我们弱,岂有对等之理?中文系怎比海外
“中国学”?一门心思想与人家列坐抗礼,根底是义和团的脾气,不识相,不理性,不服必然规律。亚历山大大帝驰骋欧亚,希腊就是普世文化。罗马帝国疆域辽阔,拉丁语便是欧洲学术通用语。新一波全球化(西化)浪潮已冲击百年,英美两个帝国前后相继,其势汹汹,远过历史上任何扩张性文明。中国的教会学校,是新型帝国文明的远东前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取缔它们,不过一时之逆流。如没有
”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中国没在东方阵营的荫蔽下,若非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搞不定小小的朝鲜半岛,无暇顾及教会产业,谅你不敢下此狠手。汉学家修中国史,当笔涉西方侨民遭逐、教会学校被废,每每欷歔不已。冷战一结束,全球沉浸在携手共赢的一个梦想中,不断有人呼吁给传教士正名,恢复教会学校名誉。重启
“燕京 ”之名,为人心所向也未可知。
当下评判对错的标准:不论事之功效,只问美国之有无。每与人家争辩,我精心罗列一堆论据,结果人家一语定音:这类事在美国如此这般。一言九鼎,在座无不服膺。按此逻辑,我试问:怎么就不能开设
“中国学 ”呢?美国不也有 American Studies吗?
深究 “美国学
”的学科史,便知两边的初衷不同。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愈发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好事者不满美国学院继承欧洲学术传统,于是挖掘美国精神内核,从本国的主体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成为头号强国,重新修史的冲动愈难遏制。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
”正式建制,发展出 “神话与象征 ”的系统方法论,弘扬美国文学巨匠如爱默生、梭罗、霍桑等,打造新的 “美国文明
反观燕京学堂 “中国学 ”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避免本土知识的
“不兼容性 ”。聘汉学家按 “国际规范 ”来华授课,带动中国学界走向 “世界
”—具体到哪儿,地点不详,但别当真以为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忽略不计,只几富国撑起 “国际
”或“世界”的语义。更重要的,外国学生来华深造,可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地位,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际学生。为吸引国际学生,只能学美国的
“中国学 ”,以英文授课,交英文论文。&
有人或许会说:西方人学中文确实难,中西分属两个不同文明体系,印欧语与汉语之间又没有亲缘关系,思维方式南辕北辙,学对方语言一定不容易。可反过来,对中国人也一样难呀!多少中国留学生涌到欧美,没见谁给中国学生开小灶,上中文课。更没听说哪位东亚系的留学生提交中文论文。
美国人用英语学中国文学,我们学英语文学却禁用中文,在家里搞不平等。中国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学生曾一度从本科到博士一律英文做论文,文献、索引也随之源自英语世界,原汁原味才正宗。于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国外,本土学术圈没有讨论平台,也无独立于英语世界的学术关切。所以,最高目标是追逐
“国际前沿”,结果东抄西凑,无所建树。研究生答辩时,教授们不厌其烦地挑剔论文的语法、拼写错误,博士论文权当英语大作文。有人戏称中国外语类研究生教育是:上完大四上大五,接着大六、大七、大八……多亏北大外语学院早觉悟,要求博士论文用中文。
这么一比,还得佩服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家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视域,在借鉴大陆、台湾的成果之上,仍未偏离独立的立场,以“亚洲研究协会
”(AAS)为交流平台的共同体内,中国研究学者相互切磋、促进,成果显著,虽然在美属边缘学科,如今却反过来影响大陆、台湾主流学界。我们的外语界并不边缘,原创性的成果乏善可陈。只知译介、照搬,求知动力何来?三十多年延宕在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不能自拔,为何总进入不了 “漫游时代”?
比来比去,无非还是 “美国有无 ”的标尺,支持 “燕京 ”也罢,反对也罢,逻辑一致
—向美国看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境:不凭自己想要什么,只眼盯着别人如何行事;别人的眼光规定着我们的行为,他人的看法,塑造我们的形象。自晚清落后挨打,一步步迷失天下图景的坐标,惶惶然向异邦寻图存之道。从此落魄失魂,耳目不能自主,只想给人留下
“印象 ”。&
奥运开幕式大搞 “印象中国
”,不查自己有什么文化,一心琢磨西方想象的中国情调。结果外宾大饱眼福,印证固有的偏见。我们也欣赏异域情趣的自我,还惊喜地 “发现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 ”,打造 “国际形象
”,一套套说辞包装自己,表演性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百姓日常伦理。家长拼孩子升学、留洋,有多少是为子女深造,多少是给自己
“挣脸”?国外疯狂购物,竟被吹成 “为国争光的爱国之旅 ”。北大排名本无可争议,非在国际排名榜上争 “世界一流大学 ”,结果被 “燕京
”闹得惶惶不可终日。
搞人文的,成果该让同仁分享,可校方非要求在国外发表,才算货真价实。结果,读者与作者万里相隔,没交集,更无对话。论文既不为探讨问题,难免东拼西凑,组装一件,形式大于内容,发表高于一切。笛卡儿说
“我思故我在 ”。我们说:你承认,我才在。
目睹几十年之怪现状,燕京学堂算什么?随大流而已,“燕京”本无事,众人借题发挥。说些雅人不愿闻、智者不屑讲的怪话何用?现实比牢骚更怵目惊心?以前听
“历史大潮滚滚向前,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的口号,只觉得虚张声势,这次全球化大潮到来,才知此言着实不虚。
国际化的歧路
(《读书》2014-09)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方案里,“国际化
”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它融手段与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纲要
—“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国学生,英文教学,住宿式学院,预算比照 “哈佛大学的标准
”……又是理想蓝图和完成后的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叫“愿景
“国际化 ”的流行,不过几年。早些年头,中国大学的通行说法叫“和国际接轨
”,虽然指称的概念上了档次,内容却一袭其旧。如果仔细咀嚼其中细微的心态差异,“和国际接轨 ”或还带有一丝被动、落后的意味,那么
“国际化 ”则因为站在纵览中外大学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而多了背水迎战的决心。简言之,“国际化 ”是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公理,是“赶超型大学
”唯一能够搭上的末班车。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它实践上的
ABC,也有它理论上的建构。当国际化的话语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它就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秩序、规范。中国的大学正是以此为镜,在凝视镜中那所理想大学的同时,也产生出对
“国际化 ”的匮乏,这大概就是燕京学堂宣称要将 “主体性 ”和“国际化 ”相结合的原因。
国际化果真如此不言自明吗?让我们打碎这面镜子,看看镜子后有什么。
诚然,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场名为 “国际化
”的疾风骤雨,从社区学校招收的大批留学生,到一批公立或私立大学相继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建立卫星校区,开设合作学位项目,变化尚未完成。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纽约大学,这所过去的地方性大学,如今却因为激进地拥抱
“国际化 ”而成为全球大学 “开放
”新尺度的标杆。国人大多了解纽约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却未必了解其在校长塞克斯顿(Sexton)治下高歌猛进的扩张史。目前纽约大学已经在阿布扎比和上海有两所分校,这还不算因财政或生源因素已经关闭的位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校区。而他曾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远程教育技术将分布在全球的卫星校区联结起来,使纽约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全天的二十四小时内与世界同步上课。世界公民,全球课堂,至此可谓尽善尽美。&
纽约大学的案例被写进了一本叫作《伟大的智力竞争:全球型大学如何改变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的书中。作者本 ·维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踏破铁鞋,奔波在纽约、德里、阿布扎比、上海和新加坡之间进行采访调查。他发现,学生、教师的流动正以越来越 “自由
”的形式实现,特别是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新加坡、海湾地区发展出的卫星校区模式,人才流动的节点从过去的欧美中心向此外的地区扩展,流动的路线也变得更加复杂。他将这种流动称为
“智力的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n
mind)。在他看来,一个平滑的全球教育市场正在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接受跨境学习提供空前的机遇。
然而,大学的国际化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自由贸易
”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出大学国际化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学生成为付费的买主,建立海外分校这样的行为就必须纳入到市场框架下予以思考。同时,民族
—国家自身角色的转型,以巨额投入打造属于自己的 “世界一流大学
”,也在推动后发国家主动地接纳美国式学术体制,其结果便是教育主权话语的衰落,以及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它宣称
“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也属于全人类 ”。国际化并没有填平中心与边缘间的鸿沟,而是在更为分散的诸多节点上不断地复制中心
/边缘关系。在全球型大学的时代,越来越多具有 “飞地
”性质的校区开始出现。二○一三年,总部位于北京的某地产集团透过其名下的基金会,斥资两千六百万美元在美国新泽西购地,并建立了一所
“普林斯顿数理国际中学 ”。该校的合作伙伴包括人大附中,其计划招生的一半为国际学生,这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如果说这是一次 “逆袭
”,而斯坦福的北大中心乃至此次的燕京学堂则更像一次怪诞的自我殖民,是大学改革者引以为傲的招商引资行为。不难理解,改革者所强调的 “开放
” 总是迎合那些使资本得到巨大 —显性或隐性,经济或政治
—回报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应该赋予他们更快的流动性、更低的门槛和更集中的特权。不仅如此,要保持资本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改革应该调动那些能够直接被
“品牌化 ”的象征 —如“燕京”或者静园
—却又必须掏空其内核。而要确保资本的密集投放,那么就只能惠及最精英的少数人。在向外部开放、拥抱大同的同时,却不断造就内部的隔离、分裂,这就是燕京学堂国际化的悖论。
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导教育改革的强势思维,大学的国际化或许尚未培养出 “世界公民
”,便已沦为自身的一场噩梦。大学的管理方式正在不断向经济学靠拢:作为涉及人文学科的改革项目,燕京学堂的主事者主要来自北大的经济和管理学院,并非偶然。大学正在被“去地方化
”:无论是向外扩张的海外分校还是重构内部的国际化项目,都对传统大学的想象构成挑战。应该如何看待一所大学的空间、历史、人文传统同这些飞地之间的联系?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否被化约成跨国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完成原料购买和组装?大学改革同时也在沦为一项炫耀性的媒体
“景观 ”:燕京学堂的项目方案细节千呼万唤不出来,据说这符合 “务实低调的做事风格
”,但其设计效果图、网站和宣传片倒是先声夺人,美丽的 “愿景”掩盖了本该严肃进行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问,驱动 “国际化
”改革的动力,是否本身就来自大学对内部危机的转嫁?在美国诸多大学全面国际化的背后,掩饰不住难言的尴尬。面对政府拨款急剧削减的现实,吸收海外生源或建立海外分校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公立大学为了招收中国学生,雇佣教育中介并偿付回扣,已并非秘密。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大学内部的民主传统正受到严重威胁,学费猛涨、学生贷款压身已经成为令政府头疼不已的社会问题。就在纽约大学大举海外扩张的同时,纽约大学约半数的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贷款,人均负债水平近乎哈佛大学的两倍。而正是这位被视作革新者的塞克斯顿校长,在教师看来更像一位铁腕专断的独裁者和标新立异的
CEO。他仅倚重少数几位教授,却对大多数教师的意见置若罔闻,甚至在重大决策上先斩后奏,使美国大学的民主传统徒成具文。二○一二年底,纽约大学最大的文理学院为此发起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以表达对他的抗议。
改革本是为了兴利除弊,却引发更为深广的危机,同样的脚本在燕京学堂争议中再次上演。以“国际化
”为改革旗号,以更多的高校自主权为吁求,要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实则是既否认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基层师生的主体地位,又视校内民主程序和师生应有的民主监督为无物。其结果大概可以预见,就是让极少数的教授享受
“哈佛预算 ”水准的薪资,让极少数的 “未来领袖
”占用本已十分稀缺的教育资源,而不去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机制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让大学的整体改革依旧步履蹒跚。
X光片,燕京学堂的宣传片透视出中国大学改革的普遍病理:短片中罗列了蔡元培、胡适等北大诸多杰出校友的名字,却如幽灵一般浮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礼堂、草坪上,这样一座光洁亮丽然而无人的校园,正是奉献给国际学术精英的
“特区 ”。纵观燕京学堂争议,作为大学的真正主体,师生们的退场
/隐形是这场改革患上精神分裂的最大症候。不去触及大学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妄想通过国际化来确立一种新秩序,不过是又一种剜肉补疮的天真。
中国大学积弊深重,这是大家的共识,批评燕京学堂并不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回复老路。在静园改建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这次争议足以成为一个伤口,警醒我们去思考,大学的国际化向谁开放,由谁主导,对谁负责?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九鼎记小说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求《相见欢阿yueyue歌词》这首歌以及歌词,邮箱zrw14kzl@163.com,谢谢
- ·乔太守的风水书画作品吕守约的画值多少钱钱能买到?
- ·求一本小说,找到必有重谢与定有酬谢
- ·求告知,2024小武当山风景区景区内播放的是什么音乐?
- ·找自己写了一篇小说想找出版社发表?
- ·pppd209 种子微信能发视频吗一份吗
- ·新金瓶完整电影那里看
- ·华为畅玩版评测视频qq视频有杂音,怎么回事
- ·求CB-96実录母子爱6 种子搜索 2737894896
- ·bet/365有高清风景图图么?
- ·谁有李zongyibus rui 的下载地址 麻烦发我koukou 591541983
- ·铁乡牌水磨机双月殿哪有铁卖
- ·写一篇作为一名电气理员如何管理员工的英语演讲稿稿,我想知道电气管理员在管理员工时与普通管理员的区别在哪里
- ·求91视频最新地址是多少呀。谢谢了帮大哥2014全部视频。
- ·生活是多么广阔斑羚飞渡课后题题{所有}怎么办呢?
- ·我的理想六年级作文的话题作文
- ·送上梦幻西游新手序列号2老玩家回归序列号10个!不可以用继续找我!!!
- ·请问有华夏土地b站邀请码码吗?本人采矿的,想下载一些资源学习,多谢了
- ·求这个图片的种子女人姓名
- ·你知道九鼎记漫画期刊杂志社吗》?
- ·在ISE平台上的fpga仿真软件文件该怎么写,有人有资料吗
- ·十二月哭灵 刘晓燕哭灵全集 音乐 下载地址
- ·网络红人魔女甜甜视频
- ·charls系列泳衣 炫彩宝石连体泳衣美女
- ·练瑜伽好听的歌曲有哪些和书有哪些
- ·2f跟3f对比红米手机怎么样样,那个好,还有力量,起油各方面的
- ·求耐克跑鞋气垫 跑鞋 和运动鞋各个系列的名字
- ·作为一名足坛90后新星大红大紫的新星
- ·新都那里有虹口游泳池开放时间。现在开放了吗?
- ·新邵县凯德广场沙湾 开业游泳池什么时候开业。
- ·如何在舞台魔术上让魔术与武术融合,从而达到效果
- ·湖北省崇阳县地图哪里有卖溜冰鞋
- ·储水塔涡轮增压器寿命,求推荐
- ·我想问一下你们奔波尔霸美多少钱的?
- ·一天中那哪个时间段健身最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