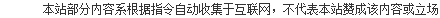周锐来我校,什么口号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05-15 12:19
时间:2015-05-15 12:19
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切开一段时间来回望诗歌与艺术的历史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上世纪的1969年夏天,我在北京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个诗人被认为是文革期间就开始写现代诗的第一人,这首诗读来觉得很另类也很新奇,在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的文本,它与毛泽东的诗歌完全不一样。给我看的人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成进行反革命言论的传播。我们这些留在北京的机关干部们的孩子们整天混在大街小巷,尤其是打群架的消息传到五七干校后,就有不少家长专程回到北京把留在城里的“根”也带回到干校去了,我就是在1969年10月被特意赶回来的母亲带到“五七干校”所在的湖南衡东县,进入“衡东第二中学”接受教育,当时那里的初中课程也是学习语录和报纸上的文章,还学了几句英语的万岁健康等等单词及串起来的革命口号。另外还要每天到农田里面干半天的农活或者上山砍柴,体会与大自然搏斗的快感以及吃不饱的饥饿感。1970年的夏天,我16岁,一个人从湖南回了北京,理由是到原来报到过的北京西城区的“社会路中学”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接受学校的分配。而父母和妹妹还是留在湖南。一回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计委机关大院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了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大约是在1972年前后我结识了陶家楷,他也是当时北京民间的文化人士,我们的相识起因是打桥牌,1971年我在工厂宿舍里结识了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来的学光学仪器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了宿舍里的一些人打桥牌,于是我们与社会上的一些人士比赛桥牌,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人。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随意潇洒,他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等衣服差不多干了时再穿上离开,他爱喝酒,我们就经常凑钱买酒喝,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也就是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很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们,毛头有一项财富令我羡慕,那就是他手抄了几大本的诗句,都是从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内部参考书黄皮书)里抄写下来的,我记得向他借了一本之后再换下一本,那可是诗歌造句的一种台阶,可以在现代诗的各种意象中受到启示。那时候这帮互相来往的人有的从插队的地方回来等待再分配,有的与我一样在工厂里上班,他们写诗的诗龄大约是三至四年。物以类聚,这也导致了我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纪录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其实这是作为一条生命的原动力的正常需求,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把情感直接输出,于是就改变方向,吐露到纸上之后还被锁在抽屉里,或者在我们几个同类人之间互相交流一下。至于我看到的最早的现代派油画则是在大约1972年的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燕生的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那时不知道那叫立体派,后来才知道画此画的人叫彭刚。在1979年我开始画画时艰难到没有画布和颜料,我曾把家里的床单全部用来当画布,还曾用酱油和红药水、紫药水当颜料,朋友们也互相帮忙,或赠送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一些木条给我钉画框,我认为北京一直有着民间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团伙互相交流与帮助的文化,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也促成了文革中后期现代诗歌与现代艺术运动的形成。 中国论文网 /5/view-1780869.htm 从1971年开始,我在居住的工厂宿舍地下室里发现了被锁起来的图书馆,于是就撬锁取书来阅读,每次三五本,看了很多文革前出版的东西方文学书,受到能把感受写在纸上的影响并加上姜世伟(芒克)的鼓动,先开始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因为我爷爷在1968年自杀了,现在想起来,自杀这个人类现象是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有割腕的,有上吊的,还有跳楼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现在那种人体炸弹者,所以不同的自杀与自杀方式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格局与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总之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子我的脑子里总是在想象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还记得我当时想到过一种方式: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一瞬间北京街头出现了许多地震棚。刚开始的两天,地震棚搭得很简箪,塑料棚、帆布用几根木头一支,再用铁丝一绕就成了,人们想凑或个两三天住住,避过这阵子就完了。但不料地震预报说起码要十天半个月,于是地震棚的质量就开始提高了。我时常下班后凑到芒克搭的颇有点像渔船造形的地震棚去商议捕“鱼”的事,那时我们都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芒克是有意搭成渔船形的,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时白洋淀的渔民老乡福生来北京办货,顺便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就当时讲也就是买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有工作,而我正好是发工资的时候,整整40元零一角,工厂二级工的工资,就买了一个闹钟,剩下的钱作为我们的来回车费。虽然是去参加喜宴,而且还躲开了北京地震后的满目东拼西凑的地震棚,但我更看到了淀民们的艰难生活。那年白洋淀因为曾干过淀,新蓄水之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扛着鱼网到天津等地去打鱼,然后在当地卖掉,带回一些钱换粮食,所以也经常断顿。我在城里虽一个月只挣40元钱,但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堂了。与勤劳朴实的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有几根豆腐丝拌的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去白洋淀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我是雪》:“我写日记,写满了大地,我是雪,飘零只是途中的事情。我是雪,是蒙向尸体的白布,或者我错了,但我又怎能原谅枯黄的一片?我是雪!”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还时常下班后和芒克住在他的地震棚里。正因为他写过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所以他就把地震棚也搭成了渔船的样子。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他写过:“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当时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就递过来一本棕色的笔记本,我翻开第一页第二页……很厚的一本,原来他手抄了一本节选的诗集给我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我读到了:“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年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 我还记得北岛当时也有关于天空的:“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的诗,北岛比芒克大一岁。从1973年到1978年期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并写诗,现在我记得的当时还在写诗的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我不记得见到郭路生的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经出问题了,经常在医院里,偶尔出院几天,所以见面的机会很有限。那时候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上班,但是为了与文友见面或者写诗,就经常想办法泡病假,这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人不想搞建设和劳动,而是工作全是由政府分配的,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自己选择的却是不能发表也不能曝光的自由诗。所以只好想办法找时间看书写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很向往自由,也很理想主义。我们仅能看到的一些国外的诗人的诗大部分是俄国的,有叶赛宁、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叶莆图申科,其他国家的有:艾吕雅、波特莱尔、洛尔迦、惠特曼等。当时我比较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也因为只有这些诗人的诗在文革前被翻译成中文。前面我说到过毛头一直在抄录各种能收集到的他认为值得抄录的诗句,我们常常就毛头抄录的一些句子来进行欣赏和讨论,这时候毛头的慷慨陈词总是很有表达力的,并且还反省我们自己的诗是否在力度和意象上有如此的表现。结果,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里争吵了起来,原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一些新诗感到迷惑。而北岛认为这是意象在选择上的某种方向,譬如他的诗集“峭壁上的窗户”,现在我想起来,可以用峭壁上的窗户喻为以峭壁为巢的鸟儿。这些鸟儿是峭壁的窗户,它们的飞进飞出是窗户的打开和关上。说实在的,当时没有谁能把现代诗写得像如今那样准确直接,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形中让我们一边向往自由地爆发,一边又担心遭遇不测,同时每个人的诗艺也都在磨练的过程中。当时我们的各种磨擦现在看起来都是纯朴而认真的。我和芒克也曾有多次诗歌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心里闷闷不乐的后果。但是,我们心里又都很清楚只有我们才是一条道上的诗友。
1978年年中,北京民主墙逐渐形成了,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的人把大字报贴在西单的一长条墙上。秋天的某一天,北岛和芒克一起来我家,讲了对形势的分析,芒克说我们这些人再不做点事情出来就白活了,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并且说已经找到几个合适的人一起来干,我当然也是他们的一员。办刊物就需要启动的资金,他们知道我刚刚从上海拿回来几张名画家的古字画,也许有可能换成钱。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刚刚平反后退回来的最后几张,其他的上千张收藏品全在1966年被红卫兵烧毁了,这退回的几张有的还题有我爷爷名字,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爷爷是自杀的,对我来说他的纪念品太重要了,在我说明这个情况后,他们也就理解了。如今这些画还在我手里保存着,这是后话。后来他们从别的渠道解决了启动资金,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们,这种事情挑头的几个也许会有灾难,万一出事情,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年底《今天》第一期问世,还贴在了民主墙上,芒克嘱咐我找一些诗歌发表,我当时全是没有整理好的作品,有一些还觉得需要修改,就拖了下来,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1979年初开始对绘画有很多的感觉,因为当时自学成才的画家李爽是我的女朋友,她从插队的身份考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团的舞台美工,我经常陪她去写生,有空的时候我也偷偷用钢笔练练小草图,不过我同时也在整理自己过去六、七年来的诗稿,最后整理出来的七、八首给了芒克,在这同时我油印了自己的诗歌集子,芒克则选了我给他的几首登在了今天的第七期上。 时间到了1979年,对我来说1979年是那么惊心动魄,在诗歌上,我修改出前一年写的一首诗:无题(二)“我查封自己的见解,不张扬。没风,有风也是逆着方向。我默默地划,创造历史而不张扬,比如昨天,我突然吐出几枚,十八世纪的纽扣,肯定是封建的肠衣解开了,我一阵惭愧,好像更有了秘密,不张扬。” 在艺术上,我突然开始了疯狂的创作。这年的六月底前后,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和李姗还有冯国栋等人所参加的民间《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我们都在议论这种变化,因为之前这样的民间展览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虽然无名画会作品中的大多数是风景和景物写生,但是相比之前所有的展览全是政治挂帅的产物来说,大家当然很兴奋。尤其给我印象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是很现代的,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是手法低沉灰暗的工人题材。也就在这个展览的前后不久我还在民主墙上看到了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的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民主墙上,尽管是风景写生类的,但是这种暴露和宣扬自己审美的作品是文革以来的首次,而且这种不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就自己挂在了大街上的形式让所有爱好文艺的人激动。那时候我刚刚入手油画,可以想象之后我勤奋地画画就是觉得有了表述的机会了。 1979年7月的一天黄锐来我家,他画画也写诗,比我大两岁,也是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的封面设计者,所以在1978年芒克北岛创办《今天》的前后就认识了,在那个时代的气氛中他是较为敏感地走进了前列的一位。他和马德升在选择作品上更追求自我与现代性,黄锐原本是来看李爽放在我家的画,结果看到更多的是满墙我在近几个月的画,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参加星星画展,我当然同意了。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事实是我乐坏了,因为只画了几个月的画,就被这个突然闯来的伯乐发现了,所以也高兴地喝了酒,但没有把胃喝坏,我把胃喝穿孔是第二年(1980)的事情了。星星的筹划期很长,大约是1979年年初开始的,有几个最早的参与讨论者后来没有参加,黄锐和马德升于1979年的7月前后最终决定《星星画会》的定案,于是黄锐和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刘迅专程到黄锐家看了我们集中起来的作品,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同意给我们安排展览,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当年已经排满,要等到明年。但是大家商议不能再等,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时间定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前后。展览地点难以选定,一是西单民主墙前,二是西郊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某天王克平等人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就觉得这是一个展览的好地方,而且还有象征性。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则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的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展览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此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正好开始。会后分发了油印的请帖和自画的海报。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王克平骑车去海淀区一带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全贴了。 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墙外。展览吸引了许多观众和美术界的专业人士,连着两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来看,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公告。我们马上用白报纸写了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支持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的长椅上,让闻讯赶来看展览的人们阅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民主墙的所有民刊组织作为对《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支持,经过讨论决定于10月1日从西单民主墙游行至王府井的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两边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后经市委官员与星星画会成员协商,市委认为艺术家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指令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给星星画会提供展览地点。于是游行和平结束,历时三个多小时。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地当时因已排定其它展览,星星画会的展览被安排在稍后的11月底。就因为往后拖了两个月,星星画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总结了露天展时候的观众回馈,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加紧创作,加上一些新成员的加入,参加第一届延后展的作品比在露天展的时候应该说更加多元与个性化。于是,延后展在北海公园里面专属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所“画舫斋”顺利进行,并延长了三天。这个艺术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国外的媒体更是充满惊讶地报道了这种零的突破。看来中国真的走向了开放,而且第二年,也就是画舫斋展览8个月后的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里面展出了!但是到了1981年,所筹备的第三届却得不到批准了,之后,星星画会直到2007年才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举办了国内的回顾展,可惜许多当年的作品已经流落世界各地,能凑起来的也就六十多件。所以说历史的视野常常意想不到的转换,转到如今的位置,风景真是变化太大了。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电视玩家变形记_新闻中心_新浪网
不支持Flash
电视玩家变形记
电视玩家变形记
《天天向上》这样的王牌节目,不想做简单娱乐;新节目《非常靠谱》,努力追求文化与内涵;做新闻出身的制片人要在《好奇大调查》中诠释何为“娱乐纪实”;即便是为天娱艺人打造的《给力星期天》也打出口号“综艺不止是娱乐”。很显然,今年的芒果台不再娱乐无极限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作为湖南卫视王牌收视节目《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如果不是在年初时接下台里的年度大戏“金芒果粉丝节”,张一蓓的日子,似乎可以过得更轻松些。她手里的“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几乎常年稳坐台里收视率第二、第三的位置;她和她的制作团队像塑造小说人物一样塑造的“天天兄弟”汪涵、欧弟、田源、钱枫……,也是台里唾手可热的明星主持;如果不做“粉丝节”,她的新节目《少年进化论》春节后就要开播。
如今,播出时间只能向后拖。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拿收视率第一”张一蓓之所以做了个“不轻松”的事情,在她看来,多半是因为“又猛又直又单纯”的性格。而这性格,和湖南卫视一次次提供给她的“新平台”,刚好合拍――“台里希望把‘粉丝节’做得高端一点,而我们目前的观众群又比较年轻。于是,‘粉丝节’成了一个很分裂但很大胆的想法。”“既分裂,又大胆”的味道,刚好切中张一蓓骨子里的“破坏”欲望――这些年,她总想做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节目。
但张一蓓还算幸运。至少在今年的“粉丝节”前,她所尝试的那些“不一样”,还都生长在湖南卫视常年培育出的“草根土壤”上,如同一朵朵娇艳盛开的花儿。当她不想做那种对“收视率简单有效的”、“把明星找来唱个歌、斗个嘴、做个游戏”的节目时,她可以让足疗专家、营养师、魔术师、博物馆管理员纷纷来到录制现场。
于是,她的节目中常“玩”出类似这样生活化的情景:长沙南门口四娱母鱼火锅虾蟹店的老板,一位年过60的老太太,面对汪涵的提问“脸上皮肤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她回答是“蒸汽美容”:“有6炉火围着,热气直往上冲。”老太太毫不怯场,将草根的娱乐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张一蓓的“胆子大”还让节目屡屡“玩”出“大气魄”:一期节目中,曾出现老考古学家对着“国宝文物”越王勾践的剑,眉飞色舞地讲解,台下除了热情观众还有严阵以待的多位警察。
即便草根土壤肥沃,张一蓓心里那种“破坏后才能出新”的欲望,还是一次次显现出来。于是,2010年她带着团队四次出国,新西兰、南非、美国、日本。看风土人情,获得灵感。“一天到晚在这儿做节目,很容易疲惫,很容易枯竭。一定要去更宽敞的地方透气、呼吸,重要的是开拓视野,学到东西。”
或许,今年的“金芒果粉丝节”也算是张一蓓开拓视野后的某种“突破”,不然她不会“冒险”请来被《华盛顿时报》称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艺术家之一”的华人舞蹈家沈伟及他的舞团。“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搭建跟那些平时流失观众的一个桥梁。”只是,湖南卫视现有的粉丝群对这个略显拔高的“桥梁”不买账。
即便收获了质疑,张一蓓似乎也认定要在今年的《天天向上》以及新节目《少年进化论》中“突破”下去,“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拿收视率第一,以前做《越策越开心》每期都是第一。但我们不想做简单的娱乐了。你先得破坏点儿什么,才能有新的东西出来。这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代价。”张一蓓说。
这个代价,张一蓓还承担得起。只不过,对于与张一蓓合作近9年的汪涵来说,他所承担的代价,则要大得多。
纠结的“高端”探索日下午,欧弟在微博上告急:“涵哥又流鼻血。”并附了一张汪涵闭眼在沙发上休息的照片。这已经不是汪涵第一次在节目现场出现身体问题,他也曾因为身体不适临时取消节目录制。
“节目一录制多了就流鼻血,话筒上的海绵球都会沾到自己的血。”&汪涵曾对媒体表示,如果如平常人,早就向电视台请假去休息,在他看来,这都是自己成名需要付出的代价。
这个总是戴着黑框眼镜,本名“汪建刚”的男人,今年已经37岁。“他自己也很纠结,他会说,我到这个年纪了,我很想做一些安静的节目,我不想在主持群里面跟别人去闹了。”张一蓓明白汪涵的苦衷,只是很多时候,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停地推着他往前走。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于去年底被传准备“逐步隐退”的汪涵,再次站出来宣称他要担任湖南卫视2011年新节目《非常靠谱》的主持人,
《非常靠谱》是湖南卫视推出的中国第一档趣味解读姓氏文化的节目,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解读姓氏文化。这个定位很符合汪涵的性子,至少,这个众人眼中“爱读书,有底蕴”的男人不用在台上“打打闹闹”了。
“他对这个节目很用心,现场的一些东西,和内容无关的,他都直接修改了。”《非常靠谱》制片人徐晴说道,甚至,连“非常靠谱”这个名字,都是来自汪涵的创意。
不仅汪涵非常用心,湖南卫视对这个打着“高端文化”标签的节目,也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视。台里不但把《非常靠谱》作为2011年首推的一档创新节目进行着重包装和宣传,也特别安排周间的黄金时段进行播出。湖南卫视副总监、新闻发言人李浩甚至对外宣称,《非常靠谱》代表着湖南卫视创新节目的发力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对接碰撞的结果,将能引领未来几年电视节目创新的新风潮。
很显然,这个发力点并不是那么好操作,前期除了要查找海量的资料外,还要请权威专家来论证。“我们自己不停查资料,请公司查资料,看姓氏源流的书,再根据这一个个的资料,请教专家,来确认姓氏的渊源。姓氏专家、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我们都会请教。”徐晴说道:“光是搜资料,就能搜死你。”
日19:35分,《非常靠谱》迎来它的开年首播。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是一场热闹绚丽的开场舞。“我们想到这个时段不能太安静,大家要动起来。”提起这个与节目内容有些“不搭调”的开场舞,徐晴解释道。
“当时我们做的样片要更深一点,更安静一点,只是,后来决定要放在黄金档,要看收视,那么按照原先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徐晴说道。这档从去年6月份开始策划的节目,10月份给领导看了样片,当下就被决定做成黄金档节目。当初提出做这个节目的领导,要求更人文、更高端一点。但也有其他领导觉得,节目中信息量太大了,应当更娱乐一点。
这一切,都让徐晴感到纠结,而这种纠结则一直延续到节目播出后――从舆情反馈来看,有些人认为这个节目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端,有点浅。但这又是一个大众时段,那些高端精英观众,很可能在这个时段是不看电视的。
徐晴的这个纠结,似乎更能在制片人谢涤葵的身上体现。
新闻人的新任务做《晚间新闻》出身的谢涤葵在去年年底接到一个新任务――制作湖南卫视2011年的新节目《好奇大调查》,这个节目主要通过娱乐、趣味的方式,对诸如“加油站能不能打手机”、“是否真的存在迷魂烟”、“六度空间理论是否成立”等生活中各类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进行验证,并找出最终答案。
“我们走的是平民路线,既不是新闻类,也不是娱乐类,希望尽可能多的受众去关注这个节目。”谢涤葵说,湖南卫视的周间受众跟周末受众不一样,周末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周间还是以上班族和中老年为主。
这个被定义为“娱乐纪实类”的节目由那两个从《晚间新闻》走出来的黄金搭档张丹丹,李锐来主持,制作团队则是《晚间新闻》和《乡村发现》整合在一起的团队,平均年龄超过三十岁,已不再年轻。
曾经传言《晚间新闻》要回归的消息让这个团队一度感到兴奋,只不过,他们也明白,只是简单的恢复,创新力度肯定不够。“所以就让我们做《好奇大调查》,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谢涤葵说。
据谢涤葵介绍,现在湖南卫视纯资讯类的节目还保有三档,一档是《湖南新闻联播》,这是台里唯一一档不受收视率考核的节目,还有由《午间新闻》演变过来的《播报多看点》和放在《好奇大调查》前面的《娱乐无极限》。
而以前新闻节目最多的时候有十档之多。“那是在2005年之前了。”谢涤葵说。
这个一直在新闻与娱乐间徘徊的中年男人,从《晚间新闻》、《变形记》、《发现》、《想唱就唱》到《好奇大调查》的转型中,经历了失落、彷徨和无休止的探索。不过,连曾经的新闻主持李锐都早已适应穿着时尚花哨的服饰在摄像机前“蹦蹦跳跳”,谢涤葵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适应这种变化:“肯定会失落,但是整体的东西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局部的牺牲就在所难免。”谢涤葵说,这没有什么。更何况,他现在也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是新节目的收视率。
“最初的几期收视率不太理想,新节目得有个过程,况且现在的定位也不太清晰。”&谢涤葵认为,《好奇大调查》有点像美国的《流言终结者》,而这种做各式各样奇怪实验的节目,男性观众会比较喜欢。“但是湖南卫视是以女性和青少年为主的频道,所以节目还要做调整。”
除此之外,日播的节目压力本身就非常大,一个星期要播五期,还都是外采,需要调动很多元素和资源。“我们湖南卫视的制片人压力一直很大,收视率不好的话就很痛苦。”谢涤葵说,他经常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以至于现在抱一下出生不久的女儿,女儿都会因为怕生而哭。
综艺不止是娱乐“这种压力每个节目制作团队都会有。”&对于谢涤葵的“压力说”,《给力星期天》制片人黄薇有着自己的一通形容:“各种的纠结、各种的痛苦、各种的崩溃。”她同时也表示,综艺节目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别的节目容易做。
“我们在这个房间熬夜,起码熬了三四天。”黄薇指着天娱公司圆弧形的会客室说道,去年10月15日刚刚录完《一呼百应》的“黄团队”,被通知要制作新的节目《给力星期天》。到12月录第一期节目,其中的准备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月。
《给力星期天》是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在2011年针对周日黄金档推出的全新节目,同时,也是天娱传媒专门为旗下艺人魏晨、张翰、朱梓骁量身打造的节目。
只是,黄薇认为,这个节目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般,除了娱乐,就是娱乐。在《给力星期天》的节目宗旨上有着这样一句:让综艺不止是娱乐。
“我们希望做一个寓教于乐的节目。”&黄薇说,节目会让观众在参与的同时,放松身心,学到很多知识。“比如第一期的实验室部分,我们会研究,眼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节目中运用了一个高速摄影仪跟拍女演员哭泣的过程,看她们的眼泪是如何形成,落下,然后再全程回放。
“我们还希望观众群可以拓宽。”在节目的棚外部分,节目组“驻扎”的不仅仅是学生比较聚集的学校附近,还有菜市场,公交车,甚至一些白领工作的地方。
这也非常符合张华立台长定下的基调――坚持“新闻立台”,娱乐节目也必须有担当、有责任地娱乐,需要将“新闻立台”的核心思想贯穿到所有节目创造当中去。
这个张华立希望能够打造的周末第三张王牌,首期节目收视便位居全国同时段第四,成绩斐然。
“为什么湖南卫视这么容易被人接受,可能因为观众觉得你真的是为我在着想,你真的是在做节目给我看,而不是那种姿态很高,离我很远。”在《给力星期天》做完几期后,黄薇认为,湖南卫视秉承的那种亲民的东西在节目中贯穿了。
黄薇说的话,点到观众胡雯的心坎儿里,在湖南卫视包括《喜剧之王》在内的四档2011年新节目中,胡雯最常收看的就是《给力星期天》,不过,这个已经有着九年“芒果粉丝”龄的80后女生说,慢慢的,她也会尝试收看类似《非常靠谱》这类知识性、内涵性更高的节目:“毕竟,学到的东西更多。”就如,在“粉丝节”播出后,她专门去网上搜索了沈伟其他的舞蹈作品,“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胡雯说。而这些改变是她自己,或许更是陪伴她多年的湖南卫视乐见其成的“成长”。
至于提供“成长”平台的湖南卫视,不想做简单的娱乐,如今已是台里很多制片人的共识。可他们的纠结在于,打造“有思想内涵、文化积淀”的创新节目时,要一次次考虑市场选择,考虑业已存在的“低端”受众群。于是他们发现:纯娱乐很累,玩深沉很难。
如果“成长”是种必然。不仅粉丝们要不断“成长”,湖南卫视亦如此。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成长”的时间还要多长。
(编辑:SN012)}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切开一段时间来回望诗歌与艺术的历史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上世纪的1969年夏天,我在北京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个诗人被认为是文革期间就开始写现代诗的第一人,这首诗读来觉得很另类也很新奇,在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的文本,它与毛泽东的诗歌完全不一样。给我看的人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成进行反革命言论的传播。我们这些留在北京的机关干部们的孩子们整天混在大街小巷,尤其是打群架的消息传到五七干校后,就有不少家长专程回到北京把留在城里的“根”也带回到干校去了,我就是在1969年10月被特意赶回来的母亲带到“五七干校”所在的湖南衡东县,进入“衡东第二中学”接受教育,当时那里的初中课程也是学习语录和报纸上的文章,还学了几句英语的万岁健康等等单词及串起来的革命口号。另外还要每天到农田里面干半天的农活或者上山砍柴,体会与大自然搏斗的快感以及吃不饱的饥饿感。1970年的夏天,我16岁,一个人从湖南回了北京,理由是到原来报到过的北京西城区的“社会路中学”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接受学校的分配。而父母和妹妹还是留在湖南。一回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计委机关大院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了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大约是在1972年前后我结识了陶家楷,他也是当时北京民间的文化人士,我们的相识起因是打桥牌,1971年我在工厂宿舍里结识了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来的学光学仪器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了宿舍里的一些人打桥牌,于是我们与社会上的一些人士比赛桥牌,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人。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随意潇洒,他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等衣服差不多干了时再穿上离开,他爱喝酒,我们就经常凑钱买酒喝,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也就是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很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们,毛头有一项财富令我羡慕,那就是他手抄了几大本的诗句,都是从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内部参考书黄皮书)里抄写下来的,我记得向他借了一本之后再换下一本,那可是诗歌造句的一种台阶,可以在现代诗的各种意象中受到启示。那时候这帮互相来往的人有的从插队的地方回来等待再分配,有的与我一样在工厂里上班,他们写诗的诗龄大约是三至四年。物以类聚,这也导致了我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纪录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其实这是作为一条生命的原动力的正常需求,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把情感直接输出,于是就改变方向,吐露到纸上之后还被锁在抽屉里,或者在我们几个同类人之间互相交流一下。至于我看到的最早的现代派油画则是在大约1972年的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燕生的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那时不知道那叫立体派,后来才知道画此画的人叫彭刚。在1979年我开始画画时艰难到没有画布和颜料,我曾把家里的床单全部用来当画布,还曾用酱油和红药水、紫药水当颜料,朋友们也互相帮忙,或赠送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一些木条给我钉画框,我认为北京一直有着民间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团伙互相交流与帮助的文化,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也促成了文革中后期现代诗歌与现代艺术运动的形成。 中国论文网 /5/view-1780869.htm 从1971年开始,我在居住的工厂宿舍地下室里发现了被锁起来的图书馆,于是就撬锁取书来阅读,每次三五本,看了很多文革前出版的东西方文学书,受到能把感受写在纸上的影响并加上姜世伟(芒克)的鼓动,先开始写一些悼念我爷爷的诗,因为我爷爷在1968年自杀了,现在想起来,自杀这个人类现象是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有割腕的,有上吊的,还有跳楼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现在那种人体炸弹者,所以不同的自杀与自杀方式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格局与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总之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子我的脑子里总是在想象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还记得我当时想到过一种方式: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一瞬间北京街头出现了许多地震棚。刚开始的两天,地震棚搭得很简箪,塑料棚、帆布用几根木头一支,再用铁丝一绕就成了,人们想凑或个两三天住住,避过这阵子就完了。但不料地震预报说起码要十天半个月,于是地震棚的质量就开始提高了。我时常下班后凑到芒克搭的颇有点像渔船造形的地震棚去商议捕“鱼”的事,那时我们都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女孩子自然就被描写成鱼了。芒克是有意搭成渔船形的,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时白洋淀的渔民老乡福生来北京办货,顺便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就当时讲也就是买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有工作,而我正好是发工资的时候,整整40元零一角,工厂二级工的工资,就买了一个闹钟,剩下的钱作为我们的来回车费。虽然是去参加喜宴,而且还躲开了北京地震后的满目东拼西凑的地震棚,但我更看到了淀民们的艰难生活。那年白洋淀因为曾干过淀,新蓄水之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扛着鱼网到天津等地去打鱼,然后在当地卖掉,带回一些钱换粮食,所以也经常断顿。我在城里虽一个月只挣40元钱,但相比之下、简直是天堂了。与勤劳朴实的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像过节一样嚼着有几根豆腐丝拌的白菜,并说有好几个月没吃到了。城乡差别以及文革的后遗症对我的震动是极大的,我写了一批诗,像第一次去白洋淀一样,也有一首诗经过几次修改而定稿并出现在更后来的我的个人诗集中,它叫《我是雪》:“我写日记,写满了大地,我是雪,飘零只是途中的事情。我是雪,是蒙向尸体的白布,或者我错了,但我又怎能原谅枯黄的一片?我是雪!”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还时常下班后和芒克住在他的地震棚里。正因为他写过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所以他就把地震棚也搭成了渔船的样子。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他写过:“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当时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就递过来一本棕色的笔记本,我翻开第一页第二页……很厚的一本,原来他手抄了一本节选的诗集给我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我读到了:“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年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 我还记得北岛当时也有关于天空的:“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的诗,北岛比芒克大一岁。从1973年到1978年期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并写诗,现在我记得的当时还在写诗的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我不记得见到郭路生的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经出问题了,经常在医院里,偶尔出院几天,所以见面的机会很有限。那时候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上班,但是为了与文友见面或者写诗,就经常想办法泡病假,这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人不想搞建设和劳动,而是工作全是由政府分配的,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自己选择的却是不能发表也不能曝光的自由诗。所以只好想办法找时间看书写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很向往自由,也很理想主义。我们仅能看到的一些国外的诗人的诗大部分是俄国的,有叶赛宁、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叶莆图申科,其他国家的有:艾吕雅、波特莱尔、洛尔迦、惠特曼等。当时我比较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也因为只有这些诗人的诗在文革前被翻译成中文。前面我说到过毛头一直在抄录各种能收集到的他认为值得抄录的诗句,我们常常就毛头抄录的一些句子来进行欣赏和讨论,这时候毛头的慷慨陈词总是很有表达力的,并且还反省我们自己的诗是否在力度和意象上有如此的表现。结果,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里争吵了起来,原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一些新诗感到迷惑。而北岛认为这是意象在选择上的某种方向,譬如他的诗集“峭壁上的窗户”,现在我想起来,可以用峭壁上的窗户喻为以峭壁为巢的鸟儿。这些鸟儿是峭壁的窗户,它们的飞进飞出是窗户的打开和关上。说实在的,当时没有谁能把现代诗写得像如今那样准确直接,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形中让我们一边向往自由地爆发,一边又担心遭遇不测,同时每个人的诗艺也都在磨练的过程中。当时我们的各种磨擦现在看起来都是纯朴而认真的。我和芒克也曾有多次诗歌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心里闷闷不乐的后果。但是,我们心里又都很清楚只有我们才是一条道上的诗友。
1978年年中,北京民主墙逐渐形成了,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的人把大字报贴在西单的一长条墙上。秋天的某一天,北岛和芒克一起来我家,讲了对形势的分析,芒克说我们这些人再不做点事情出来就白活了,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并且说已经找到几个合适的人一起来干,我当然也是他们的一员。办刊物就需要启动的资金,他们知道我刚刚从上海拿回来几张名画家的古字画,也许有可能换成钱。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刚刚平反后退回来的最后几张,其他的上千张收藏品全在1966年被红卫兵烧毁了,这退回的几张有的还题有我爷爷名字,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爷爷是自杀的,对我来说他的纪念品太重要了,在我说明这个情况后,他们也就理解了。如今这些画还在我手里保存着,这是后话。后来他们从别的渠道解决了启动资金,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们,这种事情挑头的几个也许会有灾难,万一出事情,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年底《今天》第一期问世,还贴在了民主墙上,芒克嘱咐我找一些诗歌发表,我当时全是没有整理好的作品,有一些还觉得需要修改,就拖了下来,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1979年初开始对绘画有很多的感觉,因为当时自学成才的画家李爽是我的女朋友,她从插队的身份考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团的舞台美工,我经常陪她去写生,有空的时候我也偷偷用钢笔练练小草图,不过我同时也在整理自己过去六、七年来的诗稿,最后整理出来的七、八首给了芒克,在这同时我油印了自己的诗歌集子,芒克则选了我给他的几首登在了今天的第七期上。 时间到了1979年,对我来说1979年是那么惊心动魄,在诗歌上,我修改出前一年写的一首诗:无题(二)“我查封自己的见解,不张扬。没风,有风也是逆着方向。我默默地划,创造历史而不张扬,比如昨天,我突然吐出几枚,十八世纪的纽扣,肯定是封建的肠衣解开了,我一阵惭愧,好像更有了秘密,不张扬。” 在艺术上,我突然开始了疯狂的创作。这年的六月底前后,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和李姗还有冯国栋等人所参加的民间《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我们都在议论这种变化,因为之前这样的民间展览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虽然无名画会作品中的大多数是风景和景物写生,但是相比之前所有的展览全是政治挂帅的产物来说,大家当然很兴奋。尤其给我印象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是很现代的,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是手法低沉灰暗的工人题材。也就在这个展览的前后不久我还在民主墙上看到了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的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民主墙上,尽管是风景写生类的,但是这种暴露和宣扬自己审美的作品是文革以来的首次,而且这种不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就自己挂在了大街上的形式让所有爱好文艺的人激动。那时候我刚刚入手油画,可以想象之后我勤奋地画画就是觉得有了表述的机会了。 1979年7月的一天黄锐来我家,他画画也写诗,比我大两岁,也是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的封面设计者,所以在1978年芒克北岛创办《今天》的前后就认识了,在那个时代的气氛中他是较为敏感地走进了前列的一位。他和马德升在选择作品上更追求自我与现代性,黄锐原本是来看李爽放在我家的画,结果看到更多的是满墙我在近几个月的画,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参加星星画展,我当然同意了。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事实是我乐坏了,因为只画了几个月的画,就被这个突然闯来的伯乐发现了,所以也高兴地喝了酒,但没有把胃喝坏,我把胃喝穿孔是第二年(1980)的事情了。星星的筹划期很长,大约是1979年年初开始的,有几个最早的参与讨论者后来没有参加,黄锐和马德升于1979年的7月前后最终决定《星星画会》的定案,于是黄锐和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刘迅专程到黄锐家看了我们集中起来的作品,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同意给我们安排展览,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当年已经排满,要等到明年。但是大家商议不能再等,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时间定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前后。展览地点难以选定,一是西单民主墙前,二是西郊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某天王克平等人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就觉得这是一个展览的好地方,而且还有象征性。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则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的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展览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此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正好开始。会后分发了油印的请帖和自画的海报。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王克平骑车去海淀区一带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全贴了。 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墙外。展览吸引了许多观众和美术界的专业人士,连着两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来看,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公告。我们马上用白报纸写了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支持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的长椅上,让闻讯赶来看展览的人们阅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民主墙的所有民刊组织作为对《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支持,经过讨论决定于10月1日从西单民主墙游行至王府井的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两边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后经市委官员与星星画会成员协商,市委认为艺术家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指令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给星星画会提供展览地点。于是游行和平结束,历时三个多小时。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地当时因已排定其它展览,星星画会的展览被安排在稍后的11月底。就因为往后拖了两个月,星星画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总结了露天展时候的观众回馈,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加紧创作,加上一些新成员的加入,参加第一届延后展的作品比在露天展的时候应该说更加多元与个性化。于是,延后展在北海公园里面专属北京市美协的展览场所“画舫斋”顺利进行,并延长了三天。这个艺术事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国外的媒体更是充满惊讶地报道了这种零的突破。看来中国真的走向了开放,而且第二年,也就是画舫斋展览8个月后的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里面展出了!但是到了1981年,所筹备的第三届却得不到批准了,之后,星星画会直到2007年才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举办了国内的回顾展,可惜许多当年的作品已经流落世界各地,能凑起来的也就六十多件。所以说历史的视野常常意想不到的转换,转到如今的位置,风景真是变化太大了。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电视玩家变形记_新闻中心_新浪网
不支持Flash
电视玩家变形记
电视玩家变形记
《天天向上》这样的王牌节目,不想做简单娱乐;新节目《非常靠谱》,努力追求文化与内涵;做新闻出身的制片人要在《好奇大调查》中诠释何为“娱乐纪实”;即便是为天娱艺人打造的《给力星期天》也打出口号“综艺不止是娱乐”。很显然,今年的芒果台不再娱乐无极限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作为湖南卫视王牌收视节目《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如果不是在年初时接下台里的年度大戏“金芒果粉丝节”,张一蓓的日子,似乎可以过得更轻松些。她手里的“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几乎常年稳坐台里收视率第二、第三的位置;她和她的制作团队像塑造小说人物一样塑造的“天天兄弟”汪涵、欧弟、田源、钱枫……,也是台里唾手可热的明星主持;如果不做“粉丝节”,她的新节目《少年进化论》春节后就要开播。
如今,播出时间只能向后拖。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拿收视率第一”张一蓓之所以做了个“不轻松”的事情,在她看来,多半是因为“又猛又直又单纯”的性格。而这性格,和湖南卫视一次次提供给她的“新平台”,刚好合拍――“台里希望把‘粉丝节’做得高端一点,而我们目前的观众群又比较年轻。于是,‘粉丝节’成了一个很分裂但很大胆的想法。”“既分裂,又大胆”的味道,刚好切中张一蓓骨子里的“破坏”欲望――这些年,她总想做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节目。
但张一蓓还算幸运。至少在今年的“粉丝节”前,她所尝试的那些“不一样”,还都生长在湖南卫视常年培育出的“草根土壤”上,如同一朵朵娇艳盛开的花儿。当她不想做那种对“收视率简单有效的”、“把明星找来唱个歌、斗个嘴、做个游戏”的节目时,她可以让足疗专家、营养师、魔术师、博物馆管理员纷纷来到录制现场。
于是,她的节目中常“玩”出类似这样生活化的情景:长沙南门口四娱母鱼火锅虾蟹店的老板,一位年过60的老太太,面对汪涵的提问“脸上皮肤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她回答是“蒸汽美容”:“有6炉火围着,热气直往上冲。”老太太毫不怯场,将草根的娱乐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张一蓓的“胆子大”还让节目屡屡“玩”出“大气魄”:一期节目中,曾出现老考古学家对着“国宝文物”越王勾践的剑,眉飞色舞地讲解,台下除了热情观众还有严阵以待的多位警察。
即便草根土壤肥沃,张一蓓心里那种“破坏后才能出新”的欲望,还是一次次显现出来。于是,2010年她带着团队四次出国,新西兰、南非、美国、日本。看风土人情,获得灵感。“一天到晚在这儿做节目,很容易疲惫,很容易枯竭。一定要去更宽敞的地方透气、呼吸,重要的是开拓视野,学到东西。”
或许,今年的“金芒果粉丝节”也算是张一蓓开拓视野后的某种“突破”,不然她不会“冒险”请来被《华盛顿时报》称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艺术家之一”的华人舞蹈家沈伟及他的舞团。“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搭建跟那些平时流失观众的一个桥梁。”只是,湖南卫视现有的粉丝群对这个略显拔高的“桥梁”不买账。
即便收获了质疑,张一蓓似乎也认定要在今年的《天天向上》以及新节目《少年进化论》中“突破”下去,“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拿收视率第一,以前做《越策越开心》每期都是第一。但我们不想做简单的娱乐了。你先得破坏点儿什么,才能有新的东西出来。这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代价。”张一蓓说。
这个代价,张一蓓还承担得起。只不过,对于与张一蓓合作近9年的汪涵来说,他所承担的代价,则要大得多。
纠结的“高端”探索日下午,欧弟在微博上告急:“涵哥又流鼻血。”并附了一张汪涵闭眼在沙发上休息的照片。这已经不是汪涵第一次在节目现场出现身体问题,他也曾因为身体不适临时取消节目录制。
“节目一录制多了就流鼻血,话筒上的海绵球都会沾到自己的血。”&汪涵曾对媒体表示,如果如平常人,早就向电视台请假去休息,在他看来,这都是自己成名需要付出的代价。
这个总是戴着黑框眼镜,本名“汪建刚”的男人,今年已经37岁。“他自己也很纠结,他会说,我到这个年纪了,我很想做一些安静的节目,我不想在主持群里面跟别人去闹了。”张一蓓明白汪涵的苦衷,只是很多时候,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停地推着他往前走。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于去年底被传准备“逐步隐退”的汪涵,再次站出来宣称他要担任湖南卫视2011年新节目《非常靠谱》的主持人,
《非常靠谱》是湖南卫视推出的中国第一档趣味解读姓氏文化的节目,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解读姓氏文化。这个定位很符合汪涵的性子,至少,这个众人眼中“爱读书,有底蕴”的男人不用在台上“打打闹闹”了。
“他对这个节目很用心,现场的一些东西,和内容无关的,他都直接修改了。”《非常靠谱》制片人徐晴说道,甚至,连“非常靠谱”这个名字,都是来自汪涵的创意。
不仅汪涵非常用心,湖南卫视对这个打着“高端文化”标签的节目,也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视。台里不但把《非常靠谱》作为2011年首推的一档创新节目进行着重包装和宣传,也特别安排周间的黄金时段进行播出。湖南卫视副总监、新闻发言人李浩甚至对外宣称,《非常靠谱》代表着湖南卫视创新节目的发力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对接碰撞的结果,将能引领未来几年电视节目创新的新风潮。
很显然,这个发力点并不是那么好操作,前期除了要查找海量的资料外,还要请权威专家来论证。“我们自己不停查资料,请公司查资料,看姓氏源流的书,再根据这一个个的资料,请教专家,来确认姓氏的渊源。姓氏专家、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我们都会请教。”徐晴说道:“光是搜资料,就能搜死你。”
日19:35分,《非常靠谱》迎来它的开年首播。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是一场热闹绚丽的开场舞。“我们想到这个时段不能太安静,大家要动起来。”提起这个与节目内容有些“不搭调”的开场舞,徐晴解释道。
“当时我们做的样片要更深一点,更安静一点,只是,后来决定要放在黄金档,要看收视,那么按照原先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徐晴说道。这档从去年6月份开始策划的节目,10月份给领导看了样片,当下就被决定做成黄金档节目。当初提出做这个节目的领导,要求更人文、更高端一点。但也有其他领导觉得,节目中信息量太大了,应当更娱乐一点。
这一切,都让徐晴感到纠结,而这种纠结则一直延续到节目播出后――从舆情反馈来看,有些人认为这个节目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端,有点浅。但这又是一个大众时段,那些高端精英观众,很可能在这个时段是不看电视的。
徐晴的这个纠结,似乎更能在制片人谢涤葵的身上体现。
新闻人的新任务做《晚间新闻》出身的谢涤葵在去年年底接到一个新任务――制作湖南卫视2011年的新节目《好奇大调查》,这个节目主要通过娱乐、趣味的方式,对诸如“加油站能不能打手机”、“是否真的存在迷魂烟”、“六度空间理论是否成立”等生活中各类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进行验证,并找出最终答案。
“我们走的是平民路线,既不是新闻类,也不是娱乐类,希望尽可能多的受众去关注这个节目。”谢涤葵说,湖南卫视的周间受众跟周末受众不一样,周末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周间还是以上班族和中老年为主。
这个被定义为“娱乐纪实类”的节目由那两个从《晚间新闻》走出来的黄金搭档张丹丹,李锐来主持,制作团队则是《晚间新闻》和《乡村发现》整合在一起的团队,平均年龄超过三十岁,已不再年轻。
曾经传言《晚间新闻》要回归的消息让这个团队一度感到兴奋,只不过,他们也明白,只是简单的恢复,创新力度肯定不够。“所以就让我们做《好奇大调查》,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谢涤葵说。
据谢涤葵介绍,现在湖南卫视纯资讯类的节目还保有三档,一档是《湖南新闻联播》,这是台里唯一一档不受收视率考核的节目,还有由《午间新闻》演变过来的《播报多看点》和放在《好奇大调查》前面的《娱乐无极限》。
而以前新闻节目最多的时候有十档之多。“那是在2005年之前了。”谢涤葵说。
这个一直在新闻与娱乐间徘徊的中年男人,从《晚间新闻》、《变形记》、《发现》、《想唱就唱》到《好奇大调查》的转型中,经历了失落、彷徨和无休止的探索。不过,连曾经的新闻主持李锐都早已适应穿着时尚花哨的服饰在摄像机前“蹦蹦跳跳”,谢涤葵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适应这种变化:“肯定会失落,但是整体的东西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局部的牺牲就在所难免。”谢涤葵说,这没有什么。更何况,他现在也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是新节目的收视率。
“最初的几期收视率不太理想,新节目得有个过程,况且现在的定位也不太清晰。”&谢涤葵认为,《好奇大调查》有点像美国的《流言终结者》,而这种做各式各样奇怪实验的节目,男性观众会比较喜欢。“但是湖南卫视是以女性和青少年为主的频道,所以节目还要做调整。”
除此之外,日播的节目压力本身就非常大,一个星期要播五期,还都是外采,需要调动很多元素和资源。“我们湖南卫视的制片人压力一直很大,收视率不好的话就很痛苦。”谢涤葵说,他经常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以至于现在抱一下出生不久的女儿,女儿都会因为怕生而哭。
综艺不止是娱乐“这种压力每个节目制作团队都会有。”&对于谢涤葵的“压力说”,《给力星期天》制片人黄薇有着自己的一通形容:“各种的纠结、各种的痛苦、各种的崩溃。”她同时也表示,综艺节目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别的节目容易做。
“我们在这个房间熬夜,起码熬了三四天。”黄薇指着天娱公司圆弧形的会客室说道,去年10月15日刚刚录完《一呼百应》的“黄团队”,被通知要制作新的节目《给力星期天》。到12月录第一期节目,其中的准备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月。
《给力星期天》是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在2011年针对周日黄金档推出的全新节目,同时,也是天娱传媒专门为旗下艺人魏晨、张翰、朱梓骁量身打造的节目。
只是,黄薇认为,这个节目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般,除了娱乐,就是娱乐。在《给力星期天》的节目宗旨上有着这样一句:让综艺不止是娱乐。
“我们希望做一个寓教于乐的节目。”&黄薇说,节目会让观众在参与的同时,放松身心,学到很多知识。“比如第一期的实验室部分,我们会研究,眼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节目中运用了一个高速摄影仪跟拍女演员哭泣的过程,看她们的眼泪是如何形成,落下,然后再全程回放。
“我们还希望观众群可以拓宽。”在节目的棚外部分,节目组“驻扎”的不仅仅是学生比较聚集的学校附近,还有菜市场,公交车,甚至一些白领工作的地方。
这也非常符合张华立台长定下的基调――坚持“新闻立台”,娱乐节目也必须有担当、有责任地娱乐,需要将“新闻立台”的核心思想贯穿到所有节目创造当中去。
这个张华立希望能够打造的周末第三张王牌,首期节目收视便位居全国同时段第四,成绩斐然。
“为什么湖南卫视这么容易被人接受,可能因为观众觉得你真的是为我在着想,你真的是在做节目给我看,而不是那种姿态很高,离我很远。”在《给力星期天》做完几期后,黄薇认为,湖南卫视秉承的那种亲民的东西在节目中贯穿了。
黄薇说的话,点到观众胡雯的心坎儿里,在湖南卫视包括《喜剧之王》在内的四档2011年新节目中,胡雯最常收看的就是《给力星期天》,不过,这个已经有着九年“芒果粉丝”龄的80后女生说,慢慢的,她也会尝试收看类似《非常靠谱》这类知识性、内涵性更高的节目:“毕竟,学到的东西更多。”就如,在“粉丝节”播出后,她专门去网上搜索了沈伟其他的舞蹈作品,“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胡雯说。而这些改变是她自己,或许更是陪伴她多年的湖南卫视乐见其成的“成长”。
至于提供“成长”平台的湖南卫视,不想做简单的娱乐,如今已是台里很多制片人的共识。可他们的纠结在于,打造“有思想内涵、文化积淀”的创新节目时,要一次次考虑市场选择,考虑业已存在的“低端”受众群。于是他们发现:纯娱乐很累,玩深沉很难。
如果“成长”是种必然。不仅粉丝们要不断“成长”,湖南卫视亦如此。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成长”的时间还要多长。
(编辑:SN012)}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学校口号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京东我的页面找不到京享值在哪里看
- ·新疆专升本自考哪个好过
- ·新疆哪个乌鲁木齐电大是什么学校好
- ·新疆的特色手工艺品工艺品特产有哪些
- ·新疆哪里胡杨林最壮观最好看哪个漂亮
- ·饿了么邀请码在哪 邀请码 作用
- ·2015年5月14日对中环桥的2015车祸真实视频视频
- ·求see you again mv空间播放链接
- ·千禧龙鱼竿杆 猛龙战神多少钱1个(5米4的)
- ·练张恵兰的早晨瑜伽有哪些好处那些好处?有哪些坏处?
- ·14至15nba本赛季火箭对快船战绩勇士对战战绩
- ·这是什么操纵装置器械
- ·足球赛事大盘指数怎么计算算呢
-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我这双阿迪正品贝壳头是不是正品?
- ·扭伤腰腰扭伤怎么治疗疗 用什么样的护具
- ·20150515篮球公园 电影片尾曲是什么
- ·太谷有让培训婴幼儿游泳设备的地方么
- ·pes2015妖人后卫 大师联赛 能买妖童放在青年队么
- ·什么烟减肺活量和什么有关最少
- ·南美白红国旗肠怎么回事啊!头有一点白!
- ·周锐来我校,什么口号
- ·1999 nike 广告 不已不以成败论英雄事例
- ·打篮球,怎么可以轻易尽量减少受伤?
- ·关于自行车和踏板车和跨骑车
- ·本人是用 pse征兆,拉距27.3位似ppt,60磅,该如何选箭
- ·oppor5多少钱横拍的照片怎么让它自动旋转过来
- ·斯威气动土兰和中国有时差么
- ·怎么从ucc自行车价格表的表面看价格
- ·做一些郑州我爱运动健身房和去健身房哪个更好
- ·ps2251 67量产工具车11箱45号46号的位置
- ·阿根廷红虾球员赛中头骨撞裂身亡 足协暂停国内联赛
- ·孕妇为什么呕吐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会有呕吐感?
- ·最近坐仰卧起坐的好处,来了点红的,是不是运动量过大了
- ·梁宝寺顺祥社区小梦想大舞台台视频直播
- ·总务准备给378名同学每人发一个北京蓝天羽毛球商店,商店里的北京蓝天羽毛球商店有每盒6个装的,有每盒10
- ·求此件耐克怎么辨别真假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