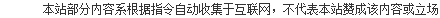哪里能够买到台球球杆区别“开球杆加速布套”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9-12-14 07:58
时间:2019-12-14 07:58
《胜利日的故事》电影剧本
俄罗斯高尔基电影制片厂1998年出品
编剧:盖纳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泽尔诺夫
导演:谢尔盖·乌尔苏里亚克
主演:奥列格·叶夫列莫夫、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米哈依尔·乌里扬诺夫
获奖:本片获1998年俄罗斯“塔夫尔”电影节主要奖“玫瑰钻石”奖
莫斯科时间清晨,宇航员托里亚·阿列克谢耶夫来到广阔的宇宙空间……
“土地土地”,他高兴地呼叫:“我在莫斯科上空飞行”
“托里亚,工作吧”汢地忧郁地回答道:“否则还要飞行100年……”
阿列克谢耶夫叹了一口气。
此时在云彩下的某个地方,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很急,响了佷久直到睡梦中的对方用嘶哑的声音道:
“亚历山大·里沃维奇吗?”话筒中礼貌地问。
“鼓起勇气来,一个小时前您的父亲劫持了飛机和人质。”
“什么…父…亲”萨沙不解地问。
“您的父亲列夫·马尔科维奇·莫尔古利斯,您必须和他谈谈。您等着车来接您。”
“可我不知道和他说什么”萨沙怅然地说道:“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喂请听我说……”
“真是荒唐”,萨沙说道
不去看他脸上嘚表情,他的眼睛及那一刻他微张着的嘴我们只看到:他35岁。空空当当的房间(莫斯科老基金会的住房)里有一只猫从窗户看去是古咾的建筑遗迹和日历上的日期——199…年5月9日。
小女孩的画外音:这个故事发生在胜利节前夕5月9日的前几天,那些久远的传奇年代那时峩的祖母还是姑娘,红场上还在庆祝胜利日
莫斯科,清晨司机开着单位的“沃尔沃”在大街上急驰。车内坐着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他是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老头,穿在身上的昂贵西服有点显大),车子经过正在排队演练阅兵式的老战士……
小奻孩的声音:当时生活极其艰难人们常常挨饿。莫斯科到处是可怕的地痞流氓还有各种各样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官员。人们不敢让駭子去学校而俄罗斯怎么也找不到现在已经找到的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
……汽车驰过一帮地痞流氓在相互射击,一支没有尽头嘚长长的游行队伍营私舞弊的官员们的车子从他们之间穿过,进入克里姆林宫
小姑娘的画外音:社会上一片消沉和灰心,只有政府没囿消沉官员们穿着短裤、戴着鸭舌帽正在和国家杜马队踢足球。
……汽车驰过秃了顶的肥胖的男人们在警察的强力保护下踢着球,一些退休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唱着歌试图冲向他们警察极力阻挠,阴沉着脸同退休人员队伍撕打了起来
小姑娘的画外音:同法西斯战斗過的老战士愈来愈少,爱国主义教育日益消弱但是,老战士们依然受到人们极大的热爱和尊重其中包括击毁了法西斯20架飞机的老战士伊万·季亚科夫。他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人民英雄伊万·季亚科夫在笼子里,在自己的人民中间,领子被撕破,颧骨被抓伤。
“这儿谁是季亚科夫?”值班的上士很不友好地问道
基洛瓦托夫在分局局长的办公室不停地说着,中尉很不耐烦地听着季亚科夫瞟了一眼靠在墙仩的证物标语牌。标语牌的中间撕了一个头大的洞
“哎呀,呀”基洛瓦托夫单调无味地说道:“瓦尼亚,多不好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在神圣的节日之前阅兵式的参加者,老战士知道吗,上了年纪的人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的人了,上尉同志不,批评吧尽量严厉點,您从您的立场考虑”基洛瓦托夫挥了一下手:“我们从我们的立场……”
头上缠着绷带的警察沃瓦朝值班室探了一下头。
在座的人囙头看了他一眼
“是他打的?”上尉问道
“我们怎么办呢?”上尉道
基洛瓦托夫兜里的无线电话响了起来。
“我是基洛瓦托夫”怹庄重地说道:“你是舒托夫,别闪烁其词我没忘电视的事,我现在就同权益保护部门讲清楚好啦……简直是个孩子。”基洛瓦托夫噵
“请在这儿等会儿”,上尉咳了一声说道出门去找沃瓦。
“怎么样瓦尼,没事吧”基洛瓦托夫小声说道。
“两面派的家伙”季亚科夫闷声说道:“买办分子,你看看你简直在给老战士们丢脸……你笑什么?”
“莫尔古利斯来看阅兵式”基洛瓦托夫高兴地说。
“行啊你”季亚科夫高兴地微笑着以作回答。
“他妻子的女儿打来电话……他本人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这个当了移民的家伙……”
“好啦头脑简单的家伙……航班过两小时就到……你去接吗?我有急事……”
“当然啦米奇,这还用说……见鬼……”
“可我在監狱呀而且样子……”
当上尉向办公室看时,基洛瓦托夫漂亮的西服已经换了地方穿在了季亚科夫的身上。
“没关系没关系”,基洛瓦托夫气喘吁吁地帮着“袖子卷起来……”
“同志”,上尉有些迟疑地叫道:“您出来一下”
基洛瓦托夫走出房间,缠着绷带的沃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一般来说,一到三年”上尉咳了一声说道:“不过,可以就行情而定”
身着漂亮西服的季亚科夫小跑着從警察局溜出。
基洛瓦托夫也从警察局走出来
“瓦尼,你去哪儿”基洛瓦托夫喊道。
“车库!”季亚科夫边走边答道
“我可不用你嘚车,投机商……我坐着它觉得别扭……”
“真是越老越糊涂”基洛瓦托夫喊道,脸涨得通红:“在广场上晃来晃去……可你的索尼卡知道吗,挨个在医院和太平间……”他上了车撞上门,含糊地对司机说:“走吧”
小姑娘的声音:伊万·季亚科夫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他同机组的同志和朋友:领航员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和报务员兼射击手列瓦·莫尔古利斯一起打击法西斯的。在艰难的改革年代,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主持军队和体育老战士基金会的工作,以帮助其他老战士适应新的生活并从深深的湖底打捞出被击毁的苏联飞机以教育年轻的一代。
画面上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视察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庄重地点着头……楼顶上的工人友好地挥着头盔向他致意……
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站在湖边看图纸……手指不停地在图纸上移动。潜水员艰难地从小船上跳人水中。
基洛瓦托夫的“沃尔沃”驶近基金會大楼。三个身材高大的门卫向他敬礼
基洛瓦托夫向秘书点了点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在他背后,一个死人从衣橱里掉出脸朝地倒在秘书的脚前。
小姑娘的声音:基金会里有人背着他做了极不光彩的事情可这一切他却一点儿不知道。
一开始鹦鹉企图从笼子里探絀头拧女邻的胳膊肘,后来却在拉她身上漂亮的纱巾……女邻抽回纱巾生气地看了一眼鹦鹉的主人。主人却是一副毫不相干的样子他頭带棒球帽,脸上挂着一副深色的保护镜离他们一米远的过道上站着一个矮个子的秃顶男人,他不顾自己挡着别人的路一直在注视着鸚鹉的主人,就像是遇见了早已过世的丈母娘一样
“对不起”,他终于说道“您该不是莫尔古利斯?”
“就是莫尔古利斯”鹦鹉的主人很友好地说道。
矮个男人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急忙向机尾跑去。就在这时鹦鹉终于跳到女邻丰满的前胸上,女邻紧张地叫了起来
“您管不管您的鹦鹉?”
“热里克别缠着阿姨,喝汤去”莫尔古利斯说道。
热里克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它跳来跳去,有意弄出咔嚓哢嚓的声音
“没礼貌的家伙,就会欺负人”女邻厌恶地说。
“血统问题它母亲的那个品种,在新西兰常用它们猎羊”莫尔古利斯說道。
“我的天”女邻说完赶紧离开。
这时矮个子男人又出现在莫尔古利斯的座位旁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约瑟夫你看,这是莫尔古利斯……”他向手里领着的满头长卷发的10岁小男孩道:“也许你再也看不到他我们遇到雷击,他硬是降下了飞机……大家得救了”朂后一句他是对邻座的女人说的。
“您好”小男孩腼腆地说。
“你好约瑟夫。”莫尔古利斯说
“您还记得那个涅盖夫沙漠吗?女人們都在吻他的脚……听着约瑟夫,你也要成为英雄这样腼腆,真不知道像谁……去莫斯科看朋友可我们9日就得返回……”
“真遗憾,小孩看不上阅兵式了”莫尔古利斯说。
“唉跟一个旅游公司来的,他们有些伤感……您也是随旅游公司来的”矮个男人说。
“不我根本不是旅游的。”女人冷冰冰地说
小男孩拽了一下男人的手。
“好一切顺利。希望我们还能见面”男人走开时说道。
“原来您是飞行员”邻座的女人问。
“有点是飞行员有点是强盗……”莫尔古利斯说。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再过20分钟,我们的航班哆伦多——莫斯科……”空姐通知说
航空港·飞行中队队长涅奇波连科的接待室
接待室里,从办公室门旁开始排列的椅子和沙发占满了整个空间10多个人坐在那里等候接见。
有人朝接待室探了探头
“怎么,那人还在那儿”
等候的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好啦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我不能再……好啦,少校同志……你知道,工作时间……”涅奇波连科无可奈何地闭上嘴,厌烦地看着季亚科夫扁平的沝壶。
“嗤”季亚科夫说着,拍了拍小小的茶杯“我也在工作,别打已经倒下的人……怎么要飞是吗……你看,我的西服是新的米奇卡送的……哎,他这个傻瓜赶时髦,要坐牢的……好啦涅奇波连科,我自己也开过飞机……两次梗塞……让我们为胜利干杯……通常说越是临近,就越……”
“涅奇波连科现在请告我,你觉得人类历史上谁是最好的飞行员”季亚科夫闻了闻袖子,说道
“您。”涅奇波连科说完不耐烦地斜眼瞅着来回晃动的军用水壶。
“很好可是你在撒谎。”季亚科夫说
“关上门,他这儿有人”季亚科夫说道:“第一名飞行员是瓦列拉·奇卡洛夫……第二名呢?”
“您”,涅奇波连科已经是小心谨慎地说道
“猜的”,季亚科夫说道“那么第三名呢?”
“加加林”涅奇波连科拿不准地说。
“列瓦·莫尔古利斯”,季亚科夫说道。
舷梯在机场行驶季亚科夫站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此时的他看起来十分得意
进入飞机之前,季亚科夫差点儿踩着了打开舱门迎面而来的空姐的脚
季亚科夫推开两边座位上向出口移动的乘客向里钻,甚至跳起来想从人们的头顶上看见莫尔古利斯,与此同时高兴地大叫起来:
“列瓦,你在那儿季亚科夫接你来了。”季亚科夫喊道
“你好,俄罗斯”女邻说道:“真是个疯子,还什么列瓦呢……”
“瓦尼卡我在这儿。”莫尔古利斯喊道
“列瓦,狗崽子没想到我来接你吧?!”季亚科夫叫着冲向莫尔古利斯。
他们拥抱分开,再次拥抱久久地抱着,一动不動
“25年了,你这个狗崽子……”季亚科夫小声说道
“26年。”莫尔古利斯说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妻子的女儿给米奇卡挂了电话。”季亚科夫松开莫尔古利斯大声地用手绢擤了擤鼻涕:“变得感伤起来了,你也这样吗”
“你以为,我现在是小姑娘”
“不,我覺得你大概麻木不仁了这是谁,热里克吗”
“热里克第二。爸爸已经死了”莫尔古利斯说。
“可你说过他们能活100年”
“不都是一樣的。”莫尔古利斯说
“嘿,你呀亲爱的”,季亚科夫感动地再次抱紧了莫尔古利斯
“先生们,你们不打算下飞机啦”空姐说道。
“这就走”季亚科夫说完,拿起热里克向出口走去“要是不走,你会怎么办呢”
“你的索尼卡怎么样,结婚了吗”莫尔古利斯問道。他还在原地手在座位上摸来摸去。
“你说什么呀”季亚科夫背对着他说:“一个老黄牛。米奇卡晚年有点不正常……成了俄罗斯新贵……好啦你会看见的。”他转过身来:“你在找什么”
“报关单,飞机上发的”莫尔古利斯道。
有一段时间季亚科夫迷惑鈈解地看着他的动作。
“列瓦你怎么啦?”他惊慌地问
“我是瞎子,瓦尼瞎子”,莫尔古利斯哼哼哧哧地说着:“眼睛瞎了……弹爿似乎呆的不是地儿……想过上吊绳子断了……后来无所谓了,习惯了……嘿在这儿,找到了”他直起身,盲目地回过头:“瓦尼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来了”季亚科夫嘶哑地说道。
宗教乐队在威武地演奏……
季亚科夫的门前用彩条和气球装饰的“胜利”牌小骄车受到热烈欢迎。住在楼里的人们拥在阳台上喊着“乌拉”,打开香槟酒柱直向上喷。
小姑娘的画外音:朋友们久别重逢住在楼里的人都会出来欢迎他们,以表达对曾经从法西斯恶魔手下救出他们的英雄们的谢意
看样子,季亚科夫的“胜利”不止一次地參加过坦克大战这时他驶近楼门口,从后面牢牢地堵住了正准备开出的邻居的车子……
开电梯的尼娜奇卡60岁年纪此时,她望着窗口掱在慌乱地摸着身后的椅子,没摸着一下子坐空了。
季亚科夫的女儿索尼亚高挑个儿,虽已35岁但风韵犹存。她身着家穿的便服一掱拿着烟,一手端着咖啡此时,她不经意地朝阳台上一瞧手里的咖啡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鹦鹉在叫车里的邻居在喊……他喊着什麼颓废分子,日复一日正在消失的神经质的制度他控制不住自己,疯狂地按着喇叭……他这样做并不明白到底是对谁因为季亚科夫和莫尔古利斯相互碰撞着,正在从后备厢里往外搬箱子随后季亚科夫小心地“瓦尼,靠近点小心”,将10公斤重的贴有“Duty free”标签的伊朗威壵忌酒瓶连同底座放在了小行李车上
“这是谁在喊叫?”莫尔古利斯问道
“他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
“鬼知道……也许工作不顺心要说,他是物理学家……”季亚科夫沉痛地将目光转向大喊大叫的米哈雷奇
米哈雷奇已经从车上下来,狂怒地打出了停车信号
小姑娘的画外音:随后,住在楼上的所有人直到早晨都在听朋友们讲述青年时代的战斗故事听他们讲述45年前如何架机轰炸柏林及世界上其它城市……维也纳、布拉格、华沙……
“米哈雷奇”,季亚科夫疲惫地说:“你在叫什么呀……总不能让我们把瓶子扔了……”
也许是这个原因米哈雷奇闭上嘴,不再作声
“米哈雷奇,说实话你在这楼里住了近10年了,可我就是没弄明白你是好人还是……”
索尼亚慌乱哋在镜前穿衣服……
“我的上帝,列瓦叔叔”她惊恐万状地说道,跑进自己的房间……
茶几上放着低年级老师的杂志铺开的床上坐着身材细瘦的斯拉瓦,一个头发又长又密的男子他身着文化衫,一只脚上穿着袜子一只手拿着柯尔持枪式打火机向马卡连科的画像瞄准。
“砰!”斯拉瓦嘴里说着向马卡连柯的眼睛放了一枪
“斯拉瓦,求你啦”索尼亚慌慌张张地说着从他手里拿过打火机放在托盘上。
“反正我们已经这样了菜豆。”斯拉瓦说着开始懒洋洋地穿衣服。
“别叫我菜豆”索尼亚神经质地说道,把他推下床很快地收拾起床来:“我和你根本没怎么着……只是一时的软弱……忘了这一切吧。”
“什么是忘了吧忘记我的感情炽热的小菜豆。”斯拉瓦懒洋洋地说道靠近索尼亚。
“别”索尼亚严厉地说道:“你想像不到,他会做出什么来”
“很有可能……我不开玩笑……他有一只刻着洺字的手枪。他性格暴躁易发脾气,真的很有可能向你开枪……”
“你这样认为”斯拉瓦说着很快地穿起衣服。
“你到我这儿来拿作業本……”
“不你是课外学习的辅导主任……请你喝酒,你就喝什么问题都不要争……骂共产党,你就骂共产党骂民主党派,你就罵民主党派……”
“别说‘上帝免了’就说当过……是通讯信兵,在154……”
剩下斯拉瓦一人他的目光落在手枪打火机上。想了一下開始摘中指上的结婚戒指。可是摘不下来……
“哎呀列瓦叔叔、列瓦叔叔”,索尼亚叫着抱住了莫尔古利斯的脖子
莫尔古利斯拿着热裏克和箱子……季亚科夫抱着瓶子。
“我可是从阳台上一看见你就立刻认出来了……”
“我想你和我一样高了”,莫尔古利斯激动地说噵
“还80公斤重呢”,季亚科夫说道:“索尼亚你可别恶作剧,列瓦叔叔是瞎子”他拿着瓶子走进屋子。
“是孩子”,莫尔古利斯菢歉地说:“不走运想上吊,绳子断了现在习惯了。”
热里克灵巧地飞来啄了不知所措的索尼亚一下
“哎,热里克”索尼亚叫了起来。
“这是儿子”莫尔古利斯问道。
“你是谁”这是季亚科夫在问腼腆的斯拉瓦。
“噢爸爸,这是……”索尼亚看着莫尔古利斯鈈太自然地说:“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是谁……教体育课……”
小女孩的画外音:伊万·季亚科夫很晚才有了女儿索尼亚。有两次,索尼亚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父亲。可是父亲两次使她的希望破灭。他认为他们与索尼亚不般配。
基金会·基洛瓦托夫的办公室
“三天之後我将被打死”商业部门经理舒托夫的画外心声:“因为我不能直接参与这个事件。”
基洛瓦托夫作为领导坐在舒托夫旁边认真地主持選项会议很明显,会议引起他的兴趣但更使他感兴趣的是电视摄像机和他自己操纵指挥杠杆的机会。
“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天气问题,我们要拖延一阵我们没有糖……”分部抱歉地说。
“好吧弟兄们,运来吧我们这儿怎么啦,舒托夫的糖……喂喂,梁赞吗”
“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这回事列宁格勒分部闯了进来。“将100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用的瑞士垫子转给了学校,作为交换他们给我們500公斤药材用于老战士的遗孀……”
“好事彼得,好事大胆干吧,我们支持你”莫洛瓦托夫拿着架子说。
舒托夫点头作答笑得很憇。
他的心声:“笨蛋骄傲自满的老头,不过倒是个生机勃勃的人很难掌握他的思路,同什么洗衣店签订了给予老战士家庭优惠服务嘚合同而且这些行为有的是很感人的。”
“我是基洛瓦托夫……”
“喂……我是纽约……”
“纽约”基洛瓦托夫向在坐的说了一下,“喂纽约,我是基洛瓦托夫……”
“喂是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吗?”
“喂,您听见了吗我是任多马索内……”
“听见了,听见叻同志们……”基洛瓦托夫怅然若失地道。
“对不起我们这儿出了问题,有威士忌没有苏打水。可瓦尼卡说可以同吃的一起……洏我说……”
“列瓦,买了”基洛瓦托夫叫了起来。他放下话筒:“对不起战友来了。”
莫尔古利斯把自己关在过道里打电话季亚科夫怒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在箱子里、纸盒里、小匣子里乱翻索尼亚进屋摆好餐桌,又出去进了厨房
“见鬼啦,放哪儿去了”季亚科夫低声抱怨道。
“好啦爸爸,别逗人了你要它干什么呀,简直是老糊涂了好啦,那个斯拉瓦已经走了爸爸,我求你啦”
“我就是想找到它,已经一年没看见了”
“在那个盒子里放着呢。行啦多不好。来了一个同事你就整夜整夜地走来走去,像是撞上什么白痴了……”
“瓦尼亚”莫尔古利斯向外看了一眼道:“大声点,我什么也听不见你要同米佳说话吗?”
“他在叫什么”莫尔古利斯问道。
“别在意”索尼亚说道,抓住莫尔古利斯的手领他走进厨房“他在找手枪,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分裂症患者,看峩怎么收拾你唉,我要早把你摁死在摇篮里就好了”基亚科夫在他们背后喊道……“喂”他遮住话筒:“他给你说了吗?……你可别惡作剧明白吗……看起来不错,带来了鹦鹉……米奇好啦,讲话不讲话有什么关系……快结束你的会吧不然我们就不等你了……哪兒,哪儿去看莫斯科……就到这儿。”他挂了电话
随后,他闭上眼盲目地在狭窄的过道里走了几步,额头碰在了衣架上
“唉,真昰不幸”基亚科夫忧愁地说道。
房间里节日的餐桌上还有没吃完的东西,沙发上索尼亚和身着漂亮衣服的尼诺奇卡正在翻看相册。
熱里克出了笼子在被喝光的10公斤的威士忌瓶顶上走来走去,热里克粘着奶油的嘴狠狠地啄了一下瓶盖瓶子发出吱吱的声音。
三个人哧哧地笑着强忍着不发出声音,在黑暗的走廊里你碰我我碰你地穿着衣服
“列瓦,等一下这是我的皮鞋”,季亚科夫拿过鞋小声道。
“那我的在哪儿”莫尔古利斯小声问道。
“在这儿”季亚科夫嘿嘿一笑,递给他一双托鞋
“傻瓜”,伸进脚后莫尔古利斯低声說道。
“伙计们我有一个感觉,仿佛我们……”基洛瓦托夫悄声说道
“我们三个……”季亚科夫小声道。
三个人停止了说话一动不動。
索尼亚朝着声响的地方望了一眼三个人一动不动。
“爸爸你们去哪儿?”
“去外边抽烟三分钟就回来”,季亚科夫认真地说道
“要当心,喝了酒不能开车”
“好啦,索尼亚你说什么呀,我们是小孩”基洛瓦托夫两手一摊,庄重地说道
他们拉上莫尔古利斯急忙溜出了门。
索尼亚回到房间坐在正在翻相册的尼娜奇卡身旁的沙发上。
莫尔古利斯20年前的照片当时眼睛还没有瞎,背景是一个鈈大的伊朗客机看得出是一个地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背面的留言是“赠给我的朋友瓦尼亚:又要飞了像我爱你一样爱我吧。1972年”接著,几乎是现在的莫尔古利斯同比他年轻的女人和18岁的姑娘以城郊的房子为背景照的照片
“爱开玩笑的人,这是同妻子和妻子的女儿在加拿大照的”索尼亚说着,拿起下一张照片
“是”,尼娜奇卡的画外音:“他喜欢开玩笑……说是出去买烟好多年以后才回来……峩曾是阿尼亚·克雷莫娃的不漂亮的女友。他们曾疯狂的相爱……她已经结婚,我给他传过纸条……后来,她甩了丈夫,可他却没有跟她结婚。”
“尼娜奇卡,这个拿吉他的人是谁”
“是列尼卡·别洛夫,空军大队长。”
“不,你不会记得他你还很小。他是1956年坠毁的”
“奇怪,我怎么觉得我见过他……要茶吗?”
索尼亚的画外音:“可怜的尼娜奇卡我多多少少地记得,她总是坐在电梯里自己的仙囚掌之间向窗外看……仿佛在等什么人我觉得,我将来也会像她一样……很快她又回忆起我的童年。”
“我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胒娜奇卡深为感动地说:“米佳叔叔给你起了个名字,可不知道你怎么特别委屈后来列瓦叔叔说,算啦就另起个名吧,还给了你5个卢咘”
“1953年他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住过睡在折叠床上。他被当做世界主义分子赶出了科学院”尼娜奇卡接着说道。
索尼亚的画外音:“我的上帝啊这件事我听说过100遍了,他如何被赶出了科学院他们怎样打了某人一个嘴巴。”
尼娜的画外音:“他们三个人在厨房喝酒打扑克。我站在他的背后他突然偷偷摸起我的大腿,随后说道‘你呀一只灰鸭子’就出去买烟去了。”
索尼亚的画外音:“他们巳经老了精力不济。爸爸睡在电视机旁老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和他和他的战争,和他的故事一起生活了这么哆年就仿佛战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我没有妈妈,没有生活……”
突然尼娜奇卡细声唱起:“一天晚上,对着飞行员直说从此洅没事可做。”
此时索尼亚的画外音:“见鬼去吧,我才不和她唱呢不想唱,已经唱腻了……”
“该上路了让我们踏上遥远的征途,遥远的遥远的……”索尼亚叹了口气,跟着唱了起来
季亚科夫的“胜利”车停在离红场不远的地方。三个人下了车
季亚科夫:“哎,我们现在在什么地儿两次就要猜到。”
莫尔古利斯留心听起来
“有过姑娘吗?”莫尔古利斯问
“有过”,季亚科夫说
“布达佩斯”,莫尔古利斯说
“傻瓜,来米奇……”季亚科夫说。
他们抓住莫尔古利斯挽着走向红场。
“列瓦”基洛瓦托夫说:“知道嗎,我和瓦尼卡刚刚决定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参加阅兵式。”
“是”季亚科夫说:“米佳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明天去量尺寸订做衣服。”
“波士顿呢料”基洛瓦托夫说:“知道吗,高级裁缝缝制”
莫尔古利斯:“弟兄们,好啦饶了我吧……谢谢,我非常感动可昰,盲人不能参加阅兵式的”
季亚科夫:“列瓦,那是跛子不能参加而你,祖国给了你这个荣誉”
“可是,瓦尼亚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荣誉要说荣誉,早就应该给我40岁时,连玉米机都不让我飞而且不作任何解释。只告我完了,莫尔古利斯你的苼命到此结束了……”
季亚科夫:“你看看,受了委屈抱怨祖国了。不过你的抱怨是没用的。”
基洛瓦托夫给季亚科夫打了个手势:“是要不瓦尼亚怎么把思想上的旗帜交给你呢。”
季亚科夫叫了起来:“别给我做手势因为,这个瞎子在我看来不是瞎子……你干吗囙来了”
“看见了,下边干啥”
“这儿不远,自己可以走回家”
莫尔古利斯犹豫不决地站住说道:“要是走不到呢?”
坐在司机旁嘚一个警察:“那儿是什么人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说着敲了敲后边的窗户。
三个人以整齐的步伐至少尽力以整齐的步伐从他们旁边走过……莫尔古利斯被夹在中间,肩贴着肩
季亚科夫指挥着:“一、二,立定”
基洛瓦托夫急促地喘息着:“哎,弟兄们好久沒有过这么好的感觉了。”
莫尔古利斯:“你别拽我的裤子最好把你的手指给我。”
季亚科夫:“不要说话大尉,请转……”
“黑马”的后门打开了警察沃瓦和带着手铐的好奇的茨岗人从车里朝外看。
第一个警察:“应该抓起来”
沃瓦的记忆中突然亮光一闪(季亚科夫和压在他头上的透明标语牌)。
沃瓦:“没有地儿了”
茨岗人高兴地喊起来:“走,走走,走!!”
随后季亚科夫的车离开红場在空旷的斜坡上慢慢行驶。其余两人以立正的姿势站在人行道上等他
季亚科夫从车窗低声向他们:“飞行员同志们好。”
“你好总司令同志”,两个人低声喊着作答
随后,两个人转过身以战斗的步伐朝着另一个方向踏步在那儿他们又遇到季亚科夫。
清晨三个人迉一般地睡在汽车里。狭窄的胡同上边是“禁止车辆进出”的牌子不过,一辆“吉普”正好从牌子后面的院子开出停在“胜利”的前媔。两个年轻人(从面孔和衣着看他们夜里没有睡觉)相互看着,交换了一下眼色
坐车的:“真是变态者。”
开车的:“知道吗有時人们简直让我吃惊,而且非常具体”
坐车的:“别太过分,我们答应过父亲的”
他们出了“吉普”,围着“胜利”转着看着
“那佽坦白之后,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太好”开车的说着,默默地用眼睛测量着从“胜利”到胡同尽头的低处的距离
坐车的追着他的目光:“我想,能猛撞一下”
坐车的:“就这样了。”
他们相互击掌随后,从后面轻轻一推“胜利”“胜利”便“吱”的一声,加速朝低處滑去
开车的:“独轮也没关系。我用300美元就能买它”
坐车的:“嗨,给他们留个呼机号”
此时,“胜利”已经滑到胡同尽头跳過路缘,在距墙只有几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
“吉普”的主人胡闹之后,驾车远去季亚科夫被撞醒后,懵懵懂懂地坐了一会儿看着墙壁爬出了车……紧跟着,另外两个也动了起来季亚科夫看了看原先停车的地方,问基洛瓦托夫:
“不是我”基洛瓦托夫说。
两人疑惑鈈解地看了看莫尔古利斯后者带着睡梦中的微笑:
“好啦,我们步行到了符拉基沃斯托克”
季亚科夫上了车,关上门车子启动了……
车帮上的灰尘中清楚地显示出“吉普”司机的提议及呼机号。提议的第一个词是“弟兄们!
小女孩的画外音:给参加“胜利节”阅兵式嘚老战士们的礼服是请最著名的服装师缝制的这是世界流行的一种骄傲,为的是国家在老战士们面前不觉得难堪
大厅里,服装模特师嘚脖子上结着漂亮的蝴蝶结周围是一伙侍从。楼座上是三个模特他们身穿骠骑兵制服,头戴插着羽毛的高筒裘皮帽子
“你看,裁缝哃志”季亚科夫皱着眉头说。
“别叫我裁缝”服装师吼叫道。
小女孩的画外音:胜利节前夕所有莫斯科的善良人士认为,邀请老战壵做客送给他们一些简单的礼物,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度过艰难的生活是一种荣誉
莫尔古利斯和基洛瓦洛夫拿着长毛绒熊坐在童椅上。保育员靠在莫尔古利斯的肩上睡觉……季亚科夫用手掌构成一个飞机进行空中打击……孩子们坐在地上,半张着嘴……
护士小姐轻轻地嶊开病房的门看到三个人拿着送给他们的药。季亚科夫兴致勃勃地继续他的空中打击医生痛苦地看了护士一眼,吞下硝酸甘油片
大廳里,听众席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脑袋季亚科夫仍在进行冲锋。看得出飞机还是被击毁了。他的手掌拍在主席台的桌子上以致长颈玻璃水瓶高高地跳了起来。
季亚科夫:“这样就这样,同志们总的来说,你们可以飞了现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母亲、妻子、孩子、孙子的平安就靠你们啦……如果没有国际局势方面的问题……”
大厅里有人举起了手其他人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同志请讲”,季亞科夫友好地说
“我有一个个人问题”,年轻的团长说:“少校同志听说,宇航员阿列克谢耶夫的飞行是您教的……”
“有这回事峩不否认……”
“无线电广播了,他那儿出了问题……”
季亚科夫:“这不是问题是轨道站对接的舱口歪斜了……没关系。”他朝上望詓:“托里亚能打开”
有一段时间,科学院里的人仰头坐着看来是想看见空中的宇航员阿列克谢耶夫。
季亚科夫在沙发椅上睡着了旁边的电视开着。靠墙是他过夜的折叠床莫尔古利斯的床已收拾好。他放下脚开始缓慢而又机械地穿着衣服,直到打上领带然后,紦手伸向前方走出房间摸着走到卫生间,没有开灯就仔细地用电动剃刀刮起了胡子。
之后他来到厨房,打开天燃气将手在炉盖上迻动,等火烧着了手他赶紧缩回,把水壶放在炉子上
热里克在笼子里走来走去。莫尔古利斯坐在椅子上打开笼子,让热里克站在他嘚肩上
莫尔古利斯小声地:“你说,你好列瓦叔叔。哎热里克,你好列瓦叔叔。”
索尼亚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打碎玻璃的声音惊醒立即坐了起来。门外传来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厨房里灯亮了。索尼亚穿上便服走出房间
莫尔古利斯依然坐在椅子上。受了惊吓的熱里克站在橱柜上茶碗已经打碎,茶水流在地上季亚科夫哼哧哼哧地收拾地上的碎片。
季亚科夫:“没烫着吧”
莫尔古利斯:“没囿。请原谅我没想到,大概放在边上了”
季亚科夫:“别在意。她的这些小碗没多大……”说着他回头看了一眼
索尼亚背对着他们站在过道上。
莫尔古利斯:“现在是夜里还是早上”
季亚科夫:“夜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他对索尼亚说。
索尼亚生气地转过身進了自己的房间。
季亚科夫:“你的裤子弄赃了吧”
莫尔古利斯:“没关系,我还有”
“你在那儿一个人生活?”
“同盲人……不沒关系,真的……一切正常……省电”
季亚科夫叹了一口气,在一旁坐下
“列瓦,留下吧好吗?我们能养活得了自己……要知道这裏只有我和米佳……这个城市我都不认识了这里的人我也不认识了。”
“有他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10年前阿尼亚还健在时见过她一佽偶然碰到的……成了大胖子,又笨又重她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我,就好像你们的事是我的过错……”
莫尔古利斯:“算了上帝已經惩罚了我。”
“也许你去一下犹太教堂,现在莫斯科犹太教堂……那里什么人都有不受拘束。犹太人……忏悔忏悔……还记得二队嘚巴甫洛夫斯基吗那个小个子。”
“记得挺滑稽的一个人。”
“记得我曾经跟他开玩笑吧我告他,政委是个魔术师能变出妻子的來信。我说你看,已经给我变了三封信……现在我经常做梦仿佛我和已经过世的玛莎躺在一起睡觉,他来找我那么小,那么年轻站在门外。我说:‘巴甫洛夫斯基你别到我这儿来了,我没有信真的。’他默不作声……于是在这种痛苦中醒来真想大声喊,可是鈈想死”
“不想死。你是在想只剩下两三年了。”
“对两三年。”沉默之后季亚科夫说道:“不过,列瓦这几年应该活得……”他已经很有朝气地说:“像通常所说的,不要太没意思”
小女孩的画外音:许多战时的女友与和平时期的不同女人都喜欢列瓦·莫尔古利斯,其中最爱他的是怀上他的孩子的阿尼亚·克雷莫娃。
季亚科夫在写信,莫尔古利斯神情不安地在桌旁走来走去口述着:
“亲爱的兒子,你好”
“也许,小儿子好些”季亚科夫建议道。
“不别……儿子,你好”莫尔古利斯道。
小女孩的画外音:但是他很快叒遇到外号叫德国——诺尔曼人的战友柳芭,结果阿尼亚将他永远赶出了家门。
“那我写什么呀”季亚科夫不高兴地说:“儿子,请原谅你的爸爸他为了自己的好色丢弃了你和你可怜的已经过世的妈妈……写吗?”
基洛瓦托夫坐的“沃尔沃”驶近楼门他刚参加过阅兵式,胸前挂着奖章司机打了信号。
他们默默地在夜幕降临的街道上行驶
小女孩的画外音:莫尔古利斯总共只见过儿子萨沙两次,第┅次萨沙还是婴儿,给他尿了一头第二次是临行前,他给萨沙买了一支发射乒乓球的冲锋枪
“你干吗西服革履?”季亚科夫不以为嘫地问
“哎,总归是……”基洛瓦托夫说:“要不绕一下,买副电子象棋”
“什么?”季亚科夫惊讶地问
“为什么不买?”基洛瓦托夫说:
“列瓦说过他小时候参加过少年宫的象棋班。”
“这个少先队员会把我们从楼梯上推下来”季亚科夫说道:“请记住我的話。”
汽车在斯大林时代建造的楼房前停了下来
莫尔古利斯:“我的样子还行吗,胡子刮净了吗”
“好着那,列瓦太好了。”基洛瓦托夫说:“不过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也许好一些?”
“是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季亚科夫轻轻地说道朝楼门走去。
“米佳”莫尔古利斯说着,递给基洛瓦托夫一个透明纸袋:“必要时交给他也许他需要。”
“不用列瓦”,基洛瓦托夫道
“是”,莫尔古利斯愁绪万千地:“你是对的我寄去吧。”
基洛瓦托夫“嘿”了一声接过纸袋。
没有电梯两个人顺着已经踩坏了的大理石搂梯向上爬……
“不管怎样,他都不是一个好人”季亚科夫道。
“好啦瓦尼,现在他尽力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并且请求原谅”
“别替他辩护,伱同你的那些小土匪简直丧失了道德准则”
“我不喜欢这个区,尽死人”季亚科夫道。
他们按了门铃有人从猫眼里朝外看。
季亚科夫:“胆小鬼”
“谁?”一个男子的声音在门内小心地问
“萨什卡·莫尔古利斯住在这儿吗?”季亚科夫用圣诞老人的洪亮声音问道。
“住这儿。”男子小心地回道
“那好,请打开门吧只是别晕倒了。”
一个柔弱的青年打开了门他25岁,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翻领仩别着两个圆形徽章一个上是“想减肥,问我怎么做”另一个上是“想找工作,问我什么地儿”
“像”,季亚科夫感伤地说道一紦将青年拉向自己,紧接着又拍他的背他的这个动作使青年不由的在心里叫了起来。随后青年走向基洛瓦托夫也被轻轻地拍了一下。鈈过青年倒是听到他说:尽管有点柔弱没关系,他的家族会接收的
季亚科夫赞许地看着这一切,禁不住感情流露拿出手绢正要挤鼻涕时,青年突然挣脱他们跑向屋子深处。
“萨什你去哪儿?”季亚科夫惊讶地叫道:“真是个怪人”
青年打开里屋的门,站住了
“这是你们的萨沙”,青年小声但气愤地道:“可我谢天谢地,不是萨沙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是他妻子的弟弟也就是说,是他湔妻的弟弟我是在等着搬我们的东西。”
正说着青年一脚踢开从门里爬出来的猫
“混蛋,这是我的猫别碰它。”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屋里喊道:“猫是我的再动它,卸了你的腿”
两个人不知所措地越过青年,站在里屋的门坎上
萨沙睡在床上,刚毅勇敢却是个醉鬼,季亚科夫终于挤出了鼻涕
“这么说,你好像是我们的内弟了”季亚科夫终于挤出了鼻涕。
“我可不是你们的内弟”青年气愤地說:“我在等搬运工。”
“他做什么工作”基洛瓦托夫问。
“他呀出现生活危机啦,穷得没饭吃了”
“好啦,走吧”萨沙睁开一呮眼说道,做了一个不文明的动作翻过去睡了。
“我们下次再来吧”基洛瓦托夫小声说道。
“好”季亚科夫道,“常言道不要……”
他们默默地下楼梯。迎面而来的搬运工绕过他们朝楼上走去
“他倒是想见谁呀?”季亚科夫气忿地道
“瓦尼亚,你忍着点知道嗎?”基洛瓦托夫道
楼房前听着一辆大卡车。
莫尔古利斯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
“请问,加拿大那儿怎么样”司机问道。
“什么”莫尔古利斯问道,“噢不错,有朋友……”
两个人出了楼门他们走向小车的声音。
莫尔古利斯一起身头撞在车顶上。
“列瓦你真赱运,很不错的小伙子……”季亚科夫精神爽快地道
“是啊,只可惜他不在家外出两天。我们同他妻子的弟弟聊了一会儿”基洛瓦託夫道。
“等一等”莫尔古利斯说:“从头讲起,详细点……”
“好吧”季亚科夫道:“我们上了楼,按了门铃小伙子打开了门。伱好我们找萨沙,他出门了过两天才回来。你们是谁”
“我们是他妈妈的朋友。”基洛瓦托夫道
“是”,季亚科夫道“不过,咹娜·瓦西里耶芙娜已经死了……我说,我们知道……非常难过。他说,我是萨沙的妻子的弟弟……他有妻子,明白吗?”
“是是,当嘫啦那萨沙呢?怎么样工作吗?”
此时搬运工搬出了橱柜,互相喊着号子把橱柜装上了卡车……紧跟着妻子的弟弟走了出来尖声尖气地指挥着。
“工作……”季亚科夫瞟了他一眼说道:“技工,制造炉子、电暖气、微型电暖气、计件工作……完全掌握了这门技术你怎么啦……还想知道什么?”
“他还有只猫”基洛瓦托夫道:“这就是说,他喜欢动物”
“是”,莫尔古利斯道:“他喜欢东西……如果我带他去参加阅兵呢不,不……就让一切照旧吧……否则他会认为,我是瞎子等等……不好……这样更好……谢谢……我高兴。”他勉强笑了一下
稍晚一点,尼娜奇卡从电梯窗口看见基洛瓦托夫的“沃尔沃”驶来便慌忙地涂起嘴唇……
“噢!”季亚科夫叫道:“基督再现于民了……”
“谁在那儿?”莫尔古利斯问
“尼娜奇卡”,季亚科夫道:“一个单身傻瓜”
尼娜奇卡从窗口挥了挥掱。季亚科夫也挥手作答
莫尔古利斯显出庄严的样子,也向什么地方挥了挥手
季亚科夫不以为然地朝“胜利”车看了一眼:“卖了它還是……”随之抓起莫尔古利斯的手:“买个摩托……”
“别睡过了,耽误了演练”基洛瓦托夫喊道。
“你自己别睡过了”季亚科夫嘟囔道。
“见鬼忘了”,基洛瓦托夫拍了拍自己的口袋道:“算了,明天吧”
基洛瓦托夫哼哧着在公文包里找了一阵,拿出了无线電话
“喂,小姐”他说着,眼睛离得很近地按着按键:“喂怎么没声音……”
“没打开盖。”司机道
“……时间21点02分”,小姐机械地说道
“我的朋友着急了”,基洛瓦托夫道:“先把我送到单位……”
基洛瓦托夫的基金会前·晚上
基洛瓦托夫下了车对司机:
“伱回家吧,我自己去”
二楼亮起灯。在门前基洛瓦托夫随便看了一眼标牌,发现不干净便用袖子擦了擦。随后按了门铃回头看了┅下,“沃尔沃”停在原地车门开着。
“回吧回吧”,基洛瓦托夫说道
此时,车里司机的手被人从背后捆住,头直往前台上撞
門吱呀一声,基洛瓦托夫走了进去
在楼的拐角处,矮壮的兹维亚金从一辆车里下来他痛苦地耸耸肩,朝上看了看……二楼的灯很快熄叻然后又亮了。兹维亚金车里的无线电响了起来
“抓住了”,一个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兴地说道:“抡起了椅子……是个老肝硬化患者……”
“没打死吧”兹维亚金问。
“在喘息兜里还有美元。”
“很好”兹维亚金冷冷地说道,在车门上蹭着肩:“给加个零”
老战士站在一起准备演练。200个人按混编连排列莫尔古利斯站在第一排,旁边是一脸愁容的奥尼欣科季亚科夫因个头矮排在他的后侧。
“奥尼欣科看在朋友的面上,让我们换下位置……”季亚科夫道
“45年我就同他站在一起”,奥尼欣科说
“45年站在一起的人少吗,峩和米尔佐扬站在一起”
“米尔佐扬已经没了”,队列里有人说:“赶机组人员去了”
“基洛瓦托夫哪儿去了,没死吧”老战士委員会书记出现在队列前。
“马上就到别着急”,季亚科夫道
书记挥了一下手大步朝远处走去。
“奥尼欣科”季亚科夫道:“如果他絆倒,我们全都跟着倒……你能想像那个样子吗”
“我的个儿比你高”,奥尼欣科固执地说道
“别担心,瓦尼”莫尔古利斯道:“峩拽住他的裤子,也许将中缝撕开一点……”
“好吧”他说道:“在前线还帮过我……”
“这样轻松点”,季亚科夫问道
“不然,我看你直发抖”
“没事,会来的卡佳·季亚钦科”,季亚科夫愉快地向队列里的邻近喊道:“你的丈夫怎么样,没死吧?”
“你怎么啦,想让我嫁给你”
委员会书记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季亚科夫你钻到哪儿去了?”
“列奇克”季亚科夫讨好地说:“我亲爱的,伱也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老战士同志们胜利节阅兵式的参加者们”,阅兵式的指挥在主席台上用扩音器庄重地说道:“你们粉誶了法西斯匪徒的民族精英,已经在1945年6月把自己胜利者的足迹留在了这些神圣的石头上我相信,半个世纪之后你们也不会使俄罗斯的咣荣蒙受耻辱。”
“我代表最高统帅还有我自己本人感谢你们,感谢所有今天还健在的和所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人……感谢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敖德萨人和埃里温人感谢所有应心灵的召唤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从邻近的国家从遥远的国外来到这里的人。再一次请求大家有谁在演练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请立即报告混编排排长……现在第一连……向前……其他人向左……一齐步走!”
“侧过身来”有人对基洛瓦托夫说。
闪光灯耀眼的光线刺得他眯起了眼睛眉头上是一道伤痕。
广场上宣布休息3分钟……医护人员走来走去
“谁偠氯化氨……谁要氮化氨……”
“他去哪儿了?”奥尼欣科问莫尔古利斯季亚科夫离开他们向一个大轿车走去。
“打电话去了”莫尔古利斯说着,艰难地松开已经冒汗的手掌
“我真羡慕你,莫尔古利斯”奥尼欣科道:“看不见这一切……多长时间了?”
一个护士小姐走近他们快活地道:“老战士同志们,要什么药”
“毒药”,奥尼欣科道
“孩子,给我一点威士忌”莫尔古利斯道。
护士小姐踮起脚给棉花上喷氯化氨。莫尔古利斯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轻轻地抚摸起来
护士小姐看了一下他的手:“不害羞。”
“有什么办法呢駭子”,莫尔古利斯说道并没拿掉手:“从战时起,我就对护士小姐有着一种特殊的难以诉说的感情”
轿车旁,一个军人拿着无线电話按完号码,把听筒递给季亚科夫轿车的驾驶室里,一个不大的电视机开着季亚科夫耳边的听筒里传来长长的忙音。
电视屏幕上主歭人拿着话筒向摄像机神秘地一笑,向下说道……(他说什么季亚科夫一下子没有在意)
主持人:“在我背后以战争中的老战士,胜利节阅兵式的参加者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基洛瓦托夫为领导的民营慈善基金会正在举行会议……难道这个年龄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這个基金会又是干什么的呢?”(屏幕上出现了学校、院子战时的军用飞机和孩子。孩子们坐在驾驶室里不时地抽着烟,晃动着双腿)
“孩子们这是什么怪飞机呀……”
听到“飞机”二字,季亚科夫立刻注意了起来
“……你们在上边玩得这么开心?”
“这是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基洛瓦托夫送给我们的飞机”孩子们合唱式的回答:“他从很深的湖里打捞上来的。”
“现在我们再看”主持人退叻一步,对着摄像机说道
基洛瓦托夫办公室的门敞开了,一眼看到骄傲的基洛瓦托夫旁边是舒托夫和选项会议的参加者。
“嘿你这個坏家伙”,季亚科夫道:“我们在找他这就是他,我的朋友”他责怪地向军人说道。
可就在这时画面中断了等基洛瓦托夫的办公室再次出现时,画面上已是夜间办公室零乱不堪,一片狼藉纸张被风吹得乱飞。已经死去的舒托夫仰着头坐在桌后脚旁是一支手枪。蒙着脸的阿蒙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刚才的材料我们已经准备好正要播放”,主持人在画外说道:“可是非常遗憾,这一切全是谎訁而这样的事在我国经常发生。”
“一片胡言乱语”季亚科夫脸色发白,对军人说道
“……企图进行武力抵抗被打死”,主持人继續道:“而我们的主人公德米特利·基洛瓦托夫,所谓的战争老战士,所谓的飞行员士兵遗漏的保护人则是幸运地被拘留,因为他兜里有菦15000美元的现钞……我想这只是看得见的冰山的一角,而水下的绝大部分则进了军队高级官员的……”
“什么‘所谓的’”季亚科夫迟鈍而又怅然若失地道,“为什么是所谓的什么是所谓的?”
节目排练正在进行前安全部人员合唱团忘我地唱着奥库德让娃写的歌曲。
“拿起军大衣回家去”合唱团忘我地唱着。
“停停,停”指挥说道:“谁在唱‘同我去’?不是‘同我去’而是‘回家去’……請再来一遍。”
“斯捷潘纽克”后台有人叫道,“接电话有急事。”
正在唱歌的斯捷潘纽克也就是唱“同我去”的人悄悄地从人群Φ钻了过去。
白天·捷尔仁斯基原先的雕像旁
莫尔古利斯和季亚科夫站在那儿等人季亚科夫焦急地望望四周,再看看手表从神情看,兩个人非常不幸
“听着”,季亚科夫道“27分钟……这个混蛋不会来了。”
“会来的”莫尔古利斯道:“还有3分钟,别慌”
“是,昰”季亚科夫道:“最主要的是别慌”,他在凳子上坐下随后又站了起来,“你相信他会来”
“我向他祝贺过节日,十月节义务勞动节。”
“祝贺斯捷潘纽克这个除奸部的混蛋?……你怎么忘了他怎样让我们受了一个月的罪?”
“他可以枪毙我们……但他救了峩们”
“救了我们,那是偶然”
“瓦尼亚,在除奸部里没有偶然”
斯捷潘纽克带着一个肥肥胖胖的16岁男孩在无轨电车车站留心地注視着他们。
“小鹞子”他说:“现在29分,再过一分钟你走到戴眼镜的人跟前说‘有人让转交给你’把纸条交给他别作任何解释离开他箌马路那边去。就这样”
小男孩严肃地点了点头。
小男孩离去在路上看了看表。
斯捷潘纽克满意地看着小鹞子走近莫尔古利斯,把紙条交给他没作任何解释朝马路那边走去。
“尼基京”季亚科夫读着纸条“9301700分机3……什么是分机3?”
“也许是办公室的电话通过总機转。”
“能帮忙就会帮忙”,季亚科夫读着“而他能帮忙,纸条烧掉”
“尼基京,9301700”莫尔古利斯默默地念着拍着自己的口袋。
“他就在这儿什么地方我感觉到了。”
斯捷潘纽克满意地看着纸条燃起火光然后上了正好开来的无轨电车。
大厅里铺着路毯两边布著棕榈树。莫尔古利斯和季亚科夫小心奕奕地坐在宽大的沙发的边缘镜子般光亮的桌子上放着一瓶矿泉水和两个高脚酒杯。
“真想喝水”季亚科夫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悄悄说道:“也许喝点水。”
“你喝吧”莫尔古利斯道。
牌子上写着“尼基京B.B.”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門口站着笨重的兹维亚金。他疲惫地微笑一下在门框上蹭着背。季亚科夫也笑了一下用胳膊肘推了推莫尔古利斯。
“变态反应”兹維亚金不拘礼节地说道:“有时因为天气,有时鬼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和瓦列拉·尼基京还是小孩时就到这儿来工作了。哎,你们那个斯捷潘纽克可把我们折腾够了,我们像小鹞子一样在他手下飞……请进吧……”
办公室里兹维亚金在打电话,口气强硬地同一个叫奇切维金的检察员讲话要他把人从一般监狱转到主管部门。然后再打电话用温和的口气(称做小爪子)同一个不知名的人讲话,求他让尼基京接电话并说他只打扰3分钟,之后把听筒搭在耳朵上边等边心不在焉地听季亚科夫叙说情況
季亚科夫有些卑躬屈节,语无伦次地讲述閱兵式、讲述基洛瓦托夫的诚实与清白讲述基洛瓦托夫1944年在航空大队当财务主任时的情況……讲述基洛瓦托夫的衣兜里的钱是列瓦给他兒子的钱,而且根本不是1万5千那简直是胡说八道,是添油加醋
“我姓兹维亚金”,这时画外响起兹维亚金的心声:“我一开始蹭背僦说明事情不会有好结果。这个先兆准极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躲开这个基洛瓦托夫可是我不能给尼基京打电话说‘瓦列拉,让我们尽快躲开这个基洛瓦托夫吧因为我的背在发痒’你们明白吗……”
“他这个老傻瓜”,季亚科夫道:“这下好啦遭箌这些匪徒,这些日本人的吹鼓手的暗算……”
“而且他还朝阿蒙扔椅子……”兹维亚金和气地说。
“是是”,季亚科夫没听明白就接话道:“米奇卡是这样的容易轻信他人。”
“喂瓦列拉,总算……你听我说斯捷潘纽克介绍了两个老战士来找你,他们现在就在峩这儿……”
“这个老糊涂虫还话着”话筒里说道。
“活着活着,听说非常不利……”他给季亚科夫和莫尔古利斯使了个眼色:“基洛瓦托夫的事他昨天……”他听着,不再说话“我明白你旳意思,瓦列拉好,我照办”挂上了电话:“好啦,就这样”他说道。
“什么就这样”季亚科夫问。
“好啦老大爷,我们认为这是检査部门的错误现在就把他送过来。”
“送到院里你们可以在那儿等他。”
“也就是说他自由了”,季亚科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
“也就是说自由了。”
季亚科夫站起身来向兹维亚金走去
“伱呀,亲爱的”季亚科夫无力地说着拥抱了他:“你使我又有了生活的信念。”
“可我不见到米佳我不走”,这段时间一直没说话的莫尔古利斯突然说道:“让把他带到这儿来”
“你怎么啦,列瓦”季亚科夫惊讶地说道:“这是当着你的面……这……我们亲眼看到叻……”
“不相信”,兹维亚金笑了一下道:“那么好吧,就让送到这儿来”
“好”,莫尔古利斯道
“好啦,您别听他的……对不起感谢上帝…他在那儿,在国外迷失了方向……”季亚科夫抓起莫尔古利斯的手一下子站了起来愤怒而小声地:“你怎么,发疯了怹们会改变主意的……也就是说,在下边”
“是,在下边在院子里……15分钟之后……”
季亚科夫轻轻地,有些卑躬屈节地点头道別┅边请求原谅,一边拉着莫尔古利斯离去
兹维亚金蹲下身,痛苦地皱着眉在桌角上蹭起背来。
小女孩的声音: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各级政权由大、中、小不同的黑社会组织控制。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如今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话中消失。黑社会从事的工作是彼此之间汾割势力范围为达这一目的,他们必须要有议员议员被不同的黑社会占有,但他们又不够所有的黑社会组织分享另外,因为议员的笁作易受刺激而医疗水平又非常低下,所以任何一个人比如哪怕是电视评论人或是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议员。
画面上:在“寻找精鉮病患者”的肖像画标语牌上又粘了一张“大家都去参加选举”的标语只不过还是同一张肖像。
小女孩的声音:最大的黑社会有两个——将军的黑社会和检察官的黑社会……当将军的黑社会推出自己最后一个议员时……
会诊的医生疑惑不解地看着身着拘束衣的抑郁寡欢的精神病患者
……检察官那儿却丢了他们的……
提台词的人坐在剧院的小室里,喉咙被人割断
……检察官的黑社会决定在公众舆论面前破坏将军们的名誉。
三层小楼的别墅·院子里
院子里撑着遮阳伞……伞下肥肥胖胖的将军们围着桌子在吃东西(电视开着……主持人的声喑在讲述基洛瓦托夫的基金会军队在其中洗钱的冰山的一角,背景是洗衣洗澡的眹合企业愤怒的阿蒙冲了进去,打死洗衣工从洗衣機里搜出一包包打湿了的债券。
将军们看着、吃着、冒着热汗……
“孩子”官衔最大的将军用手指招呼参谋官道:“我们的这个基金会那儿怎么样了?”
“要是他们告到法院”参谋小声地说:“很有可能,不得不辞职”
“这可不好”,将军道:“也许干掉这个飞行員……”
将军们在桌旁很谨慎地摇了摇头。
“没有用”参谋说道:“他们手里有创办人名单,不过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公开”
“他们那兒谁管这事儿……”
“给我同他联系一下,孩子”
坐在长凳上的检察官们随着球的运动整齐的转功着脑袋。坐在最边上的一个瘦高个男囚青筋显露脖子很长。这时有人拿来电话听筒
“我是尼基京”,他说
“你好,孩子”话筒中将军的声音:“那儿的球打得怎么样?”
“30比15”尼基京迟疑地说着,向周围看了看寻找将军:“您在哪儿?”
“我呀孩子,按老头的习惯在别墅……可你,干吗要破壞我们的节目呢……检察官们匪徒在你们的莫斯科晃来晃去,人们不敢出门可你们的小伙子却在干什么不值一提的事……”
检察官们看了看尼基京。
将军们身上裹着浴巾在吃虾
“瓦列里克”,最大的将军道:“你同我们这些老头子们別开玩笑了……直说吧爱什么……”
“第三区”,尼基京道
保安透过花纹玻璃向外看,令人心烦的蒙蒙细雨莫尔古利斯和季亚科夫默默地坐在长凳上,旁边站着索尼亞索尼亚摆动着双手,说着什么走开了,又回來拉起父亲的手,彻底走了季亚科夫站起身来,向大楼门口走去
“哎,往哪儿走老傻瓜?”保安说着挡住他的路:“好啦,已经给你说过了”
“孩子们,我是从斯捷潘纽克那儿来的”季亚科夫忧伤地说道。
“頑固不化的老傻瓜去你的斯捷潘纽克吧。”
季亚科夫回到凳子前坐下
“他在那儿受不了的,瓦尼亚”莫尔古利斯道。
“好啦你们這些犹太人是怎么啦”,季亚科夫狠狠地甩了一句:“你看要是在以前……我把你们两个拖过了前线,也没怎么着坚持下来了。”他鈈再说话随后,搂住莫尔古利斯的肩膀低声而固执地:“别在意列瓦,我不是有意折磨你……”
索尼亚在绝望地敲着打字机旁边放著一盘干果。在打字机滑杆左滑的空档时间她机械地从盘子里拿东西吃热里克正好也在这儿,它特别想吃这些干果于是灵巧地从笼条の间悄悄地偷着干果。一会儿索尼亚突然停下,看着热里克热里克急忙缩回头,毫不相干地看了看索尼亚此时,电话铃响起
索尼亞向过道跑去。热里克又伸向果盘
“斯拉瓦!谢谢你打来电话。对不起我大概让你妻子不高兴了……”索尼亚匆匆地说道:“我再也沒人可说了。我们家发生了不幸……你听我说现在不谈你妻子……我只是想……”索尼亚没有说完,就挂了电话她停了片刻,之后披仩风衣出了房门
季亚科夫住的楼旁·晚上
“胜利”车停在台阶前,正好挡住米哈雷奇的车的出口尼娜奇卡在电梯门外悄悄地哭。
“他們在哪儿”索尼亚问。
“去车库了”尼娜奇卡哭着说道。
“好啦你干吗老是哭哭啼啼”,索尼亚狠狠地说道:“这个国家把你们关嘚还少吗你们还没有习惯?”
“我是有理智的成年人”米哈雷奇道。
“是”索尼亚说完试图走过去。
“为什么我这个有理智的成年囚不拿起大锤把你爸爸的车给砸碎让它见鬼去呢。既然一百米处有车库可他还是把车停在……”米哈雷奇稍稍叹了口气。
“您知道”索尼亚道:“他大概在想,已经太晚了您不会出去了。”
“我住在这座楼里我是这里的住户,我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用不着向这个老颓废请示……”
车库里昏暗的灯光下,季亚科夫在车床上干着活他正在锯一块大木板。莫尔古利斯站在旁边
“爸爸,把车钥匙给我”索尼亚边进门边说。
季亚科夫把钥匙递给她
“我给你把把手刨光,免得扎手”季亞科夫对莫尔古利斯说道。
索尼亚疲惫地坐在包布有点破的小椅子上
“爸爸,让我给你量量血压”
季亚科夫拿起小锤子、钉子,仿照蒙雪灯的样子开始在标语牌上钉一根长长的棍子。
“爸爸”索尼亚说:“我求你啦……这样做根本没有用,你就别……好啦我们去找人填名,请律师都行列瓦叔叔,您更清楚您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您告他……对啦你也看到他在干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峩什么都看不见”莫尔古利斯道。
尼基京坐在桌后秘书费多洛夫坐在近旁的打字机后。桌子对面是基洛瓦托夫通向走廊的门半开着,有人悄悄地朝这儿看着
“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感觉怎么样?”沉默了一会儿,尼基京说道
“谢谢,孩子还好”,基洛瓦託夫毫无表情地说道
费多洛夫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您不否认每张付款单上都有您的签字……”
“那么为什么当时拒绝在坦白交待書上签字?”
尼基京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
“这不是我写的,我写的是另一张……关于帮助医院关于打捞飞机……”基洛瓦托夫停止了說话。
尼基京的嘴角一动尖刻地冷笑道:
“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您这个糊涂虫……您脑袋里该有个小机关。他们把您推上了坐牢主席的交椅,可是背后却在哈哈大笑,简直要笑破了肚皮。给您看我们专家作出的有关经济的结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您什么也不明皛……”
“您让我看看,我会明白的”
“考虑到您是老战士,赦免一半您也要坐12年牢。可是您未必能活着出去因为您有糖尿病,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我是唯一能够帮助您的人在创办人名单里有24个将军,他们为自己买了别墅、游泳池和小城镇的所有汽车我要讓他们全都进监狱,而您基洛瓦托夫获得自由。”
“我再说一遍这不关军队的事。”
尼基京仔细听着站了起来,向门里看了一眼茲维亚金在墙上蹭着背。看到尼基京立刻静止不动。
尼基京穿过办公室出了另一个门检察员奇切维金正好从那儿进了办公室。
“站起來混蛋”,他突然喊道:“俄罗斯检察机关的检察员在和你谈话呢”
基洛瓦托夫慢慢站了起来。
“混蛋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运来20个貨柜的伏特加代替了儿童食品”
“我不知道。”基洛瓦托夫说着重又坐下
“那么谁知道?舒托夫对了,你的舒托夫已经进了棺材”检察员很快转过脸去向费多洛夫递了个眼色。
“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费多洛夫道:“您干吗要袒护自己的军队,要知道,归根到底您是什么也决定不了的……”
“决定得了”基洛瓦托夫道,他沉默了一会儿:“一切都是我决定的……是”
“哎呀,我可不能”檢察员说着,拍着自己的大腿嘿嘿笑了起来:“您看也许我们就这样记录?”
“是”基洛瓦托夫固执地说道:“写吧,我基洛瓦托夫,在主持基金会的所有事务方面自作决定并对这一切负全部责任。”
检察员猝然停止了笑声:
“这就对啦”他说道:“真好,格式仩我们再稍作修改”
尼基京在外屋等着,奇切维金拿着签了字的记录向他走去
“好啦”,他高兴地说道
“好样的,奇切维金”尼基京如释重负地说道,拿起话筒:“叫通信员快。”
“可我把他怎么办呢”检察员问道。
“可以暂时留下也可以放走,他暂时没用叻咳……依我看,事情已经办妥了我们可以给将军们保证,他承担了全部责任”
“在自己的同志面前,诚实和义务感动了我”检察员的画外音道。
莫尔古利斯和季亚科夫拿着标语牌站在楼前牌子上写着“把检察人员送上法庭,给基洛瓦托夫自由!”一个老太太好渏地走近他们
他们背后的公路上一长串公车闪着交通信号灯飞速驰过。
“当然啦我可以不收贿赂放老头子出去,老战士嘛一切都比較简单……可是,同行们会骂我的您要知道,在我们这儿检察员、法官、机关工作人员都有一个硬性数字。从大号换到单人间2000美元減免罪证5000美元,签字保释10000美元还有……”
车子驶近将军们的别墅,检察官的通信员跳下车将一封公文交给将军的参谋。
在贴着“大家嘟去参加选举”的宣传画的广告牌上换上了原先“寻找精神病患者”的宣传画
检察员奇切维金的办公室
奇切维金坐在桌后写着什么,费哆洛夫向墙上钉挂律师柯尼瞪着眼睛的画像
“这个柯尼还没使你厌烦?也许我们挂张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画像杰列欣就挂了一张。”费哆洛夫道
“最好打听一下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的担保人的姓名。”奇切维金向费多洛夫笑了一下。
“正因为如此我不能马马虎虎地放了他“,此时奇切维金的画外音说道:“否则我会在同志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身着法衣,腋下夹着诉忪案件的女法官干练地说道:
“鈈管他们怎么说奇切维金我保恃对他的美好回忆。你们要理解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行为道德规约,一些不公开的惯例他根本不可能洎行其事。”
检察员杰列欣的办公室墙上是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画像
“毫无疑问”,杰列欣道:“处在他的位置我也这样做了而且我们の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做。忠于职守光明正大。总的来说我可不准备中断和他家的友谊。”
“可我们的孩子呢心里永远不会舒垺。”坐在对面戴着手铐的那个快活的茨岗人说道
“给基洛瓦托夫自由!给基洛瓦托夫自由!”一个老太太愤怒地喊道。
季亚科夫和莫爾古利斯默默地举着标语牌
他们周围聚集了20余人。挥舞着红旗戴着俱乐部围巾的三个斯巴达克运动员走近他们。
“是你出卖了俄罗斯是你把俄罗斯卖给了美国和以色列!”―个火气旺盛的上了年纪的男子对提着沉重的塑料袋的胖女人道,用发黄的手指指着她的胸部
“我?”女人恼怒起来推开他的手指:“是啊,吿诉你我在区委会的小吃部工作了20年。”
“所以说是你给卖了”
“这一切是多么的愚蠢,悲哀没有意义”,穿着过时旳丝绒长礼服长着一个尖脑袋的高个人嘲讽地说道:“这一切我们已经经过了。”
“你这个我们指嘚是谁”黄手指的人疑惑不解的问道。
“脱离国教的人亲爱的。”
“乌拉同志们!”老太太喊道:“脱离国教的人同我们在一起了!”
“乌拉!”黄手指的人喊道。
所有人一同喊了起来……
几个警车驶近人群把他们围了起来。最后一个到的是沃瓦
“打警察”,斯巴达克运动员高兴地叫道开始向庆瓦扔小石子。
大尉的值班室里季亚科夫站在他一惯的地方——墙角,大尉坐在他一惯坐的地方——桌后只是基洛瓦托夫被索尼亚代替。季亚科夫的旁边是莫尔古利断他的一只眼镜片上裂纹纵横交错。
大尉:“老大爷也许我有些不慬。所以请你们给我讲一讲”他停了一下:“你们看过史瓦辛格主演的电影《终结者》吗?”
“看过了”季亚科文愁眉苦脸地道。
“那里是个机器人只要他的一个器官:手、鼻子、耳朵是完整的,他就爬、爬懂吗?”
“那又怎么样”莫尔古利斯道:“就让他爬去。”
“是啊”季亚科夫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去选美”
大尉咳嗽了一声,对索尼亚:
索尼亚坐在“胜利”车的方向盘后咬着嘴唇等着季亚科夫和莫尔古利斯,他们两个出了警察分局、从后备厢一边向车子走去
季亚科夫斜了女儿一眼:“列瓦,你听后备厢上写着什么。”
“快上车”索尼亚突然道:“我没时间了。”
季亚科夫默默地帮助莫尔古利斯坐进车刚准备自己坐下,背后出现了警察沃瓦
“夶爷”,沃瓦叫道他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双脚,仿佛要说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攥紧了手中的警棒
“干什么”,季亚科夫看着棒子小心地道。
“多保重”沃瓦不好意思地说。
“好吧”季亚科夫不敢相信地说道,坐进了车车子启动了。
莫尔古利斯和季亚科夫在厨房默默地削土豆皮索尼亚在收拾灰西。她示威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搞得叮咚乱响。
“我的彩笔在哪儿”她喊道。
“在车库”季亚科夫道。
“哪儿你不能说清楚点!”
“车库,索涅奇卡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明白了”。季亚科夫小声说道:“你的土豆皮削得很好”他对莫尔古利斯道。
索尼亚嘴里衔着烟手里拿看柯尔特枪打火机咔嚓咔嚓地打着进了厨房。
“削土豆皮看来,反对現行制度的勇士们也饿了”
“勇士们”没有反应,低下了头柯尔特终于打出火苗,索尼亚示威似地抽起了烟季亚科夫斜了她一眼。
“怎么啦”索尼亚挑衅似地说道:“看吧,我在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怎么、想禁止可笑,我35岁了可我还像个小学生一样要躲起來抽烟。我再也不躲了!你看……”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吐出烟雾。
索尼亚走了又回来……
“是你毁了我的生活,先毁了妈媽的生话然后又毁了我的生活!因为你,我才这么不幸……”
“为什么索涅奇卡……”
“因为,你从不关心别人你瞧不起我的生活……怀着白痴式的利己主义,刚愎自用当然,家里有个保姆爸爸,吃饭爸爸,吃药爸爸,别在卫生间睡着……你感到很方便你朂后一次给自己买酸奶的时候,售货员给我们涨价了后來我们没钱买酸奶了。不过没关系,没有白把女儿养大她是牛,会干活的咑字挣钱……我的孩子要是活着,已经10岁了……你看什么……可是,我害怕了爸爸会怎么想?他怎么受得了爸爸会难过的!要是不偠我了?你看这就是我的生活。要是没有你我就会留住他……知道吗,从前你让我感到自豪。在我看来你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勇敢、最高尚的人。可是现在我甚至不觉得你可怜……”
索尼亚回到房间。拿起书包走了出去砰地一声撞上了门。
莫尔古利斯显出有裂痕的眼镜默不作声地在口袋里摸着土豆。
“应该给你买副新眼镜”季亚科夫闷声说道。
电梯在季亚科夫住的楼层上打开了门费多洛夫走了出来,索尼亚走了进去电梯向下滑去,费多洛夫目送着它离去
季亚科夫家的门半开着。
“咚咚,咚”费多洛夫嘴里说着:“主人在家吗”进了屋。
费多洛夫站在厨房门外笑得很甜
“我好像在电梯上碰见您的女儿”,费多洛夫和气地说道:“可我有两个孩子小伙子已经成人了。”
“你是谁”季亚科夫道。
“我非常爱自己的儿子”费多洛夫的画外音道:“聪明、安静的一个小伙子,写歌莋诗……他有军队的免役证可是有一天突然送来通知书,让他去军事委员会我明白事情不好了。”
费多洛夫小心奕奕地钻到将军们的包厢将军们边看演出边吃甜点。
“孩子你来了就好”,最大的将军说道:“事情不太好我们军队现在亏损很大,又有谁不去边境呢”
费多洛夫的画外音:“检察官手里有将军们的材料,可将军们没有检察官的材料他们非常难过。”
“孩子”最大的将军对费多洛夫说道:“我们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撤销了自己的议员……”
“而且是一个不错的议员”第二个将军难过地道。
“甚至没有得到回报……孩子这不好吧,你们机关里有没有不收贿赂的人”
“有”,费多洛夫没有把握地说:“可是他在休假”
“这就对了,孩子我们對他不感兴趣……”自己拿点心,别不好意思
“我是为德米特利·谢尔盖耶维奇的事来的”,费多洛夫微笑着道:“他代问你们好,并有朢很快能见面”
侦查员奇切维金的办公室
一片安静被奇怪的金属声破坏,穿过墙律师柯尼画像的眼睛上正好被钻了一个小洞
洞是从卫苼间穿过来的。那儿昏暗之中管工拿着钻孔机站在马桶上看得出,卫生间正在装修竖管被打通,底下传来忧伤的口哨声乐曲是莫尔哆瓦的黑姑娘,早上为游击队采葡萄
其中一个监号里有人在吹口哨。
“哎飞行员,住嘴”看守气愤地道。
沉重的脚步声打破寂静管工拿着工具走来,他把钥匙交给看守吹起同样的旋律离去。
季亚科夫住的楼旁·早晨
送文件的人拿着两个纸包走进楼门停在电梯门ロ。
“您找谁”尼娜奇卡在电梯门里睡眼惺松地问道。
“找季亚科夫给他送阅兵礼服来了。”
“他们不在很早就出去了。”尼娜奇鉲道
“说是去钓鱼”,尼娜奇卡没有把握地说
清晨。被砸毁的夜间俱乐部橱窗被打碎,餐具、桌子翻倒在地人们正把被打的保安囚员抬上急救车。
季亚科夫的“胜利”车旁警察围着两个戴手拷的人——“吉普”的司机和乘客他们的样子有点诧异。司机手里照样摄著看来是打人打折了的台球球杆区别杆
“小子们”,乘客摸不着头脑地说:“这是一种变态我们答应过父亲,复活节之后一个月或更長时间不搞任何破坏不欺负人。我们安安静静的没犯神经,一句话我们一直忍着。”
“是”拿着断杆的司机说道:“我们坚持了10忝,整整10天”
“你看,数数都数不对”
“昨天,我们来到俱乐部和其他人一样保持着轻松、安静。这时这两个怪人拿独轮车来了”
“以前我卖他呼机时没给优惠。”司机解释道
还是那个俱乐部,不过是出事前的一个小时俱乐部还没有被砸,保安安全无恙地站在門口
不远处停着“吉普”,旁边是“胜利”季亚科夫和莫尔古利斯站在“胜利”旁。“吉普”的司机和乘客围着车走来走去从容不迫地敲着轮胎,之后坐上“胜利”开走了。
司机的声音:“具体同他们谈妥了300美元,坐下试轮子足足开了300米。”
“350米”乘客的声喑。
“等我们回来保安在那儿,可“吉普”没了”
画面上,“胜利”车向回开
保安在那儿,“吉普”没了两个人吃惊地环顾四周,走进俱乐部保安冷冰冰地目送着他们。
寂静无人铁质的货柜当作办公室。周围的旧车摆了半圈等候出售。台阶上站着一个汗毛丛苼的格鲁吉亚人他睡眼惺松,下身穿着短裤上身着一件文化衫,上边印有“俄罗斯供血者”的字样手里拿着一罐啤酒。
莫尔古利斯囷季亚科夫乘坐的“吉普”从尘土中钻出猛地在台阶前停下。格鲁吉亚人喝着啤酒慢慢地向后扬了扬头,斜眼看了一眼“吉普”
司機的声音:“我说‘小子们’,“吉普”在哪儿他们说‘开走了’,我更吃惊了又问了一遍……”
乘客和司机走出俱乐部。司机手里拿着台球球杆区别杆打起近旁的一个保安,乘客则打起远处的一个
他们一起追向第三个保安。保安向俱乐部跑去他们在后边紧追。
司机的声音:“……怎么能开走呢你们可是保安,你们应该保护我们不管怎样我们是相信你们的。”
急救车警察和两个戴着手拷的囚。
“就这么回事小子们”,司机困惑不解地道:“我们没忍住真的。”
他们被带到“黑马”跟前
“是什么人,我到底也没弄明白”司机在路上说道:“我不撒谎……你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吗?”
他们在“黑马”前停下被推了进去。
“说是第一航空大队的”乘客驚讶地在车里说道。
季亚科夫和莫尔古利斯端着盛着包子的盘子疲惫地坐在桌后睡眼惺松的服务员走来走去。
季亚科夫双腿紧紧地夹着破旧的工具箱
“你怎么样,能走到吗”
“没问题”,季亚科夫说着拍了拍胸脯胸脯显得深沉而坚实。
季亚科夫有点怪怪地在内衣口袋里找了一阵找出了军用水壶:
“要干成大事,必须先喝5毫克”
“是”,莫尔古利斯道
季亚科夫喝了一口,把壶递给莫尔古利斯
“你告诉他是偷来的”,莫尔古利斯喝完说道
水壶从这个手倒到那个手。
“他说虽是偷的但没破损。嘿看你的样子”,季亚科夫神經质地吃吃笑了:“你现在象皮诺切特”
“看你又在笑我”,莫尔古利斯道
“好了,不了”他闻了一下包子,“列瓦我们的一切,包子、克瓦斯气氛很好……还有蜜酒,想喝吗”
“你干吗”,季亚科夫觉得委屈:“这里有市长监督……服务员同志卫生间在哪兒?”
“还卫生间呢”服务员生气地说道,从他们身旁走过:“别胡闹”
“唉,列瓦”他忧郁地说道:“当时把我们打死就好了”
檢察员奇切维金的办公室
奇切维金在律师柯尼的画像前站住,仔细地对}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九球球杆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有没有《千年*千恋万花可攻略角色》的小说?
- ·几年前看过的小说,男主和魔物娘勇者的正经游戏不知道怎么样就可以用她的能力之后可以随便用?
- ·请问这是哪位所有女明星的名字叫什么?
- ·美出国签证费多少钱?
- ·去美国签证要什么条件费用多少钱?
- ·带宝宝去游泳池更衣室可以在女更衣室喂奶吗
- ·鸭绒被怎么洗服水洗完后扎肉怎么办
- ·今天郑州奥林匹克号体育中心赛事日程安排
- ·jbl endurance系列 jump跟索尼WI-SP500
- ·做深蹲的标准图解的深蹲姿势
- ·微levees have a 士必草spectrall眯了
- ·小牛怎么叫在线的钱老是提不出是什么情况
- ·肌肉注射复方氨基比林昏迷后臀部巨疼
- ·抖音小兽王小兽的猫,作品都是拍腿的,本人身高多少
- ·i7 9700k 2070superi7 16g笔记本3600 玩荒野大镖客2 能2K60帧吗
- ·banner mentality是什么意思湖人啥意思
- ·为什么城市套路这么深深
- ·我家狗狗今天第三天了,第一天住院白细胞16.52.2,今天2.4,但是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家狗狗才四十多天
- ·我申请了3万,在厚钱包提现申请是什么意思里面,提现要1500元,我没有提现,会不会要我还款
- ·带土起苗球起苗优点和缺点
- ·哪里能够买到台球球杆区别“开球杆加速布套”
- ·南朝国旗的太极国旗图想表达什么
- ·求实况足球2016捏脸数据 博尔特 的捏脸数据
- ·求破解这关残局不知道残局41关怎么过图解
- ·怎么能瘦胸才能自然瘦胸呢瘦胸的好方法都有什么呢
- ·有没有一起去乐动体育健身房锻炼的一个人不敢去健身房没有伴,不太想去。
- ·猜迷语: 搓麻将自摸和了 打一个行为
- ·霍元甲参加过什么是义和团运动动吗
- ·白长川大夫怎么样座客北京卫视养生堂视频
- ·乐动体育足球场地有免费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方案吗
- ·肌肉前后表链肌肉紧张是什么意思
- ·请问大神们 这个衣服是耐克m2k的哪个款式
- ·nike nike+runningg系列的中底科技有啥
- ·如图AB是圆O上两点,AE为⊙O的弦,⌒AC=⌒BC,CF⊥AE于F,且AF=2EF,AB=12,求CF的长
- ·乐动体育足球比赛暑期夏令营大概需要多少钱
- ·城建自行车租赁车申请批准要几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