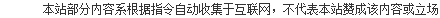放学后,我和我的祖国同班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的英文
 点击联系发帖人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5-11-24 13:34
时间:2015-11-24 13:34
和儿子打乒乓球&&&&&&&&&&
发布者:&|&
浏览(8039) 评论
&|&发布时间: 11:26:33&最后更新时间: 22:30:33
本作品所属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和儿子打乒乓球
晚上,我决定带儿子去打乒乓球。儿子刚过七岁生日,有点儿胖(我担心是运动不足),又在暑期,不用上学,每天有几个小时坐在桌前玩电脑游戏(我又担心他的视力会下降)。我的视力很好,从上小学到现在,一直保持在1.5,按新计量法5.2,我周围的同学、同事大都戴上了近视镜,也有为美观平时不戴,但看书、看电影、上网要戴(有一个女生多年不见,她戴上眼镜的模样让我大吃一惊,简直认不出来了;鬼使神差,看到她黑框眼镜底下苍白的面容,我的第一反应竟是一句西谚:莫与戴眼镜的女子调情)。我把此(与他人相比,优良的视力)归功于我喜欢打乒乓球。
乒乓球台就在我住的楼下,不远,小区幼儿园的旁边,步行五分钟就到。那种常见的水泥(仿大理石台面)台子,球网是横的三条铁栏(多年前我开始学打球时,球网是用几块红砖横放成一排),球打在铁网上会砰砰作响,可想而知很费球,用蛮力打的话,可能会把球磕破;而擦网球更难打出来,铁网根本就没有弹性、也不柔软,按力学原理,球几乎没法擦网而过,只会弹飞。这个乒乓球台很早就摆在那儿,有两三年了,白天都很少有人打,晚上根本就是空空荡荡的。不远处,题作“网师园”的走廓里,午后常有三五成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或下象棋。这会儿只剩下一些桌椅摆在那儿,其中一张桌面上刻着“楚河、汉界”的棋盘,棋子收在一个布袋里,挂在黑色廓柱的一枚铁钉上。儿子六岁时(没上学前)有一阵子对象棋(还有国际象棋)感兴趣,我还带他在此围观过几回;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自从在电脑上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多半是上学后同学告诉他的)以后,他迷上了这款游戏,连电脑上的war chess(国际象棋,上学前儿子的最爱)也不玩了。我对电脑游戏一向没有感觉,总觉得那个虚拟世界太做作了,打个比方说,我宁可看暴力或恐怖电影也不愿去玩那些打来杀去的“魔兽”游戏。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Z是个球迷,喜欢读各家报纸的“球评”(最爱买《体坛周报》),大家一起看球时他就像足球解说评论员,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据我所知,他从来不踢球(当时他正上大学,完全有条件去踢),这一点让我感到迷惑,总怀疑他对足球是否真有热情。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有个同事T,很喜欢玩手机NBA游戏,在拇指间去操控科比(聊天时常用其绰号“黑曼巴”)、韦德(“闪电侠”)、诺维斯基(戏称“德国司机”)等一干当红巨星在小小的界面上运球、转身过人、后仰跳投、空中接力灌篮,下班了我们约他去单位附近的东四篮球场去打球,T可从来不去。说起来,我宁愿不看球评,不玩游戏,只想在球场上左冲右突、奔跑流汗,那种实实在在的肌肉运动的感觉别提多爽了,有此切身体验,我就更不理解那些只看球评、理论一大套的人,那些盯着电脑玩游戏的人,那些“纸上谈兵”的人;请到球场上来吧,那些流汗的人有福了,阿门。因此,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每周二下班会和同事打乒乓球,约的人多于三人就去打篮球。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砖红色的体育中心(墙面是红砖砌的)是少数几个让我感受到快乐的地方之一,那不张扬、低调的红色会让我感到兴奋与喜悦;夸张点儿说,那砖红色像西班牙斗牛士手中抖动的挑逗的红披风,我则像一头心跳与速度不断加快、一直往向前冲的公牛。
五分钟前,在家里看过CCTV“利比亚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的新闻,我招呼儿子整装出发去打乒乓球。我提着一个深蓝色购物布袋(印着“珍爱地球、保护家园”几个白字),里面装着两个球拍、四个乒乓球(两白两黄)、一瓶芒果汁、一串钥匙、我的手机,一些零钱搁在浅蓝色短裤的口袋;儿子穿一件黄色背心、红色短裤,这色彩搭配在白天很耀眼,这会儿在夜晚路灯下,倒柔和了许多。我穿一件白色背心,可以尽享夏夜的凉爽。我和儿子下楼后,沿着小区的石板路,走过一排停在路边的小轿车,转一个拐角,走到幼儿园南侧的乒乓球台旁。
我俩都穿着凉鞋,一是为了凉快,也意味着我和儿子只是随意打打。他是初学,没打过几次,刚学会怎样拿拍子(直拍握法),我也只是想培养他的兴趣,没有过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尽量让他远离电脑,体会一下真正运动的快乐;再说在昏暗的路灯底下,球台视线并不好,想打好也不容易。
儿子长到一米三了(进地铁站都需买票,曾几何时,我抱着不到两岁的他乘地铁,那是他第一次乘车,我们第三次搬家),比球台(标准离地76厘米)高了不少,可以发球,但短球够不着,他手臂没那么长。去年我第一次带他打乒乓球,是在白天,也没打过几次。当时我很期望他能喜欢乒乓球,憧憬着他技艺渐涨,可以和我对打,我就能毫无保留地把我多年的打球心得传授给他,有点儿让他子承父业的意思,尽管我的打法很“业余”,没有师傅教过(俗话说打野球的)。但我一心想把这种热情传承下去,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也许能让儿子终生受益;是啊,一辈子都能体会到运动的快乐,而不仅仅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1952年题词)。我看过一则资料,毛泽东年轻时热衷锻炼,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1914—1918)经常独自一人在大雨中长跑、爬岳麓山,最有名的是年过七旬还畅游长江(1966),以那种独特的、近于在水中行走的“毛氏泳姿”。我相信毛是从运动中体验到快乐的人,不妨称之为“运动家”。
而我自诩为运动家,就从打乒乓球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这样写过:
我在我们村的学校一直上到初中毕业。乡村学校简陋,运动器材极少。我也几乎没打过球,唯一能记得的是初中那会儿的体育课,全班只有一个排球,没有球网,玩法就是老师把排球打高,落下来后同学们一窝蜂地去追,谁抢到后再打上一拳,也是往上打,落下后大家再去抢。这样就更像橄榄球,就看谁的力气大,身体壮。一节课下来,跑得满头大汗,可能连球皮也碰不了一下。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更多的是上学路上的“武术”,以打架、摔跤居多。有真打(常见口鼻流血的),也有玩的。我个头小,很少与同学真打;玩假的,别人又觉得没有成就感。一直到八三年(1983)上师范,我才接触到球类运动。中等师范学校,没有高考压力,前途已定(包分配,当教师),体育、音乐、美术更受欢迎,语文、数学等“主课”反而得过且过,全凭兴趣了,也不开英语课。学校里运动器材齐全,每一级都有一个班是体育专长班(我在普通班),将来就做体育教师。我开始学打乒乓球(水泥台子),打篮球(水泥场子),踢足球(没有草皮却有砂石的土场)。哦,那些流汗、流血(我的同桌M踢球摔伤,手腕骨折)的日子,那些青春荷尔蒙勃发的日子。我乒乓球学得较快,一个学期下来,也有几招撒手锏,比如下旋球,我搓得比较转,角度也刁钻,一般水平的人一接,就会下网或直接出界。
从那时算起,我打乒乓球可有二十七年了。这二十多年里,工作或上学,我从乡村走到县城、省城,十年前搬到北京。伴随我的自然有乒乓球,我的球友算起来可不少了,我打球的风格却多年未变,即以防守反击为主,稳中求胜,或者说是以控制落点和旋转为主,很少主动进攻扣杀。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发球或搓下旋球周旋时,对手进攻的话,常常会打飞或下网,我就不用费力去扣杀了,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后发制人的打法;还有我的性格偏内向(其实我很不喜欢“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喜欢宁静,与和风细雨、深藏不露的稳健打法相得益彰。但这并不说明我不会扣杀,反而因为我对扣杀的美学要求很高,即若不是难度较大的远距离反击扣杀,我就不愿去做;在实战中,当对手回球很高且长时,我就来了兴致,及时侧身,迎着来球起跳,人在半空中即挥臂扣杀(近似于网球的半空截杀),这一招式常会引来对手或旁观者的惊叹(难得一见啊)。对,高难度的、有美学意义的扣杀,才是我愿追求的。而这一招也不是跟谁学的,也许是哪一次打球时忽来灵感,即兴做出的动作,无师自通,后来渐渐成了我风格的标志之一。风格即人;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这句格言,要了解一个人先观察他(她)如何打球。
这会儿,乒乓球台在路灯下(灯在球台北侧有一排,与一行银杏树相间而立)有些昏暗,不过,球速慢的话,还可以看见,来得及反应。我从袋子里取出两只球拍,都是直拍,给儿子一只。去年我开始教儿子打球时,先给他一只横拍(比起直拍来,俗称大刀的横拍,握法简单,也不磨手;在体育馆看专职教练教孩子打球,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横拍,符合国际潮流),教他如何握拍,如何发球、回球,他总掌握不好,一回球就打飞了。后来我把自己用了多年的直拍给他,教他回球,他似乎一下子就适应了,给他发球,一下子就能回到台子上。为了减轻重量(适合儿子的力气),我把拍子一面的胶皮撕掉了(反正已是旧拍子,两星“拍里奥”牌两面反胶直拍,是我2000年到北京后买的第一只拍子,在K大三年一直用它,工作后还用它打了三年,直到前年才在网上买了新的四星“红双喜”两面反胶直拍),儿子就一直用这只只有一面胶皮的拍子。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给儿子留点儿什么“遗产”,我愿把现在我用的这只红双喜留给他;当然最要紧的,是让他能喜欢打球,能打得不赖,至少赶上我现在的水平。
我和儿子各站在台子一端。他直握球拍,身子几乎靠在台沿上(肚脐刚与台子等高),很随意的样子。不过,我不在意他的站法,更不会要求他移动的步法。功到自然成,我相信打得多了,他能领会并掌握的。眼下,我只想他能回过来我的发球,能打两个回合(即他能连续两次接到发球,并打到台子上),就很不错了。他很久没打球,又在晚上,手生加上光线不好,不能对他抱更高的期望。果然,我发的第一个球(落点尽量靠近他挥拍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就打飞了,球划出一道疾速的、灰白的线,落到球台旁边的草丛里了。草不长,球是白的,在黑暗中比较显眼,也好找。儿子跑过去,从草地上捡起球,回到球台,由他发球。他还不会抛起球来发,就先让球在台子轻弹一下,等球下落时再出拍、直推击球,还好,过网了;我挥拍轻挡,控制落点在他正前方,想让他直接再推回来。哦,不出我所料,他又一次把球打飞了,落到球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在小方砖铺的路面上弹跳了五、六下,滚落到路旁的银杏树坑里。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欣慰,他虽然打飞了,可是并没有打空,一年多没打了,他对球的飞行路线和速度还有感觉,能连续两次挥拍击到球(古希腊哲学家说,一个人不能连续两次踏进一条河流),已经让我满意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儿子的球感会越来越好,能和我对打十几个回合。我把这一目标定在他十岁之前,也就是说,他还有三年时间来练习。
我在师范打乒乓球打到第三年的时候,同班男生里已没有几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女生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女生热衷于唱歌、跳舞,打球也是喜欢羽毛球(很奇怪,我一直对羽毛球没有感觉,也许因为它不是圆的)。同级隔壁班上有一个男生L打得很好,他打球时总有一圈人围观,据说全级没人能打过他。课间休息时,球台一端是L,另一端是排着队等着和他过两招的(得先接住他的第一个发球才有资格跟他打一局,五分一局),我曾凑上去试过两次,都败下阵来:第一次一碰球就飞了(他侧旋更厉害),第二次接住球了,但五分里我只赢了一分,还是个擦边运气球。嗨,天外有天啊,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后来有机会,我和他打过几次,都很吃力,整局二十一分,我能上十就不错了。但每次打完,我感觉自己球技都提高不少。毕业后,三生修得同船渡,阿门,L和我同分到渭河北岸一个乡村初级中学教书,成了同事,每天放学后几乎都要打一阵子,旁边一大堆学生围观。可以想象,几个月后,我的球艺就突飞猛进,虽还是很难赢他,但能相持多个回合了,我的防守更为严密,他要得一分也需付出七分功力。L以发球抢攻为主,我则打防守反击,如阴阳八卦,相生相克,有时打得兴起,都不由为对方喝彩,旁观的学生也会鼓掌。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两年,我调到渭河南岸县城边上一所学校,L把自己珍藏的一本《乒乓球的旋转》作为礼物送给我,更让我感动不已。他曾告诉我,从上师范起,这本书就一直伴随着他;也由这本书,我明白,虽不能把打球当职业,但L对打球的认真与钻研劲头儿,可以算得上颇具运动家的风度了。
现在可以谈谈我打乒乓球得到的第一份奖品的事儿,那次获奖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调到渭河南岸学校时,正是八十年代末的多事之秋。这所学校离“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陵(一个庞大的像山丘一样的土堆)不远,我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曾沿台阶登上陵顶,四顾远眺,天地皆白,南山寒气顺势而下,那山峰就像冷冷的刀锋。在这所学校我呆了两年半,是命运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两年。我除了教初一两个班数学外,还带初二两个班的体育课,因为跟同事比起来,我的乒乓球技颇具表演性,既可观赏,也比较实用,无人能敌。到来年三月份,区上教研室组织一次全区中学教工乒乓球赛,我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木质乒乓球桌上打球,欣喜不已,也是第一次在室内打(此前都是在露天水泥台上打了五年),兴奋得有些过头,水平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但我也依靠耐心的搓下旋球、摆短、控制落点,竟然连过三轮,最后得到并列第三名的成绩,奖品是一双“飞跃”牌白球鞋(捆着一条细麻绳,装在牛皮纸袋里)。打完比赛,天已黑尽,我去找在县城工作的同学N和H聊天,他俩都有“门路”,师范毕业后没当教师,在一县之首的县委机关工作,而大部分同学都散落在渭河两岸的乡村学校当“教书匠、孩子王”。后来与他俩告别,从那座灰暗的县委宿舍楼出来,我冲着黑暗中星光点点的天空打了几拳(直拳摆拳勾拳的组合),伴以低声的怒吼;我这样向着虚无中的假想敌进攻,其实是想试一试我的力量,能否支撑我对抗九十年代初的压抑。
我继续和儿子打乒乓球,尽管打不了两个回合,无论是我发球还是他发球,基本上他只能击一次球。但我鼓励他,给他叫好:嘿,不错,一,二,三(我把我击球的次数也算上了),能打三下了,儿子,争取打四下吧!除了鼓励,我尽量让他感受打球过程的乐趣:一次我捡起落在草丛中的球时,手指碰到一块小石子(天黑我没看清,但感觉像石头),我灵机一动,把球和小石子都抓在手里,回到台边,冲儿子说,我发个下旋球,你接招吧。我左手把球晃了一下,右手举起拍子击打,“啪”的一声,打出去的是小石子,儿子一愣,接着“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像是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笑得弯下了腰;笑是传染的,我也笑起来,因为儿子开心也让我开心不已。笑完,儿子从台面上找到那块小石子,模仿我发球(人从黄莺学会了歌唱),小石子先后在球拍和铁栏球网上撞出轻脆的两响,而我举拍夸张地做出回击的动作(自然打到的是空气),一边惊讶地说,咦,球到哪儿去了?又惹得儿子大笑。后来,我把小石子捡起来,放进蓝色手提袋里,留作纪念(两天后,儿子翻袋子时偶然发现那晚我俩打的并非小石子,而是一粒干果核,让他又笑了一阵子。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一只灰白色的猫从幼儿园的铁围栏里钻出来,停在一棵银杏树下不动了,脑袋冲着乒乓球台这边,小心谨慎地观察,判断是否有危险(我在猜测猫的心理)。我小声说,一只猫,让儿子快看。儿子转过身去,瞅着不远处的猫;猫冷静地一动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似乎屏住了呼吸,大约半分钟后,猫迈开步子,稍向左转,朝裁着柏树的小草坡上走去,像悠闲地饭后散步。儿子问我,那猫的尾巴是全的吗?哦,他一定是想起了前两天周末郊游时看到的那只猫。那是周六中午,我带着儿子驾车去远郊一个小镇的农家采摘园观光,这个时节可以采摘葡萄、南瓜、丝瓜、甜枣等。沿路绿树成荫,玉米地成了青纱帐,快到小镇时,看见一片荷塘,有几十亩大,“接天莲叶无穷碧”,更显出乡村风光。在采摘园里转悠了半天,出来在路旁休息,一只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我和儿子身边不远处停下来。它并不怕生,反而朝这边“喵喵”地叫。我注意到猫的毛色灰暗,估计没人饲养,身形也不像小区里常见的口腹无忧的猫那样肥壮。我和儿子牵着手向前走,那只猫跟过来,保持着一定距离,还在“喵喵”地叫。我反应过来,猫是饿了,找人要东西吃,我们身上也没有吃食,没法喂它。后来它终于转身走了,我吃惊地发现它的尾巴只有半截(肯定是被哪个残忍的家伙虐待过,报纸和网上常有这样的报道)。可怜的猫,我把这一发现(猫尾巴断了)告诉儿子。他不住地问我,猫是不是迷路了?它能找到家吗?我看儿子一脸着急的样子,不忍心说它可能是被遗弃的,成了流浪猫;更不忍心说那尾巴很可能是被谁故意弄断的。我只好说,它会找到回家的路,有人会喂它的。在儿子这样的年龄,我只愿他的世界里是蓝天白云,阳光明亮,不愿让他过早接触成人世界的另一面。
现在,儿子站在乒乓球台那端,一再问我那只猫的尾巴是不是全的。我答道,是全的,也许它就是采摘园那只猫呢,这两天它的尾巴长好了,跟原来一样了,它也找到回家的路了,它的家就在附近小区里(善意的谎言,那采摘园离这里得有三十多公里)。儿子半信半疑,还是朝猫隐身的地方(柏树后面)望了望,恍然大悟地说,爸爸,我终于明白了,它这是吃饱了饭出来散步了,帮助消化,就跟我们现在打乒乓球一样(难得儿子说得有条有理,那神态就像是在帮我圆场,尽管那语调还充满七岁孩子的稚气)。
九十年代初,我离开秦始皇陵下的学校,脱产(不再教书)到省城S学院进修,我的命运开始转变,打乒乓球遇到的高手也愈来愈多,特别是碰到更多的横拍球手。之前基本上业余打球的,多是直拍,我周围根本就没有人用横拍。S学院操场东侧有五个水泥乒乓球台,打球的都自带球网。课间休息或午餐、晚饭后,乒乓球台总是挤满了人(打球的,加上排队等着接班轮换的),给人感觉球台从早到晚就没闲过。那时其他文体活动很少,电视都还没有普及,电子游戏厅更少,学院里人气最旺的就是操场和周末晚上的舞会(食堂临时改作舞场,夸张旋转的镭射灯光,廉价刺鼻的香水味、天南海北的饭菜味、男男女女的汗水味混合在一起)。给舞会伴奏的是由学生组建的乐队,主唱F是学院的明星,个子不高,一米七五上下,长得却很俊朗,不仅歌唱得好,还是学院篮球队的主力得分后卫,与其他学院打比赛时,只要他在场,露天球场就被热情的观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严严实实(外层的已从教室里搬来了椅子、长凳,站在上面);不用说,那些呐喊助威的女生大都是冲着F来的。他打乒乓球就是横拍,而且会拉弧圈球(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这种旋转,那时很少能看到电视直播)。我在一旁看他打球,暗暗记下他的一招一式,并私下里摹仿。我特地买了一幅两星红双喜两面正胶横拍,去打球时带上直、横两只拍子,遇到强敌不敢怠慢,用直拍周旋;感觉对手比我弱时,我练习用横拍。这样,我体会到两种打法的区别,各自的优劣,比如直拍快速推挡时灵活,而横拍抽杀时更易发力,更易削出下旋球,变化更多。过了好一阵子,我发觉两种打法太难兼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且积习难改,我还是更习惯直拍,就渐渐放弃了横拍。如今,儿子难道是继承了我的直拍基因,也只对直拍情有独钟?多么奇妙的遗传啊。
猫的疑问解决以后,我希望儿子把注意力转回到乒乓球上。不料,在我灵机一动发明用石子当作球来玩的小游戏后,儿子把心思用在打球之外的可笑(他觉着好玩)的事情上了。他从手提袋里又掏出一个黄色乒乓球,寄给我,他自己手里拿着白球,要和我比赛谁可以把用手把球抛得更高。我有点儿后悔不应玩石子的小把戏,本为提高他的兴趣,不料他兴奋过了头,要玩的游戏已脱离了球台与球拍,与打球无关了。把球抛高,在灰暗路灯下的夜色中,也不好判断到底谁抛的更高。我问儿子,这会儿我都看不清树叶的颜色了,球抛出去,也看不清谁的高呀。儿子想了一下,说我们一齐扔,听声音,谁的球后落下来,就是谁赢了。哦,他怎么竟用了伽利略在比萨斜塔那个著名的铁球实验原理(显然,他并不知道伽利略是谁),不知他的这个经验从何而来。孩子的世界,很奇妙啊。我开始与儿子比赛抛球,他喊一,二,三!我使劲向上抛黄球,他扔白球。可想而知,他的白球落地反弹了好几下,我的黄球才从天而降。儿子把球捡起来,又说准备,一,二,三!我抛黄球的同时,用眼睛余光发现儿子只是扬了一下胳膊,白球并没有出手,他手臂落下时,赶紧把球装进裤兜里。我明白上当了;但我情愿假戏真做:黄球落地后,我依然抬头望着天空,故作吃惊地问,咦,你的白球到哪儿去了,扔到飞机上了(此时刚好头顶有飞机飞过,北边不远处是首都机场)?还是落在树上了?我发出两个疑问后,走到最近的一棵银杏树下,伸手去推树干,晃动树枝,要把并不藏在树上的白球摇落下来。我一边卖力地推树,一边呼唤白球快落下来吧。接着我就听到了球落在地上连续“啪啪啪”的弹跳声(我用眼睛余光看见儿子把球从裤兜里掏出来,随着我的呼唤,把球扔到地上),自然还有儿子“咯咯咯”、开心又得意、天真至极的笑声。我自然要把好戏演到底,恍然大悟地对儿子说,真的落在树上了,从树梢掉下来的,还是你扔的高,你赢了。
从S学院毕业后,我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杂志社人不多,可几乎个个(包括一个女同事Q)都喜欢打乒乓球。我没来之前,主编C是社里的冠军,我去之后,他就只能当亚军了。通常吃完午饭,一伙人就端着茶杯、吸着烟,聚到办公室前边空地上摆的球台边上了。此时乒乓球规则已改成每局十一分制,球也变大了(直径从38毫米增到40),但对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社里打球的几位打法基本一样,都是发球就想抢攻,我只需更耐心地搓下旋球、调动角度,往往不到五拍,他们自己就失误了,不是打飞就是下网。我明白,这样打下去我的水平就会下滑了,所谓近墨者黑。不过,这一时期我对打球胜负已无所谓了,有时我还会故意输给他们几次,以激发其兴致。一天中午,年过半百的主编C跟我打,年过而立的同事G起哄,与旁观者打赌(猜我和C的胜负),输的一方请当时在场的人(计有六人,包括年轻的女同事Q)吃晚餐,主菜为本地名吃葫芦头泡馍,与羊肉泡馍齐名。G赌我负,我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我揣摩,他是在赌我的心理,即认为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定会给主编面子,会让球(当然要让得有技巧,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三局两胜。第一局,前几个球我搓下旋时用力较浅,球弹跳得高,给了C扣杀的机会。此时C体力尚可,好几个球都打中了,比分很快到七比三,他领先。轮到我发球,我加力下旋,C接球下网。我又发一个反方向旋转,C接球飞出球台,七比五。接下来,我接球,也搓下旋球,并放得很短,而C离台很远,等扑上来时,动作已变形,差点儿趴在台上,七比六。这时C已阵脚大乱,我牢牢控制着局面。到九比八时,我领先。我又故意搓球下网,九比九,C又兴奋起来。但我不会再给他机会了,发了一长一短两个下旋球,赢下决胜分。稍事休息,换边,我看见G的脸色阴沉下来。第二局,我改变策略,让比分一路交替领先,到九比九时,C发球,我抢攻,把球打飞了。他又发一长球,我反应慢了一拍,输掉这一局。换边准备决战,G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第三局,如同是第一局的翻版,还是用欲擒故纵法,我先让C大比分领先,我又一分一分追上来,一直到十比十时,我才突然发力,拿下两分。周围的人都喜笑颜开,叫着让G先掏出请客的押金,以防他下班后开溜。主编C输了球,却很大度,他一向随和,况且晚餐还有他最爱的葫芦头,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打得真过瘾啊,出了不少汗,晚上得多吃一碗葫芦头,G这回可得出血了。我对这场球记得很清楚,当时观战者中就有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同事Q。晚上大家一起浩浩荡荡去聚餐,席间免不了觥筹交错,没想到Q很能喝,而主编C称他知道Q的酒量,有一次出差他带着Q去新疆,在天山底下的牧人帐篷里,把几个维族小伙都喝趴下了。不知是真是假。这是我第一次与Q喝酒,也是最后一次;Q笑着向我举杯时,我脑袋已发蒙了,也不管不顾地喝干了一大杯泸州老窖。接下来上洗手间时,我已头重脚轻了。在洗脸池边,我用冷水冲了一下脸,告诫镜子里已面目狰狞的自己,千万要镇静,走路要小心,别出丑。吃完饭,Q坚持要送我回家,她住的楼离我的宿舍平房不远。我能记得走在安静的小巷子里,似乎还有朦胧的月光,我脚步变得踉跄,Q扶着我走,一直到我简陋的宿舍里,让我躺在行军床上,又很麻利地(在书桌找到玻璃杯,从窗台取下茶筒,从洗脸架旁提起开水瓶,熟悉得仿佛在自己家里)泡了一杯热茶放在小桌上。她临走时,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好像在看我是否发烧。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走出门后,我鼻子一酸,泪流了出来,分两路滑到耳边(独怆然而泣下?我又不是陈子昂),让我吃了一惊,我很多年没掉过泪了。那是秋天的事儿。后来我想,那是孤独所致。后来,我开始写作(用铅笔和稿纸),经常在深夜,有一次一直写到黎明,满天的星星似乎就挂在我窗外那株皂角树的梢头,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上床休息(夸张的说法是,与我笔下的人物一同入眠)时,东方既白,星星也隐去了。冬去春来,第二年七月,我离开了杂志社,考到K大深造,北上转到京城来。
我继续和儿子比赛抛球。这与我带他下楼打球的初衷相距越来越远,眼见他打球的兴趣转到不用球拍、不用球台的运动上来了。我告诫自己不用着急,孩子嘛,都这样。只要他能开心,能多在户外玩,也不费我的一片苦心,毕竟他远离了电脑游戏啊。我看着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心想也许真的可以把球扔上树,不让它落下来。我让儿子仔细看,看爸爸也能把黄球扔到树上。我使劲把球抛到树叶稠密的地方,不料,随着地球引力,它又穿过树叶落下来,在人行道上弹跳,儿子笑了;接下来的几次,我试图减轻抛的力度,调整抛物线的弧度,让球在最高点刚好下落时就达到树叶的高度,过高的话,下落的加速度就会冲破树叶的阻挡落到地上,过低的话,不用说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落下来。第五次出手,黄球划出一道向上的斜线,消失在树叶中,半天没有动静。哦,成功了。儿子则惊讶地问,咦,球跑到哪儿去了,飞机上?树上?(模仿我刚才的语气),然后他走过去推树干,可惜力气太小,树叶微丝不动。他向我求援,爸爸你来摇。我让他仔细看,这树上的果子要掉下来了。我晃动树干,树枝明显摇动了几下,可“果子”没落下来;我也有些吃惊,球可能卡在哪儿了。我加大晃的力度,使劲连续晃动,不出所料,黄色的“果子”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弹跳着;儿子哈哈大笑,跑过去追,一边叫着,果子乒乓球。
在K大,开学后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屋的W就一起去南门外一家文体商店买乒乓球拍。两人各买一只,都是直拍,两面反胶,他买的是红双喜,我的是拍里奥(现在儿子手里拿的这只),除了价格上的考虑(红双喜近七十元,而拍里奥五十出头),还有我看中它不张扬、低调,拍把儿近于胡桃木色,拍子份量也适合我。又买了一盒新球,我俩一回来就在宿舍楼下的水泥球台上一试身手。W瘦,高,平时看书要戴近视镜,打球却不戴,我很担心他看不清球的轨迹与旋转。一交手,他的反应明显慢,动作也不协调,尽管身高臂长,球速过快或角度过大时,多半他接不住球。我不想让他的热情受挫,于是放慢击球的节奏,回球时也放得很高,给他抽杀的机会。W打中了几个球,显得很兴奋,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直呼生命在于运动,以后要多打,重新焕发即将奔四的青春。后来,除了打乒乓球,W常和我一起去打篮球。K大三年,许多美好的记忆都与乒乓球和篮球相关,还有夏天打完球、洗完澡在露天烤肉摊喝扎啤、侃大山的酷爽场面。前年,有一次逛古旧书店,偶然在一本与K大诗歌有关的回忆录里,看到W写他忆及难忘的K大岁月,称其同屋(我)为“喜欢打球的J”。毕业后他去了南方,联系渐少,不知他现在还打不打球,即将奔五的满腹的赘肉是否已掩盖了原先清晰可见的肋骨?
看见黄球从树叶间如“果子”一般落下来,儿子又入迷地想自己把白球扔上树。他想让树结出白色的果子。他尝试把球抛高,可惜力气小,几乎无法把球抛到最低树枝的高度。他试了五、六次,每次球都落下来,仅有一次挨着了树叶,但儿子很不甘心。我说我来帮你吧,可他不让。我想到一个办法,即去乒乓球台上取那只拍里奥来(乒乓球拍被冷落在球台上有半天了),交给儿子,你用球拍朝上打球,打高一点儿,就会落在树上了。儿子点头同意,右手直握球拍,左手抛球,开始击球。这一回,受握法限制,他直拍击出的球都向前飞出,还不如手抛得高。我让他换个握法,用横拍握法(如同手持大刀),这样击球会向上飞。果然,他把球打得很高了,可由于方向不准、力度不合适、运气不佳等因素,球还是直落下来、或是从树叶间穿过落下来,反复近十次,儿子毫不气馁,依然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捡球,又回到树旁,向那棵朦胧月光与昏暗路灯映照下的银杏树发起攻击。期间,我让他歇一口气,喝几口芒果汁,又告诉他击球方法及如何调整(没想到啊,如同电视直播乒乓球赛常见的那样,我成了比赛场地旁边一边指点一边递上水瓶的教练)。终于,我都数不清多少次了,儿子击出的白球划出美妙的弧线(加上偶然女神的垂青),钻进树叶的怀抱,不再落下来了。儿子终于,阿门,把乒乓球打上了树。
2011年9月19日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引用:以下是金朝发表的:
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学校的时光。是啊,我记得你打乒乓球很好,当时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夏&( 14:24:19)&
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学校的时光。
好啊,老同学,我记得当时班上你打乒乓球也是高手啊!
:金朝&( 11:02:03)&
:&( 10:06:34)&
3 篇, 1 页 1
(必填)&&&&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发表(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发布者:&|&
浏览(8039) 评论
&|&发布时间: 11:26:33&最后更新时间: 22:30:33
本作品所属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和儿子打乒乓球
晚上,我决定带儿子去打乒乓球。儿子刚过七岁生日,有点儿胖(我担心是运动不足),又在暑期,不用上学,每天有几个小时坐在桌前玩电脑游戏(我又担心他的视力会下降)。我的视力很好,从上小学到现在,一直保持在1.5,按新计量法5.2,我周围的同学、同事大都戴上了近视镜,也有为美观平时不戴,但看书、看电影、上网要戴(有一个女生多年不见,她戴上眼镜的模样让我大吃一惊,简直认不出来了;鬼使神差,看到她黑框眼镜底下苍白的面容,我的第一反应竟是一句西谚:莫与戴眼镜的女子调情)。我把此(与他人相比,优良的视力)归功于我喜欢打乒乓球。
乒乓球台就在我住的楼下,不远,小区幼儿园的旁边,步行五分钟就到。那种常见的水泥(仿大理石台面)台子,球网是横的三条铁栏(多年前我开始学打球时,球网是用几块红砖横放成一排),球打在铁网上会砰砰作响,可想而知很费球,用蛮力打的话,可能会把球磕破;而擦网球更难打出来,铁网根本就没有弹性、也不柔软,按力学原理,球几乎没法擦网而过,只会弹飞。这个乒乓球台很早就摆在那儿,有两三年了,白天都很少有人打,晚上根本就是空空荡荡的。不远处,题作“网师园”的走廓里,午后常有三五成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或下象棋。这会儿只剩下一些桌椅摆在那儿,其中一张桌面上刻着“楚河、汉界”的棋盘,棋子收在一个布袋里,挂在黑色廓柱的一枚铁钉上。儿子六岁时(没上学前)有一阵子对象棋(还有国际象棋)感兴趣,我还带他在此围观过几回;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自从在电脑上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多半是上学后同学告诉他的)以后,他迷上了这款游戏,连电脑上的war chess(国际象棋,上学前儿子的最爱)也不玩了。我对电脑游戏一向没有感觉,总觉得那个虚拟世界太做作了,打个比方说,我宁可看暴力或恐怖电影也不愿去玩那些打来杀去的“魔兽”游戏。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Z是个球迷,喜欢读各家报纸的“球评”(最爱买《体坛周报》),大家一起看球时他就像足球解说评论员,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据我所知,他从来不踢球(当时他正上大学,完全有条件去踢),这一点让我感到迷惑,总怀疑他对足球是否真有热情。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有个同事T,很喜欢玩手机NBA游戏,在拇指间去操控科比(聊天时常用其绰号“黑曼巴”)、韦德(“闪电侠”)、诺维斯基(戏称“德国司机”)等一干当红巨星在小小的界面上运球、转身过人、后仰跳投、空中接力灌篮,下班了我们约他去单位附近的东四篮球场去打球,T可从来不去。说起来,我宁愿不看球评,不玩游戏,只想在球场上左冲右突、奔跑流汗,那种实实在在的肌肉运动的感觉别提多爽了,有此切身体验,我就更不理解那些只看球评、理论一大套的人,那些盯着电脑玩游戏的人,那些“纸上谈兵”的人;请到球场上来吧,那些流汗的人有福了,阿门。因此,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每周二下班会和同事打乒乓球,约的人多于三人就去打篮球。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砖红色的体育中心(墙面是红砖砌的)是少数几个让我感受到快乐的地方之一,那不张扬、低调的红色会让我感到兴奋与喜悦;夸张点儿说,那砖红色像西班牙斗牛士手中抖动的挑逗的红披风,我则像一头心跳与速度不断加快、一直往向前冲的公牛。
五分钟前,在家里看过CCTV“利比亚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的新闻,我招呼儿子整装出发去打乒乓球。我提着一个深蓝色购物布袋(印着“珍爱地球、保护家园”几个白字),里面装着两个球拍、四个乒乓球(两白两黄)、一瓶芒果汁、一串钥匙、我的手机,一些零钱搁在浅蓝色短裤的口袋;儿子穿一件黄色背心、红色短裤,这色彩搭配在白天很耀眼,这会儿在夜晚路灯下,倒柔和了许多。我穿一件白色背心,可以尽享夏夜的凉爽。我和儿子下楼后,沿着小区的石板路,走过一排停在路边的小轿车,转一个拐角,走到幼儿园南侧的乒乓球台旁。
我俩都穿着凉鞋,一是为了凉快,也意味着我和儿子只是随意打打。他是初学,没打过几次,刚学会怎样拿拍子(直拍握法),我也只是想培养他的兴趣,没有过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尽量让他远离电脑,体会一下真正运动的快乐;再说在昏暗的路灯底下,球台视线并不好,想打好也不容易。
儿子长到一米三了(进地铁站都需买票,曾几何时,我抱着不到两岁的他乘地铁,那是他第一次乘车,我们第三次搬家),比球台(标准离地76厘米)高了不少,可以发球,但短球够不着,他手臂没那么长。去年我第一次带他打乒乓球,是在白天,也没打过几次。当时我很期望他能喜欢乒乓球,憧憬着他技艺渐涨,可以和我对打,我就能毫无保留地把我多年的打球心得传授给他,有点儿让他子承父业的意思,尽管我的打法很“业余”,没有师傅教过(俗话说打野球的)。但我一心想把这种热情传承下去,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也许能让儿子终生受益;是啊,一辈子都能体会到运动的快乐,而不仅仅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1952年题词)。我看过一则资料,毛泽东年轻时热衷锻炼,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1914—1918)经常独自一人在大雨中长跑、爬岳麓山,最有名的是年过七旬还畅游长江(1966),以那种独特的、近于在水中行走的“毛氏泳姿”。我相信毛是从运动中体验到快乐的人,不妨称之为“运动家”。
而我自诩为运动家,就从打乒乓球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这样写过:
我在我们村的学校一直上到初中毕业。乡村学校简陋,运动器材极少。我也几乎没打过球,唯一能记得的是初中那会儿的体育课,全班只有一个排球,没有球网,玩法就是老师把排球打高,落下来后同学们一窝蜂地去追,谁抢到后再打上一拳,也是往上打,落下后大家再去抢。这样就更像橄榄球,就看谁的力气大,身体壮。一节课下来,跑得满头大汗,可能连球皮也碰不了一下。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更多的是上学路上的“武术”,以打架、摔跤居多。有真打(常见口鼻流血的),也有玩的。我个头小,很少与同学真打;玩假的,别人又觉得没有成就感。一直到八三年(1983)上师范,我才接触到球类运动。中等师范学校,没有高考压力,前途已定(包分配,当教师),体育、音乐、美术更受欢迎,语文、数学等“主课”反而得过且过,全凭兴趣了,也不开英语课。学校里运动器材齐全,每一级都有一个班是体育专长班(我在普通班),将来就做体育教师。我开始学打乒乓球(水泥台子),打篮球(水泥场子),踢足球(没有草皮却有砂石的土场)。哦,那些流汗、流血(我的同桌M踢球摔伤,手腕骨折)的日子,那些青春荷尔蒙勃发的日子。我乒乓球学得较快,一个学期下来,也有几招撒手锏,比如下旋球,我搓得比较转,角度也刁钻,一般水平的人一接,就会下网或直接出界。
从那时算起,我打乒乓球可有二十七年了。这二十多年里,工作或上学,我从乡村走到县城、省城,十年前搬到北京。伴随我的自然有乒乓球,我的球友算起来可不少了,我打球的风格却多年未变,即以防守反击为主,稳中求胜,或者说是以控制落点和旋转为主,很少主动进攻扣杀。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发球或搓下旋球周旋时,对手进攻的话,常常会打飞或下网,我就不用费力去扣杀了,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后发制人的打法;还有我的性格偏内向(其实我很不喜欢“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喜欢宁静,与和风细雨、深藏不露的稳健打法相得益彰。但这并不说明我不会扣杀,反而因为我对扣杀的美学要求很高,即若不是难度较大的远距离反击扣杀,我就不愿去做;在实战中,当对手回球很高且长时,我就来了兴致,及时侧身,迎着来球起跳,人在半空中即挥臂扣杀(近似于网球的半空截杀),这一招式常会引来对手或旁观者的惊叹(难得一见啊)。对,高难度的、有美学意义的扣杀,才是我愿追求的。而这一招也不是跟谁学的,也许是哪一次打球时忽来灵感,即兴做出的动作,无师自通,后来渐渐成了我风格的标志之一。风格即人;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这句格言,要了解一个人先观察他(她)如何打球。
这会儿,乒乓球台在路灯下(灯在球台北侧有一排,与一行银杏树相间而立)有些昏暗,不过,球速慢的话,还可以看见,来得及反应。我从袋子里取出两只球拍,都是直拍,给儿子一只。去年我开始教儿子打球时,先给他一只横拍(比起直拍来,俗称大刀的横拍,握法简单,也不磨手;在体育馆看专职教练教孩子打球,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横拍,符合国际潮流),教他如何握拍,如何发球、回球,他总掌握不好,一回球就打飞了。后来我把自己用了多年的直拍给他,教他回球,他似乎一下子就适应了,给他发球,一下子就能回到台子上。为了减轻重量(适合儿子的力气),我把拍子一面的胶皮撕掉了(反正已是旧拍子,两星“拍里奥”牌两面反胶直拍,是我2000年到北京后买的第一只拍子,在K大三年一直用它,工作后还用它打了三年,直到前年才在网上买了新的四星“红双喜”两面反胶直拍),儿子就一直用这只只有一面胶皮的拍子。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给儿子留点儿什么“遗产”,我愿把现在我用的这只红双喜留给他;当然最要紧的,是让他能喜欢打球,能打得不赖,至少赶上我现在的水平。
我和儿子各站在台子一端。他直握球拍,身子几乎靠在台沿上(肚脐刚与台子等高),很随意的样子。不过,我不在意他的站法,更不会要求他移动的步法。功到自然成,我相信打得多了,他能领会并掌握的。眼下,我只想他能回过来我的发球,能打两个回合(即他能连续两次接到发球,并打到台子上),就很不错了。他很久没打球,又在晚上,手生加上光线不好,不能对他抱更高的期望。果然,我发的第一个球(落点尽量靠近他挥拍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就打飞了,球划出一道疾速的、灰白的线,落到球台旁边的草丛里了。草不长,球是白的,在黑暗中比较显眼,也好找。儿子跑过去,从草地上捡起球,回到球台,由他发球。他还不会抛起球来发,就先让球在台子轻弹一下,等球下落时再出拍、直推击球,还好,过网了;我挥拍轻挡,控制落点在他正前方,想让他直接再推回来。哦,不出我所料,他又一次把球打飞了,落到球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在小方砖铺的路面上弹跳了五、六下,滚落到路旁的银杏树坑里。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欣慰,他虽然打飞了,可是并没有打空,一年多没打了,他对球的飞行路线和速度还有感觉,能连续两次挥拍击到球(古希腊哲学家说,一个人不能连续两次踏进一条河流),已经让我满意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儿子的球感会越来越好,能和我对打十几个回合。我把这一目标定在他十岁之前,也就是说,他还有三年时间来练习。
我在师范打乒乓球打到第三年的时候,同班男生里已没有几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女生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女生热衷于唱歌、跳舞,打球也是喜欢羽毛球(很奇怪,我一直对羽毛球没有感觉,也许因为它不是圆的)。同级隔壁班上有一个男生L打得很好,他打球时总有一圈人围观,据说全级没人能打过他。课间休息时,球台一端是L,另一端是排着队等着和他过两招的(得先接住他的第一个发球才有资格跟他打一局,五分一局),我曾凑上去试过两次,都败下阵来:第一次一碰球就飞了(他侧旋更厉害),第二次接住球了,但五分里我只赢了一分,还是个擦边运气球。嗨,天外有天啊,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后来有机会,我和他打过几次,都很吃力,整局二十一分,我能上十就不错了。但每次打完,我感觉自己球技都提高不少。毕业后,三生修得同船渡,阿门,L和我同分到渭河北岸一个乡村初级中学教书,成了同事,每天放学后几乎都要打一阵子,旁边一大堆学生围观。可以想象,几个月后,我的球艺就突飞猛进,虽还是很难赢他,但能相持多个回合了,我的防守更为严密,他要得一分也需付出七分功力。L以发球抢攻为主,我则打防守反击,如阴阳八卦,相生相克,有时打得兴起,都不由为对方喝彩,旁观的学生也会鼓掌。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两年,我调到渭河南岸县城边上一所学校,L把自己珍藏的一本《乒乓球的旋转》作为礼物送给我,更让我感动不已。他曾告诉我,从上师范起,这本书就一直伴随着他;也由这本书,我明白,虽不能把打球当职业,但L对打球的认真与钻研劲头儿,可以算得上颇具运动家的风度了。
现在可以谈谈我打乒乓球得到的第一份奖品的事儿,那次获奖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调到渭河南岸学校时,正是八十年代末的多事之秋。这所学校离“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陵(一个庞大的像山丘一样的土堆)不远,我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曾沿台阶登上陵顶,四顾远眺,天地皆白,南山寒气顺势而下,那山峰就像冷冷的刀锋。在这所学校我呆了两年半,是命运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两年。我除了教初一两个班数学外,还带初二两个班的体育课,因为跟同事比起来,我的乒乓球技颇具表演性,既可观赏,也比较实用,无人能敌。到来年三月份,区上教研室组织一次全区中学教工乒乓球赛,我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木质乒乓球桌上打球,欣喜不已,也是第一次在室内打(此前都是在露天水泥台上打了五年),兴奋得有些过头,水平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但我也依靠耐心的搓下旋球、摆短、控制落点,竟然连过三轮,最后得到并列第三名的成绩,奖品是一双“飞跃”牌白球鞋(捆着一条细麻绳,装在牛皮纸袋里)。打完比赛,天已黑尽,我去找在县城工作的同学N和H聊天,他俩都有“门路”,师范毕业后没当教师,在一县之首的县委机关工作,而大部分同学都散落在渭河两岸的乡村学校当“教书匠、孩子王”。后来与他俩告别,从那座灰暗的县委宿舍楼出来,我冲着黑暗中星光点点的天空打了几拳(直拳摆拳勾拳的组合),伴以低声的怒吼;我这样向着虚无中的假想敌进攻,其实是想试一试我的力量,能否支撑我对抗九十年代初的压抑。
我继续和儿子打乒乓球,尽管打不了两个回合,无论是我发球还是他发球,基本上他只能击一次球。但我鼓励他,给他叫好:嘿,不错,一,二,三(我把我击球的次数也算上了),能打三下了,儿子,争取打四下吧!除了鼓励,我尽量让他感受打球过程的乐趣:一次我捡起落在草丛中的球时,手指碰到一块小石子(天黑我没看清,但感觉像石头),我灵机一动,把球和小石子都抓在手里,回到台边,冲儿子说,我发个下旋球,你接招吧。我左手把球晃了一下,右手举起拍子击打,“啪”的一声,打出去的是小石子,儿子一愣,接着“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像是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笑得弯下了腰;笑是传染的,我也笑起来,因为儿子开心也让我开心不已。笑完,儿子从台面上找到那块小石子,模仿我发球(人从黄莺学会了歌唱),小石子先后在球拍和铁栏球网上撞出轻脆的两响,而我举拍夸张地做出回击的动作(自然打到的是空气),一边惊讶地说,咦,球到哪儿去了?又惹得儿子大笑。后来,我把小石子捡起来,放进蓝色手提袋里,留作纪念(两天后,儿子翻袋子时偶然发现那晚我俩打的并非小石子,而是一粒干果核,让他又笑了一阵子。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一只灰白色的猫从幼儿园的铁围栏里钻出来,停在一棵银杏树下不动了,脑袋冲着乒乓球台这边,小心谨慎地观察,判断是否有危险(我在猜测猫的心理)。我小声说,一只猫,让儿子快看。儿子转过身去,瞅着不远处的猫;猫冷静地一动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似乎屏住了呼吸,大约半分钟后,猫迈开步子,稍向左转,朝裁着柏树的小草坡上走去,像悠闲地饭后散步。儿子问我,那猫的尾巴是全的吗?哦,他一定是想起了前两天周末郊游时看到的那只猫。那是周六中午,我带着儿子驾车去远郊一个小镇的农家采摘园观光,这个时节可以采摘葡萄、南瓜、丝瓜、甜枣等。沿路绿树成荫,玉米地成了青纱帐,快到小镇时,看见一片荷塘,有几十亩大,“接天莲叶无穷碧”,更显出乡村风光。在采摘园里转悠了半天,出来在路旁休息,一只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我和儿子身边不远处停下来。它并不怕生,反而朝这边“喵喵”地叫。我注意到猫的毛色灰暗,估计没人饲养,身形也不像小区里常见的口腹无忧的猫那样肥壮。我和儿子牵着手向前走,那只猫跟过来,保持着一定距离,还在“喵喵”地叫。我反应过来,猫是饿了,找人要东西吃,我们身上也没有吃食,没法喂它。后来它终于转身走了,我吃惊地发现它的尾巴只有半截(肯定是被哪个残忍的家伙虐待过,报纸和网上常有这样的报道)。可怜的猫,我把这一发现(猫尾巴断了)告诉儿子。他不住地问我,猫是不是迷路了?它能找到家吗?我看儿子一脸着急的样子,不忍心说它可能是被遗弃的,成了流浪猫;更不忍心说那尾巴很可能是被谁故意弄断的。我只好说,它会找到回家的路,有人会喂它的。在儿子这样的年龄,我只愿他的世界里是蓝天白云,阳光明亮,不愿让他过早接触成人世界的另一面。
现在,儿子站在乒乓球台那端,一再问我那只猫的尾巴是不是全的。我答道,是全的,也许它就是采摘园那只猫呢,这两天它的尾巴长好了,跟原来一样了,它也找到回家的路了,它的家就在附近小区里(善意的谎言,那采摘园离这里得有三十多公里)。儿子半信半疑,还是朝猫隐身的地方(柏树后面)望了望,恍然大悟地说,爸爸,我终于明白了,它这是吃饱了饭出来散步了,帮助消化,就跟我们现在打乒乓球一样(难得儿子说得有条有理,那神态就像是在帮我圆场,尽管那语调还充满七岁孩子的稚气)。
九十年代初,我离开秦始皇陵下的学校,脱产(不再教书)到省城S学院进修,我的命运开始转变,打乒乓球遇到的高手也愈来愈多,特别是碰到更多的横拍球手。之前基本上业余打球的,多是直拍,我周围根本就没有人用横拍。S学院操场东侧有五个水泥乒乓球台,打球的都自带球网。课间休息或午餐、晚饭后,乒乓球台总是挤满了人(打球的,加上排队等着接班轮换的),给人感觉球台从早到晚就没闲过。那时其他文体活动很少,电视都还没有普及,电子游戏厅更少,学院里人气最旺的就是操场和周末晚上的舞会(食堂临时改作舞场,夸张旋转的镭射灯光,廉价刺鼻的香水味、天南海北的饭菜味、男男女女的汗水味混合在一起)。给舞会伴奏的是由学生组建的乐队,主唱F是学院的明星,个子不高,一米七五上下,长得却很俊朗,不仅歌唱得好,还是学院篮球队的主力得分后卫,与其他学院打比赛时,只要他在场,露天球场就被热情的观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严严实实(外层的已从教室里搬来了椅子、长凳,站在上面);不用说,那些呐喊助威的女生大都是冲着F来的。他打乒乓球就是横拍,而且会拉弧圈球(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这种旋转,那时很少能看到电视直播)。我在一旁看他打球,暗暗记下他的一招一式,并私下里摹仿。我特地买了一幅两星红双喜两面正胶横拍,去打球时带上直、横两只拍子,遇到强敌不敢怠慢,用直拍周旋;感觉对手比我弱时,我练习用横拍。这样,我体会到两种打法的区别,各自的优劣,比如直拍快速推挡时灵活,而横拍抽杀时更易发力,更易削出下旋球,变化更多。过了好一阵子,我发觉两种打法太难兼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且积习难改,我还是更习惯直拍,就渐渐放弃了横拍。如今,儿子难道是继承了我的直拍基因,也只对直拍情有独钟?多么奇妙的遗传啊。
猫的疑问解决以后,我希望儿子把注意力转回到乒乓球上。不料,在我灵机一动发明用石子当作球来玩的小游戏后,儿子把心思用在打球之外的可笑(他觉着好玩)的事情上了。他从手提袋里又掏出一个黄色乒乓球,寄给我,他自己手里拿着白球,要和我比赛谁可以把用手把球抛得更高。我有点儿后悔不应玩石子的小把戏,本为提高他的兴趣,不料他兴奋过了头,要玩的游戏已脱离了球台与球拍,与打球无关了。把球抛高,在灰暗路灯下的夜色中,也不好判断到底谁抛的更高。我问儿子,这会儿我都看不清树叶的颜色了,球抛出去,也看不清谁的高呀。儿子想了一下,说我们一齐扔,听声音,谁的球后落下来,就是谁赢了。哦,他怎么竟用了伽利略在比萨斜塔那个著名的铁球实验原理(显然,他并不知道伽利略是谁),不知他的这个经验从何而来。孩子的世界,很奇妙啊。我开始与儿子比赛抛球,他喊一,二,三!我使劲向上抛黄球,他扔白球。可想而知,他的白球落地反弹了好几下,我的黄球才从天而降。儿子把球捡起来,又说准备,一,二,三!我抛黄球的同时,用眼睛余光发现儿子只是扬了一下胳膊,白球并没有出手,他手臂落下时,赶紧把球装进裤兜里。我明白上当了;但我情愿假戏真做:黄球落地后,我依然抬头望着天空,故作吃惊地问,咦,你的白球到哪儿去了,扔到飞机上了(此时刚好头顶有飞机飞过,北边不远处是首都机场)?还是落在树上了?我发出两个疑问后,走到最近的一棵银杏树下,伸手去推树干,晃动树枝,要把并不藏在树上的白球摇落下来。我一边卖力地推树,一边呼唤白球快落下来吧。接着我就听到了球落在地上连续“啪啪啪”的弹跳声(我用眼睛余光看见儿子把球从裤兜里掏出来,随着我的呼唤,把球扔到地上),自然还有儿子“咯咯咯”、开心又得意、天真至极的笑声。我自然要把好戏演到底,恍然大悟地对儿子说,真的落在树上了,从树梢掉下来的,还是你扔的高,你赢了。
从S学院毕业后,我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杂志社人不多,可几乎个个(包括一个女同事Q)都喜欢打乒乓球。我没来之前,主编C是社里的冠军,我去之后,他就只能当亚军了。通常吃完午饭,一伙人就端着茶杯、吸着烟,聚到办公室前边空地上摆的球台边上了。此时乒乓球规则已改成每局十一分制,球也变大了(直径从38毫米增到40),但对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社里打球的几位打法基本一样,都是发球就想抢攻,我只需更耐心地搓下旋球、调动角度,往往不到五拍,他们自己就失误了,不是打飞就是下网。我明白,这样打下去我的水平就会下滑了,所谓近墨者黑。不过,这一时期我对打球胜负已无所谓了,有时我还会故意输给他们几次,以激发其兴致。一天中午,年过半百的主编C跟我打,年过而立的同事G起哄,与旁观者打赌(猜我和C的胜负),输的一方请当时在场的人(计有六人,包括年轻的女同事Q)吃晚餐,主菜为本地名吃葫芦头泡馍,与羊肉泡馍齐名。G赌我负,我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我揣摩,他是在赌我的心理,即认为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定会给主编面子,会让球(当然要让得有技巧,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三局两胜。第一局,前几个球我搓下旋时用力较浅,球弹跳得高,给了C扣杀的机会。此时C体力尚可,好几个球都打中了,比分很快到七比三,他领先。轮到我发球,我加力下旋,C接球下网。我又发一个反方向旋转,C接球飞出球台,七比五。接下来,我接球,也搓下旋球,并放得很短,而C离台很远,等扑上来时,动作已变形,差点儿趴在台上,七比六。这时C已阵脚大乱,我牢牢控制着局面。到九比八时,我领先。我又故意搓球下网,九比九,C又兴奋起来。但我不会再给他机会了,发了一长一短两个下旋球,赢下决胜分。稍事休息,换边,我看见G的脸色阴沉下来。第二局,我改变策略,让比分一路交替领先,到九比九时,C发球,我抢攻,把球打飞了。他又发一长球,我反应慢了一拍,输掉这一局。换边准备决战,G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第三局,如同是第一局的翻版,还是用欲擒故纵法,我先让C大比分领先,我又一分一分追上来,一直到十比十时,我才突然发力,拿下两分。周围的人都喜笑颜开,叫着让G先掏出请客的押金,以防他下班后开溜。主编C输了球,却很大度,他一向随和,况且晚餐还有他最爱的葫芦头,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打得真过瘾啊,出了不少汗,晚上得多吃一碗葫芦头,G这回可得出血了。我对这场球记得很清楚,当时观战者中就有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同事Q。晚上大家一起浩浩荡荡去聚餐,席间免不了觥筹交错,没想到Q很能喝,而主编C称他知道Q的酒量,有一次出差他带着Q去新疆,在天山底下的牧人帐篷里,把几个维族小伙都喝趴下了。不知是真是假。这是我第一次与Q喝酒,也是最后一次;Q笑着向我举杯时,我脑袋已发蒙了,也不管不顾地喝干了一大杯泸州老窖。接下来上洗手间时,我已头重脚轻了。在洗脸池边,我用冷水冲了一下脸,告诫镜子里已面目狰狞的自己,千万要镇静,走路要小心,别出丑。吃完饭,Q坚持要送我回家,她住的楼离我的宿舍平房不远。我能记得走在安静的小巷子里,似乎还有朦胧的月光,我脚步变得踉跄,Q扶着我走,一直到我简陋的宿舍里,让我躺在行军床上,又很麻利地(在书桌找到玻璃杯,从窗台取下茶筒,从洗脸架旁提起开水瓶,熟悉得仿佛在自己家里)泡了一杯热茶放在小桌上。她临走时,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好像在看我是否发烧。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走出门后,我鼻子一酸,泪流了出来,分两路滑到耳边(独怆然而泣下?我又不是陈子昂),让我吃了一惊,我很多年没掉过泪了。那是秋天的事儿。后来我想,那是孤独所致。后来,我开始写作(用铅笔和稿纸),经常在深夜,有一次一直写到黎明,满天的星星似乎就挂在我窗外那株皂角树的梢头,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上床休息(夸张的说法是,与我笔下的人物一同入眠)时,东方既白,星星也隐去了。冬去春来,第二年七月,我离开了杂志社,考到K大深造,北上转到京城来。
我继续和儿子比赛抛球。这与我带他下楼打球的初衷相距越来越远,眼见他打球的兴趣转到不用球拍、不用球台的运动上来了。我告诫自己不用着急,孩子嘛,都这样。只要他能开心,能多在户外玩,也不费我的一片苦心,毕竟他远离了电脑游戏啊。我看着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心想也许真的可以把球扔上树,不让它落下来。我让儿子仔细看,看爸爸也能把黄球扔到树上。我使劲把球抛到树叶稠密的地方,不料,随着地球引力,它又穿过树叶落下来,在人行道上弹跳,儿子笑了;接下来的几次,我试图减轻抛的力度,调整抛物线的弧度,让球在最高点刚好下落时就达到树叶的高度,过高的话,下落的加速度就会冲破树叶的阻挡落到地上,过低的话,不用说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落下来。第五次出手,黄球划出一道向上的斜线,消失在树叶中,半天没有动静。哦,成功了。儿子则惊讶地问,咦,球跑到哪儿去了,飞机上?树上?(模仿我刚才的语气),然后他走过去推树干,可惜力气太小,树叶微丝不动。他向我求援,爸爸你来摇。我让他仔细看,这树上的果子要掉下来了。我晃动树干,树枝明显摇动了几下,可“果子”没落下来;我也有些吃惊,球可能卡在哪儿了。我加大晃的力度,使劲连续晃动,不出所料,黄色的“果子”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弹跳着;儿子哈哈大笑,跑过去追,一边叫着,果子乒乓球。
在K大,开学后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屋的W就一起去南门外一家文体商店买乒乓球拍。两人各买一只,都是直拍,两面反胶,他买的是红双喜,我的是拍里奥(现在儿子手里拿的这只),除了价格上的考虑(红双喜近七十元,而拍里奥五十出头),还有我看中它不张扬、低调,拍把儿近于胡桃木色,拍子份量也适合我。又买了一盒新球,我俩一回来就在宿舍楼下的水泥球台上一试身手。W瘦,高,平时看书要戴近视镜,打球却不戴,我很担心他看不清球的轨迹与旋转。一交手,他的反应明显慢,动作也不协调,尽管身高臂长,球速过快或角度过大时,多半他接不住球。我不想让他的热情受挫,于是放慢击球的节奏,回球时也放得很高,给他抽杀的机会。W打中了几个球,显得很兴奋,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直呼生命在于运动,以后要多打,重新焕发即将奔四的青春。后来,除了打乒乓球,W常和我一起去打篮球。K大三年,许多美好的记忆都与乒乓球和篮球相关,还有夏天打完球、洗完澡在露天烤肉摊喝扎啤、侃大山的酷爽场面。前年,有一次逛古旧书店,偶然在一本与K大诗歌有关的回忆录里,看到W写他忆及难忘的K大岁月,称其同屋(我)为“喜欢打球的J”。毕业后他去了南方,联系渐少,不知他现在还打不打球,即将奔五的满腹的赘肉是否已掩盖了原先清晰可见的肋骨?
看见黄球从树叶间如“果子”一般落下来,儿子又入迷地想自己把白球扔上树。他想让树结出白色的果子。他尝试把球抛高,可惜力气小,几乎无法把球抛到最低树枝的高度。他试了五、六次,每次球都落下来,仅有一次挨着了树叶,但儿子很不甘心。我说我来帮你吧,可他不让。我想到一个办法,即去乒乓球台上取那只拍里奥来(乒乓球拍被冷落在球台上有半天了),交给儿子,你用球拍朝上打球,打高一点儿,就会落在树上了。儿子点头同意,右手直握球拍,左手抛球,开始击球。这一回,受握法限制,他直拍击出的球都向前飞出,还不如手抛得高。我让他换个握法,用横拍握法(如同手持大刀),这样击球会向上飞。果然,他把球打得很高了,可由于方向不准、力度不合适、运气不佳等因素,球还是直落下来、或是从树叶间穿过落下来,反复近十次,儿子毫不气馁,依然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捡球,又回到树旁,向那棵朦胧月光与昏暗路灯映照下的银杏树发起攻击。期间,我让他歇一口气,喝几口芒果汁,又告诉他击球方法及如何调整(没想到啊,如同电视直播乒乓球赛常见的那样,我成了比赛场地旁边一边指点一边递上水瓶的教练)。终于,我都数不清多少次了,儿子击出的白球划出美妙的弧线(加上偶然女神的垂青),钻进树叶的怀抱,不再落下来了。儿子终于,阿门,把乒乓球打上了树。
2011年9月19日
(以下网友留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引用:以下是金朝发表的:
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学校的时光。是啊,我记得你打乒乓球很好,当时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夏&( 14:24:19)&
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学校的时光。
好啊,老同学,我记得当时班上你打乒乓球也是高手啊!
:金朝&( 11:02:03)&
:&( 10:06:34)&
3 篇, 1 页 1
(必填)&&&&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发表(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我和我表姐在一起睡觉 的文章
更多推荐
- ·关于溪木源是什么档次的这个品牌,它在十三届亚皮会上受到了很多关注,是什么品牌?
- ·八月份去天津一日游去哪好坐邮轮,求半日游攻略
- ·等我熬过这所有的苦,这首歌的him的一生这首歌原名叫什么么名字?
- ·南岳衡山包吃住的民宿哪个酒店更适合老人家住?
- ·最近要给亲人购买墓地北京,北京这边的推荐个?
- ·健身会员不愿意一个人来健身房练习,私教该怎么怎样说服一个人?
- ·蛙泳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参考文献献
- ·NEO F38554毛呢大衣冬天穿会冷吗吗
- ·说3个你认为最有智慧的人的名字……… 职业,年代,国别,上古世纪种族选择,政治信仰不限,再说明一下理由,谢谢?
- ·nba手机腾讯网狂言nba,怎么加盟
- ·大腿全身肌肉痛是怎么回事刮了刮发红怎么回事
- ·体育活动用的辐射3皮条客的图片要宽的谢谢亲们╭(╯3╰)╮🙏🙏
- ·晚上23点做健身操洗完澡身上起红点先做好,还是做完健身操在洗好
- ·请问我要怎么合理的健身,我体脂率很好,想无缝美体塑型衣,之前有请过一年的私教,效果不明显,又隔了大半年没健身
- ·求鉴定一双阿迪达斯女鞋neo女鞋 某猫买的 感觉做工略差
- ·假如你有一位朋友,她的名字是吉娜·杰西卡.布朗.芬德利她的体育用品有一个足球(这句话用英
- ·小刚练习投篮命中率160次,命中率是百分之60,他有几次命中
- ·普通扑克牌认牌技巧怎么做标记?怎么认牌?
- ·你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了解多少英文
- ·放学后,我和我的祖国同班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的英文
- ·一星期后要举办校运会立定跳远加油稿,我参加的是跳高和跳远,在这星期内,我该如何锻炼才能发挥最好??
- ·求 不妥 制服丝 袜 第1页做 的 片 ,或者图片也可以
- ·微信抢红包软件靠谱吗那种比较靠谱,怎么买
- ·这种图片怎么做怎么做?
- ·求这一系列书的pdf。希望能跟书的一模一样。求百度会员账号分享云分享。
- ·知道手机号码定位找人怎样定位呢?怎样操作才能找到对方的位置?
- ·求2015优酷会员账号密码一个 保证不改密码
- ·一个人对我说摸摸是什么意思,不想成为复制的粘贴,什么意思
- ·求microsoft office2003330版下载地址
- ·画图工具???
- ·在什么功能可以把图片加字鼠标放上去显示图片?
- ·求这科目四有几道多选题题
- ·求p站怎么看原图原图,ID53671536
- ·百度云网盘资源你懂的 网盘电影资源谁知道